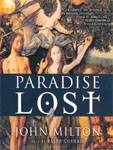《棋王》一一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准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作者:燕山雪** 奔腾的黄河两岸,黄土高原静默着,如同千百年来一直静默着的中国农民的群雕像,任凭母亲河年复一年地从自己的身上割削去大块大块的血肉。我像一个吟游诗人一般在华夏的山河间四处游历,让自己沾染天地万物的灵气和生气,一边采撷诗和歌的种子。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深深感到南方的山水太过秀气,只适合赏玩。漓江的水声如同刘三姐的山歌般动人,却也只是刘三姐般的村姑而已。而当我真正坐着一叶小舟出没于黄河的风浪中时,在黄河洪大的涛声中,我分明听见了无数喉咙在呐喊。 这呐喊声从远古一直回响到今天,有盘古开天辟地时的那声怒吼,也有神农收获第一粒稻米时的欢歌;有大禹治水时的劳动号子,也有长城脚下千万尸骨的...
序言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著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THE ARGUMENTmans transgression known, the guardian angels forsake paradise, and return up to heaven to approve thir vigilance, and are approvd, god declaring that the entrance of satan could not be by them prevented. he sends his son to judge the transgressors, who descends and gives sentence accordingly; then in pity cloaths them both, and reascends. sin and death sitting till then at the gates of hell, by wondrous sympathie feeling the success of satan in this new world, and the sin by man there mitted, resolve to sit no longer confind in hell, but to follow satan thi
- 手机访问 m.---¤╭⌒╮ ╭⌒╮欢迎光临╱◥██◣ ╭╭ ⌒︱田︱田田| ╰--╬╬╬╬╬╬╬╬╬╬╬╬╬╬╬版 权 归 原 作 者【TK】整理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1 蛇宫外面有一个人。晓菌记得他第一次来蛇宫的时候,是个下小雨的下午。整个榕树公园里,都没什么人,蛇宫外面的参观者一个也没有。所以,晓菌和印秋就都记住了这个人。蛇宫是个五十平方米的大玻璃房。临时建立在榕树公园西侧。蛇宫里面有一千八百八十八条蛇。在公证机关的见证下,十九岁的晓菌和二十七岁的印秋,三个月前,就被二十一把铜质大锁锁在这透明的玻璃蛇宫里。她们在创造人蛇同居五千小时的吉尼斯纪录。那个人出现的时候,离破纪录时间还有五十九天,就是说,在离破纪录一千四百多小时的时候,那个人在那个下小雨的冷清下午,来了。...
《玉卿嫂》第一节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没得办法。天天我都逼着她要把我奶妈找回来。有一天逼得她冒火了,打了我一顿屁股骂道:“你这个娃仔怎么这样会扭?你奶妈的丈夫快断气了,她要回去,我怎么留得住她,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已经托矮子舅妈去找人来带你了,今天就到。你还不快点替我背起书包上学去,再要等我来抽你是不是?”我给撵了出来,窝得一肚子闷气。吵是再也不敢去吵了,只好走到窗户底有意叽咕几声给我妈听:“管你找什么人来,横竖我不要,我就是要我奶妈!”我妈在里面听得笑着道:“你们听听,这个小鬼脾气才僵呢,我就不相信她奶妈真有个宝不成?”...
,到底是上海人(代序)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孩子王》一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是什么事,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我没有看见,就掉在地上,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支书又扔过火来,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金沙江’?”支书点点头,呼噜呼噜地吸他自己的水烟筒。待吸完了水烟,支书把竹筒斜靠在壁上,掸着一双粗手,又擤擤鼻子,说:“队里的生活可还苦得?”我望望支书,点点头。支书又说:“你是个人才。”我吓了一跳,以为支书在调理我,心里推磨一样想了一圈儿,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就笑着说:“支书开我的玩笑。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只管派吧,我用得上心。”支书说:“我可派不了你的工了。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
,致谢&序。^生.网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几篇是发表过的,曾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陈麟瑞、李健吾两先生曾将全书审阅一遍,并且在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愿他们几位不嫌微末底接受作者的感谢。序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
,洪晃谈新书 在话题讨论环节上,大家就我们到底是应该像洪晃一样注重生活品质和感觉的无目的生活,还是注重目标,努力生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洪晃与主持人、好朋友们虽然各抒己见,气氛活跃。洪晃感慨到:“我们的投入都是非常有目的的,是追求回报的。在咱这儿,投入的人不少,哪怕是投入爱情、艺术和友谊,都能算出个内部、外部和中部的回报率,算不出来就坚决不投。”,“我是一个喜欢发现并享受生活中的“好玩”的人;一个喜欢找乐的人。找乐对她来说,既是生活态度,又是生存状态。”洪晃感情经典对白现场观众问,“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我是指朋友、爱情、工作。”洪晃的回答很经典,“当然满意,因为我过着无目的的美好生活啊”。 ...
,A MILD ATTACK OF LOCUSTS-1{小}{说}{网}the new yorker fiction by doris lessing february 26, 1955the rains that year were good; they were ing nicely just as the crops needed them—or so margaret gathered when the men said they were not too bad. she never had an opinion of her own on matters like the weather, because even to know about a simple thing like the weather needs experience, which margaret, born and brought up in johannesburg, had not got. the men were her husband, richard, and old stephen, richard’s father, who was a farmer from way back, and these two might argue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