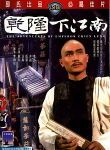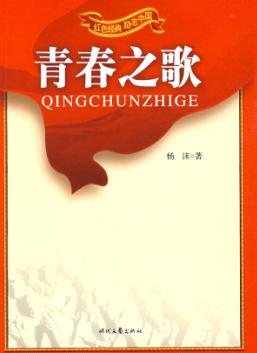《乾隆下江南》第01回 北京城贤臣监国 瑞龙镇周郎遇主话说自李闯乱了大明天下,太祖顺治皇帝带兵过江,定鼎以来,改国号曰大清。建都仍在北京,用满汉蒙古八旗兵丁,从北至南,打成一统天下。开基创业以来,九十余年,传至第四代仁圣天子,真是文能安邦,武可定国,胸罗锦绣,满腹珠玑,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三坟五典,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兵书战策,十分精通,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是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八方进贡,万国来朝。真马放甫山,兵归武库,僵武修文,坐享升平之福,有诗为证:天地生成大圣人,文才武艺重当今。帝皇少见称才子,独下江南四海闻。却说一日,五更三点,圣驾早朝,只见左边龙凤鼓响,右边景阳钟鸣,内侍太监前呼,宫娥翠女后拥,净鞭三下响,文武两边排。圣天子驾到金銮宝殿,升坐龙案之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及内外大小臣等,三呼万岁,朝见君王。圣上传旨,即赐卿等平身,随启金口说...
李有才板话一 书名的来源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是他爹给留下的,後来把地押给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楣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于公案》第一回 于按察山东赴任 邹其仁赴路登程话说本朝康熙皇帝年间,君圣臣贤,风调雨顺,出一位才能直臣,系镶黄旗汉军,姓于,讳成龙,初仕乐亭县知县。为官清明,审假虎智锁群贼,花驴巧拿恶棍,莺歌鸣冤,与哑巴断产,问忤逆孝子伸冤,夫妻团圆。总督一喜,会同抚院保题,奉旨升授直隶通州知州。心如秋水,一尘不染,审明许多公案。万岁闻知,特旨升擢山东按察使之职。谢恩回府,亲友庆贺,舆马满门,吉期已到,带领夫人公子家丁出京上任。三春景致,过些府城州县,早行夜宿,饥餐渴饮。且说一位琴堂姓邹,名其仁,原籍山西汾州人氏,科甲出身,年交四十,两房妻室,罗氏生有一子,名唤邹舒,年方一十九岁。邹公新选山东蒲台县知县,在吏部领文凭。不料夫人染病沉重,限期紧迫,留公子照管家园,带了四个家人起身赴任,不辞辛苦。这日,天交酉末,太阳西坠,至青阳镇,催马进村细观,耳听招呼:“客官歇罢,一应酒饭俱全...
《腊月·正月》第一章一这地方很小,却是商州的一大名镇。南面是秦岭;秦岭多逶迤,于此却平缓,孤零零地聚结了一座石峰。这石峰若在字形里,便是一个“商”字,若在人形里,便是一个坐翁。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秦时,商山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避乱隐居在此,饥食紫芝,渴饮石泉,而名留青史。于是,地以人传,这地方就狭小到了恰好,偏远到了恰好,商州哪个不知呢?镇前又有水,水中无龙,却生大娃娃鱼,水便也“则名”,竟将这黄河西岸的陕西的一片土地化拙为秀,硬是归于长江流域去了。地灵人杰,这是必然的。六十一岁的韩玄子,常常就要为此激动。他家藏一本《商州方志》,闲时便戴了断腿儿花镜细细吟读;满肚有了经纶,便知前朝后代之典故和正史野史之趣闻,至于商州八景,此镇八景,更是没有不洞明的。镇上的八景之一就是“冬晨雾盖镇”,所以一到冬天,起来早的人就特别多。但起来早的大半是农民...
《三遂平妖传》第一回 胡员外典当得仙画 张院君焚画产永儿词曰:君起早时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东京多少富豪家,不识晓星宜到老。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汁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足栽花蹴气球。那东京城内势要官宦且不说起,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其中个一员外,家中巨富,真个是钱过壁斗,米烂陈仓。家中开三个解库:左边这个解库专当绫罗段匹;右边这个解库专当金银珠翠;中间这个解库专当琴棋书画,古玩之物。每个解库内用一个掌事,三个主管。这个员外姓胡名浩,字大洪,止有院君妈妈张氏,嫡亲两口儿,别无儿女。正是眼睛有一对,儿女无一人。一日,员外与妈妈用坐在堂上,员外蓦然思想起来,两眼托地泪下。妈妈见了,起身向员外道:”员外!你家中吃的有,着...
《文明小史》楔子 做书的人记得:“有一年坐了火轮船在大海里行走,那时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顶,四下观望,但见水连天,天连水,白茫茫一望无边,正不知我走到那里去了。停了一会子,忽然东方海面上出现一片红光,随潮上下,虽是波涛汹涌,却照耀得远近通明。大众齐说:“要出太阳了!”一船的人,都哄到船顶上等着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阳果然出来了。记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饭才罢,随手拿过一张新闻纸,开了北窗,躺在一张竹椅上看那新闻纸消遣。虽然赤日当空,流金铄石,全不觉半点藃热,也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停了一会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乌云,隐隐有雷声响动,霎时电光闪烁,狂风怒号,再看时,天上乌云已经布满。大众齐说:“要下大雨了!”...
《冷眼观》第一回 读奇书旧事觉新民 游宦海燃萁空煮豆我记得那年从东洋毕业回国,一径就往北京去赴部考验。因路上风波劳顿,觉脑气筋里异常困倦,听人说琉璃厂是个人文荟萃之区,我独自一人逛到那里去醒一醒渴睡。忽从一家书坊店门首经过,见有一部手抄的书稿,表面上标着《冷眼观》,我拿过翻开一望,见那书中记载的人名事实,倒有一大半是我夹袋里的东西,那著者竟是先得我心了。当下就问那书肆主人:“要几何代价?”不意他不慌不忙说出几句料想不到的话来。看官,你们想他说甚么?原来他说:“我这部书,却有两等卖法。”我忙请问他哪两等?他道:“若是顽固党守旧派来买我的这部书稿,我非要英金三百镑不可;倘有热心公益中国前途新学界一般种子情愿要,我就分文不取,双手奉赠他也可以使得。”我见他吐属慷慨,就对他唱了一个大喏,先致谢了他赠书的美意,然后向他说道:“我虽不是新前途,却也异乎旧党派。我大概看了看你那...
《青春之歌》第01章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
行军掉队记夜雨飘流的回忆夜雨飘流的回忆一、无心阁的小客栈里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门,靠着天心阁的城垣,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像埋在话的墓场中似的,一连埋了八个整天。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饭外,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啸着,盘旋着,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一到夜间,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我记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也许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