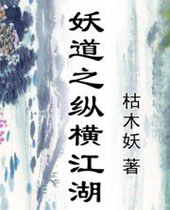相忘于江湖-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无数次梦到你微笑的样子,无数次,浮动的花香充满梦境。
只是怕醒来。
你我早已经约定,落地生根之后,心疼深入地下,这样的希望到底还算不算希望。把你带走,离开这里。
“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这徒然的思念,枉然的追寻,何时是一个尽头?他渐渐明白了自己宿命的结局,于是又有了一首《鬲溪梅令》。 “丙辰冬,自无锡归,作此寓意”,却还是借梅花以寓意:
好花不与殢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木兰双桨梦中云。小横陈。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翠禽啼一春。
好花并不等待那爱花的人,何况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开罢还将凋落。如今,丙辰过了是丁巳,冬过了是春。重拾旧欢,再续前缘,似乎的确不可能了。
十天之后,正好是正月十一,旧俗上元节日看灯的才是新年中最热闹的事情,小小的姑娘吵闹着要父亲带他去玩——
巷陌风光纵赏时,笼纱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
把女儿扛在肩膀上看灯,在人群中,每一张笑脸都沾满了月光,灯光,只有他自己的脸上有一抹暗影。他忽然想起了一首词,想起了往事。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月光如此沉重,心事磨损,成了薄薄的一层,盛不下这月光,落入心里,竟然如此冰凉,
压满心头的记忆,满满的,却说不上来,没有记叙,没有抒情,只有这淡淡七个字:少年情事老来悲。他的文字已经淡到了平白如水的境地。彻骨的寒冷只化为浅浅的春寒,他缓缓地走着,回答女儿各种奇怪的问题。她还不懂人世的悲欢。
元夕之夜,姜夔他做了一个梦,安静怦然碎裂,他的心又一次滴血。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人已去,楼已空,一场苦恋,终成绝唱。20年时光太久了,他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提到合肥,也没有如此清楚地说起这段爱情。
早知如此,悔不当初。这一句话让姜夔直接说出来,实在是不容易。20年苦苦追求,20年风雨兼程,20年无语泪流,无数次的暗夜冷梦,化为一声长叹,几个文字——这首词写得千转百回,柔肠寸断,到如今,故事好像已经讲完了。
梦里梦外,你依然是个不得已的人。
。d 。
西洲曲(节选)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心如莲子
这首《西洲曲》和许多的古诗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写作的时间和作者都难以考订。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的时候把它收入“杂曲歌辞”类,认作是“古辞”。《玉台新咏》则把它认作江淹诗,但宋本不载。明清人编辑古诗选本时也有分歧,一把它作为“晋辞”,一把它认为是梁武帝萧衍所作。遂难成定论。但从内容和风格看,它当是经文人润色改定的一首南朝民歌,精致流丽。大约美的东西,都会被喜爱的,一直被广为传诵。
此诗以四句为一节,基本上也是四句一换韵,节与节之间用民歌惯用的“接字”法相钩联,读来音韵和美,声情摇曳。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它“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确实道出了它在艺术上的特色。然而,如何正确理解这首诗的内容,颇费争议,直到目前也未能辩白,我是个疏懒的人,无心作什么考据。但它是首好诗,对我来说,这样扑朔迷离的背景倒有它的好处,闭上眼睛,触摸内心的一丝懵懂,诗句开篇说的“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慢慢想起来,梅,她是谁?
一个衣着杏子红的女孩子,背对你站在依依的水岸,看不清她的眉眼,乌黑发亮的长发在风中被轻轻地扬起……
她思念着谁吧?炽热而微妙的心情随着时光流转。
这首诗既不是以少女自述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写,也不是第三人称的客观描述,好像是一个错觉,让你在阅读的时候,无意之间进入角色,是她想起了你的——错落之间,那根神秘的弦被拨动。
这种手法,被后来的杜甫在《月夜》中借用,写诗人对月怀念妻子,却设想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正是使用同样的手法。这是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的总的设想;若不这样理解,那将是越理越乱,最终变成一团乱麻,使人读来神秘恍惚,造成似懂非懂的印象。
一首好诗背后一定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要讲一个故事很容易,世人就像一个孩子,吸引他的永远只是那奇思异想的情节,和那皆大欢喜的结局。他们需要的是归宿,快乐,以及一种取之不尽的幸福感觉。
那样真的很好做到,就像哄一个孩子开心,告诉她,无论如何,都不用难过!可是我知道那并不是真实的生活,生活从来不屑于演绎一个完整的故事,倒是我们这些辗转在生活路途上的客人孜孜以求的还是那触手可及的有始有终。
生活是一个人在未知的尘世里遭遇一种耐人寻味的平常,所以要讲一个人就难了,如何才能让她的眼神和你对视呢?再拨开历史和尘俗的羁绊,与你面对,让你安心地注视一个颤抖的灵魂,聆听她的述说——
西洲在什么地方?没有办法追究了,诗句说是:两桨桥头渡,应该是江边吧。温庭筠也有一首《西洲曲》,中有“艇子摇两桨,催过石头城”之语,可知“两桨桥头渡”是说摇起小艇的两桨就可直抵西洲桥头的渡口。
那时他要离开,我该说些什么呢?要走的会走,而要来的终究会来?
这样的话,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心,也不是我一个人有。
他修长的手指慢慢地勾着我的长发,说:我还会回来的,你等我!
而等待,那样的感受,又有多少人熟悉呢?
桥头渡口。乌桕树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常常伫立水边,这种意境最早出现在《诗经》里,妇孺皆知的一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雨丝轻盈地落在平静的水面,一弯弯的涟漪轻轻散开。过后那平静的水面,从不像是有过碎裂的痕迹。时间,就那么轻易地抹平了一切,或许那被寂寞苫荑过的土地上,那青葱的是隔年春色。
这是我看到的,我是对他说过,我的确不恨他。
这样等他归来。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他的样子在她的心头萦绕,他的声音,他的一举一动。
这样一个安安静静活着的人,眼睛里总含着默默的笑意。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那莲子是一颗心的,这样的话就是初相识的时候,他说过的。两个人一起去采莲,回来,他给她拨开说:“你看看,这红红的莲心。”依然,我知道的。
我拖过一张堆锦的旧地毯,盘着腿坐在上面一颗一颗的剥莲子。破开的一颗莲子,粉红鲜润的汁水顺着白皙的几乎透明的手指缓缓流下,喷薄满目的颜色该有多娇艳啊?
回过头来的侧影像还在我面前一样切近而清晰,带着鉴赏中的满足感,这家伙好像是有点舍不得我的样子,有点忧郁地对我笑着。
“爱你,或者是更爱,可是怎么会只是一个梦境呢?”对着空寂的庭院自觉无聊的笑笑,回忆和虚幻交织而成的爱人的影子,单薄得只需一个念头就可以击穿。内心深处的一角悄悄地陷下去,到那幻影彻底破灭的时候,我会怎样呢?
我静静地坐着,手指机械地剥着一颗颗的莲子。我想自己就这样做一个大宅院的女主人,其实也不错。我给他弹琴,让那个人斜靠着坐在我对面对我说:
你的琴弹得多好——你那么美,那么好,谁能不爱你?
在朽旧的阁楼上,只有飞鸿缥缈,落日沉沉。又一天这样在相思等待中过去了。水意悠悠,天空窈廖,心却越来越小,慢慢地只能容下你的影子。
回来,徘徊不定,终于累了,坐在廊下。
那桢木的地板铺成的前廊是一种古旧的深褐色,庭前是一的树冠下,一片恬静的浓荫罩着树下一个个有浮雕花纹的大缸。那里面浮着莲花和莲叶,雪白碧绿的田田簇成一片,向是初夏里解不开的梦境。
微闭着眼睛仰面对着天空,袅娜的风儿落下,拂着脸庞,擦着鬓发。我想自己将来出阁了,做这样一个大宅院的女主人。过了晌午就坐在这散发着古木清香的回廊里坐着,捣茶叶,剥莲子。黄昏里点上紫陶的小炉子,慢慢的扇起火来煮水,雪白的莲花枕着碧绿的梦静静地睡着。
没有一个人在身边,也没有一点声音,那时候就能听到,听到谁的脚步声慢慢的近了,在我身边坐下。掬起我的长发,悄声细语的和我说话。那声音和最初见时那样,轻柔细腻得不起纤尘。
而梦在绿色的水纹间摇荡,扬起,飘去……
/d/
采莲曲
小说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江南可采莲
《相和歌辞》是乐府歌曲名。据《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我素来喜欢旧歌,因年代久远,而散尽了流行歌曲的烟火气,有古意迷漫其间,自然而然,情意流转而出,让人忘却时光年岁的催迫。这是古歌最大的妙处。
比如这首《江南》,此曲为《相和歌辞·相和曲》其中的一首。原见于《宋书乐志》。书中说:“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说得很明白,这些歌来自民间,质朴清新,和文人们雕琢出来的歌词大有不同。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这样的民歌纯属天籁,当初的创作者或许并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单纯为快乐而快乐的歌谣,你只须侧耳倾听就够了。
这些歌原来多是无乐器伴奏的口头歌谣,后被乐官们采入乐府,以丝竹配奏。到了三国,又经过精通音乐得乐官们改造,成了魏晋的“清商三调”歌诗。更加精美和谐。如一粒饱满光泽的珍珠,垂落在听者的心里。美,不言而喻。
你若喜欢,我们就去那个曼妙唯美的绿色江南吧!
我喜欢春天,好像经过的冬天的寒冷,寂寞了太久。渴望绿色的心情很是迫切,出了三月,便几遍几遍地看路边的柳树,寻觅鹅黄破枝的那一丝萌动。
我也喜欢阳光,最好是初暖的时分,乍暖还寒的时候,阳光就觉得最为珍贵。甚至能感到阳光是柔软的,光滑的错觉,其实那不是光,而是“吹面不寒杨柳风”。
因为久居北方,所见到的多是粗粝的北风,就算是春夏,绿树红花,也依然觉得不够。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去江南,当然是夙愿。欠下心灵的一笔有年的债务。有了时间,找些空闲,必须要还清的。
在北方见水,多则是一不大的湖泊,犹有造作的痕迹。要见荷花更是不易。就算见了,也是池塘里的寥寥的莲叶。水多浓郁,不觉得清洌。就算是一幅美妙的山水画,也还缺少一份灵动的气息。
北方看莲,算是雅趣。没有采莲嬉戏的喜人。大家都记得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月夜看荷的美文。其实那里面最多的是情趣。
说到快乐,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沉积于内的心事: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清华园里面是有水塘,虽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色泽也似乎不比先生当年的差,荷花也还是那么多,看荷花的人也更多,而且清华的才子俊女多不胜数,自然赐予他们的享受,可谓适得其所。然而还是有些遗憾,像朱先生那样的文雅淡远的名士几乎没有了。景色也就少了一个灵魂。
朱先生的时代多少是拘谨苦涩的。夜半出游,寻求的自然是宁静超脱。月下看荷和当年苏东坡月下游寺相同。一半是寂寞郁闷,一半是寄情山水。
一份含而不发的忧愤。在内心里努力寻找着自我平衡的力量。
这依然还是中国读书人的士大夫的古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