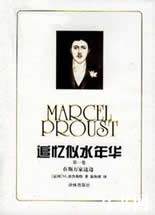战争与回忆-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此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人家觉得难以置信,斯鲁特也不能责怪他们。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已经是陈旧的故事,一次那样的集体杀戮,死人究属有限。纳粹党人不屑费心去遮掩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劫掠;秘密杀害无辜,数以十万百万计,这样的传闻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而纳粹却一概斥之为盟国的宣传或犹太人的梦吃。然而这样的屠杀还在继续,至少斯鲁特相信是如此。万湖会议纪要中的计划确实正在付之实现,在一个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恐怖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却象月球背着地球的那一面一样,永远没法知道它的真相。
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苏打水灌下他的咽喉,留下一股热辣辣的余味,使他舒畅宽慰,使他感到飘飘然。他简直有点象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回头观看着这个瘦骨鳞峋、戴着眼镜的他自己,直挺挺地躺在扶手椅和垫脚凳上,也很为这个聪明家伙感到惋惜,他也许会为了该死的犹太人牺牲掉他的前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人类的一员,而且神志清醒。如果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知道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不与之斗争,人类的前途还有多少希望呢,是不是?谁又能说得出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所办不到的呢,只要他找到了适当的言语去向全世界诉说,去向全世界宣告,去向全世界呼吁?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做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做的?
斯鲁特知道,独自借酒浇愁到了想到马克思和基督的地步,就该适可而止了。也是该上床安歇的时候了。他也就上床了。
第二天早上他正卷起衬衫袖子在打字机上打一封信给拜伦。亨利,把打听得来的关于娜塔丽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秘书进来,她名叫海迪,是个肉感风骚的碧眼金发姑娘。海迪一见斯鲁特便要卖弄风情,不过在他看来,她也就好象一块裹在裙子里边的奶油蛋糕。“日内瓦领事馆的韦恩。 比尔先生说你约好等他来的。”
“哦,是的。请他进来吧。”他把信锁进抽屉里,急忙穿上一件上衣。韦恩。 比尔一进来,海迪禁不住向这位英俊年轻的美国副领事频送秋波。此人身材矮小,前面的头发也已秃了许多,但是腰身笔直,腹部平贴,两眼明亮,所以额上的光秃也就不值得介意了。他是因为心脏得了杂音才从西点军校中途退学的,年已三十,步伐却仍象一个士官学员,并且一直在设法重回陆军。海迪弄姿作态走了出去,比尔目送她的背影,好象有点出神。
“你没把文件带来?”斯鲁特关上房门。
“见鬼,没有,生怕在火车上失落掉这样的东西,我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如果公使决心要采取行动,我会把我手头所有的东西都给他送来。”
“给你约定十点钟见他。”
“他知道是为这件事吗?”
“当然。”
比尔觉得很有难处,脑门上布满了皱纹。“我对这件事情也感到莫测高深。莱斯,你也一起谈,是吗?”
“不行。人家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有神经玻”
“见鬼,莱斯里,谁说你神经病来着?你已经看过那些案卷。你知道提供材料的是什么人。你的才华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可差得远了。去他妈的,你来吧,莱斯。”
斯鲁特觉得无可奈何,也预感事情不妙,说道:“可是得由你一个人说话。”
公使穿了一套凉爽的夏服和一双粉刷得雪白的皮鞋。他说他要去出席一个花园宴会,所以这次会见不能不干脆痛快。他朝转椅里一坐,一只好眼睛注视着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的两个人。
“公使先生,我感谢您从繁忙的日程中抽出这点时间给我,”比尔开始说,声调和手势都不免干脆痛快得过头了一点。
公使把手一挥,既不耐烦,也不以为然。“你有什么新的消息?”
韦恩。 比尔立即开始口头汇报。有两份互不相干的证实大屠杀的过硬材料到达了他的办公室,都是来自上层人士。他还从第三个来源得到目击者的宣誓证词,证明大规模屠杀的真实情况。他说得详详细细,还说了一大通什么空前浩劫、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公使的明智之类的话。
公使把脸撑在一只手上,活象一个不耐烦的法官,他问:“是什么上层人士向你证实的?”
副领事说一个是知名的德国工业家,另一个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负责官员。如果公使需要知道名字,他可以设法征求这两位先生的同意,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你亲自跟他们谈过话吗?”
“哦,没有,公使!谁肯跟一个美国官员推心置腹呢,除非他们跟他非常熟。”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他们的报告的?你又怎么知道它们是真实可靠的?”
比尔略有窘色,说是得自犹太人的来源:世界犹太人大会和争取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斯鲁特察觉,公使顿时失去兴趣:那只活动假眼转来转去,两肩垂下。“又是转过手的报告,”塔特尔说。
“公使先生,”斯鲁特按捺不住了,“关于希特勒的一个秘密计划,又能有什么别样的报告呢?”他没法不让他的声音里带点火气。“至于这个德国工业家,我自己跟他在WJC会所里谈过话,他把——”
“WJC是怎么回事?”
“世界犹太人大会。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只是没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此人是德国工业界的巨子。我也看到了目击者宣誓证词的文件。全都是有血有肉的毁灭性的揭露。”
“我的报告还没有完呢,公使先生,”比尔说。
“哦,还有什么?”公使拿起一把象牙裁纸刀拍打着手巴掌。
比尔谈了他和日内瓦的英国领事都就新证据向国内发出内容相同的密码电报,以便秘密转给犹太人领袖。英国外交部立即把电报转给了特别指定的英国犹太人,但是美国国务院扣押了电报。现在美英两国的犹太人领袖除了因为新透露的情况议论纷纷外,也正因为国务院的这一举动已被发现而觉得义愤填膺。
“这个问题我要查问一下,”公使说,把裁纸刀往桌上一扔。“以后我会告诉你的,韦恩,现在我有点话要跟莱斯里谈。”
“很好,公使先生。”
“在我的办公室里碰头,韦恩,”斯鲁特说。
比尔出去了,随手带上了房门,公使瞧瞧手表,揉揉他的好眼睛,对斯鲁特说:“我得走了。你听我说,莱斯,我不喜欢这种扣押电报的举动。欧洲事务司真叫我觉得莫名其妙。它对我的两封信都没理睬,一封是关于签证规定的,另一封是关于你的影印件的。”
“你为影印件写过信了?”斯鲁特急忙问。“什么时候?”
“波兰流亡政府公布材料的时候。它使我重新加以考虑。他们怎能假造出所有这一切?统计数字,具体地点,一氧化碳密封货车,半夜里突然袭击犹太人聚居区?搜查妇女尸的肛门和阴户是为了什么,寻找钻石珠宝吗?谁能够凭空想象得出这样的事来?”斯鲁特两眼盯着公使,胜日结舌。“就算我们承认波兰人是靠不住的。就算我们也认为他们故意给德国人抹黑,以便掩盖他们自己干的混帐事情,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呢?维希政府的警察把成千上万外来的犹太人跟他们的幼年子女相互隔离,运走了那批做父母的,上帝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在记者的摄影机镜头前面发生的事。毫无秘密可言。我收到一份基督教青年会详详细细的报告。真是叫人揪心。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你的影印件给国务院写了信,可是那不过是好象往深井里丢下一颗石子。还有关于那签证的事,莱斯,真是太过分了。”
“我的上帝,我想你是指的品行端正证明!”斯鲁特大声说。“我已经为那件混蛋事情打了几个月官司了。”
“一点不错。我简直不敢朝瑞士官员的眼睛看,莱斯里。我们并不是在作弄他们,我们恰恰是给我们自己的国家丢丑。一个逃出虎口的犹太人怎么拿得出一份他的德国老家的警察局签发的品行端正证书呢?这分明是故意按个钉子,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这儿卡祝我们非要把它废除不可。”
斯鲁特面色苍白,注视着塔特尔一清了清喉咙。“你使我重新感到人间的温暖,先生。”
公使站起身来,对着壁橱里的镜子梳好头发,把宽边草帽戴在头上摆弄好了。“况且,铁路方面的情报也是怪得出奇。那些装得满满的特长列车,确实都是从欧洲各地载运平民到波兰去的,然后掉转头来,开回来的全是空车,在此同时,德国军方却因得不到车厢和车头而焦急万状。我知道这是干真万确的事实。准是有什么蹊跷的事儿正在进行,莱斯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是只有你我两人知道的。我为这件事情写过一封给总统亲启的信,可是我后来又把它撕毁了。我们正在打败仗,实在不能再给他增添什么别的负担了。如果德国人打赢了,整个世界便要成为一个大屠场,要处死的并不只是犹太人。”
“我相信这一点,先生,不过——”
“好了,你去告诉韦恩。 比尔把他的材料全部汇集一下。你上日内瓦去给他帮个忙。只要你办得到,就设法让那位红十字会的头面人物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写下来。”
“我可以试试看,先生,不过这些人对德国人都害怕得要死。”
“行,你就尽力去办吧。这一回我要把材料直接寄给萨姆纳。威尔斯。其实你就可以担任这个信使。”他那只好眼睛对准斯鲁特发出赏识的光彩。“你?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在国内度上一个美好的短短假期?”
斯鲁特顿时觉察到,这样一桩使命会永远断送掉他在外交界的前程。“难道韦思。 比尔不正好是个现成的信使,先生?材料都是他搜集来的。”
“重心不在于材料。他不如你熟悉这个问题。”
“塔特尔先生,车子在等着,”案头扩音器发出一阵沙嘎的声响。
塔特尔出去了。斯鲁特走回办公室,一开门便听见里面的欢笑声。韦恩。 比尔和海迪在里面站着,显得很窘,海迪急忙夺门而出。斯鲁特向比尔传达了公使的指示。“我们越早动手越好,韦恩。 公使终于对这件事情热心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得趁热打铁。我们就座两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好吗?”
“我刚才和你的秘书约好出去吃午饭。”
“哦,我明白了。”
“确实,莱斯,我打算在这儿过夜,不过——”他给了斯鲁特一个男人对男人的会心微笑。“你不介意吧?”
“哦,就在我这儿作客好了。我们明天去。”。
斯鲁特立即听到邻室传来又一阵笑声。一个到手的标致姑娘比起在远处受罪遭难的成百万芸芸众生来毕竟更为重要;这是天性,永远也改变不了。
办公桌上早晨到达的邮件中有一份赫西博士寄来的正式报告,概述了亨利一杰斯特罗案件的情况。斯鲁特把它归进了一个标明是“娜塔丽”的卷宗夹子,然后把没写完的给拜伦的信撕碎。也许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从地中海沿岸的某一处领事馆传来,或许甚至从里斯本传来。坏消息则是不拘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的。
第三十七章
巴穆。弗莱德里克。柯比穿着一件衬衫,捋起袖子,坐在一张租来的旧办公桌前。这是一幢尘封垢积的办公大楼,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不远。柯比抓紧时间要在罗达坐火车到达之前完成一份报告。他心绪不宁,一半是为了对于这一次相见很担心,一半是因为凡纳伐。布什要寻根究底弄清事实真相,并且还挑出了报告中含混不清的地方。说实话,有关建造一座铀反应堆所需的纯石墨的来源问题,各方面的情况都是暗淡的。连天气也是如此。 八月里的这个下午,闷热阴沉,把窗子打开,吹进一股来自密执安湖的大风,灼热的程度不亚于沙漠地带的沙暴,再加上悬浮在芝加哥空气中的尘埃和废屑,黄沙扑面,也许够得上沙暴中的含沙量的一半;而把窗子关上,又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仿佛是穿着衣服洗蒸汽浴一般。
单单一个石墨问题便十足可以代表这项希奇古怪的事业的全貌,柯比博士如今朝夕与共的也就是这个事业。 关于铀的工作,原来进展缓慢,好如涓滴细流一般,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却已变成一道日升夜涨的大河纷至沓来的各种意见,大笔的资金,各方面的人员,成堆的问题,一切都得严守秘密。柯比在凡纳伐。布什主管的科学研究发展局的S—1室工作。知道内情的人都懂得S—l代表铀,可是对于所有的局外人,它等于是个零——他的一切麻烦,根子就在这里。他要搜求物资材料,寻觅建筑场地可就是竞争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