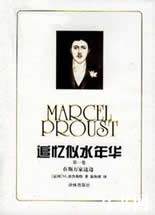战争与回忆-第1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咖啡馆里的顾客们当然只在来宾到场的时候才尽兴地喝咖啡、吃蛋糕,要不然他们就空做着喝棕色饮料和吃一盘盘蛋糕的动作,实际上那些蛋糕是他们所不能尝的。
已经一点过了。我干嘛老是这样沉痛地胡说八道呢?就连美化运动的冷酷玩笑也是一种宽慰,使人可以忘掉班瑞尔透露出来的情况,以及我为娜塔丽迟迟不回来所感到的焦虑。她六点钟非得起身。在她上云母工厂去干活儿以前,她得先到儿童游乐场和幼儿园去为这次访问排练。她跟几个其他的漂亮女人刚接下了这个任务。她们的工作都给她们安排好:训练孩子们讲述他们的小节目,并且装出十分快乐。午餐时她告诉我,孩子们得喊着说:“怎么,又吃沙丁鱼吗?”整整持续二十分钟的这种很容易识破的谎话,全给写了出来。在这方面,美化运动正产生出一些真正的好处,因为党卫军增加了孩子们的配给量。他们想要来宾们看到一些胖娃娃在玩耍,所以象女巫对汉泽尔和格雷特尔那样,正在填饱他们的肚子。
我无法相信这么显眼的一出喜剧能够欺骗谁。然而就算它成功了,德国人指望通过它获得什么呢?犹太人正在失踪,许许多多人不见了,这个恐怖万分的事件能够长时期被掩盖起来吗?我可无法明白。这件事毫无意义。不,这就象那个智力迟钝得可怕的孩子;那个智力迟钝、在空果酱罐旁边被人逮住的孩子,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抹得红彤彤的,还笑嘻嘻地不承认自己吃了果酱。
就这件事来说,它对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这细想了好几个星期,头脑都想得发昏了。 管德国人叫虐待狂、屠户、野兽、蛮子全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们象我们一样,也是男人和女人。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草草写下,比我所感到的要肯定得多。这件事的根子不可能是希特勒。我由这个前提开始。这样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德国人当中遭到了那么少的抵制,那么这件事必然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
拿破仑把自由和平等强加给了德国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压制它。他用大炮和践踏的军靴侵人了儿乎还没摆脱封建主义的一些拼凑起的专制国家,并以人类的同胞关系蹂躏它们。解放犹太人就是这种新的开明人道主义的一部分。这对德国人说来是不合乎人情的。但是他们却依顺了。
哎呀,我们犹太人相信了这一改变,可是德国人内心里却始终没改。这是征服者的信条。它支配了欧洲,但并没支配德意志。他们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猛烈抨击非德意志的启蒙运动,他们反犹太人的政党成长起来,同时德国一天天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可它始终没接受“西方的”思想。
他们在德国的皇帝统治下战败了,接下来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可怕的、绝望的愤怒。 共产党人威胁要制造混乱,推翻政府。魏玛政府分崩离析。当希特勒从这种女巫酿造的啤酒中崛起,象《麦克白》中一个神谕的鬼魂那样,然后在百货公司和歌剧院走廊中指着犹太人时;当他大声疾呼,说犹太人不仅是德国所受种种不公正待遇的明显的受益人,而且是造成这种种待遇的实际原因时;当这种疯狂的历史程式向前发展,跟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一样简单而虚假,可是又比那些口号更残忍、更直率时;德国人的怒火就在突然爆发的一阵民族活力与欢乐中发泄出来,而促使它发泄出来的那个花言巧语的疯子,手里却挥舞着杀人的武器。德国人毫无悔恨之心这一点,使这种武器到了这个人手里特别合适。要不是通过对我施加的暴力,我还不知道这种使人费解的特征。就连现在成对这仍然有点迷迷糊糊呢。
我对路德的研究有没有使这问题清楚一点儿呢?在希特勒之前,只有路德曾经用民族的声音那么透彻地讲话,使郁积的民族怒火完全发泄了出来,而就他来说,是反对腐朽的用拉丁文单调地宣讲的天主教教义。尽管我十分钦佩路德,是他的传记作者,可是这两个人的粗暴有力、挖苦讽刺的讲话却非常相似,这使我忧虑踌躇起来。路德的新教是一种宏伟的神学,一种恳切响亮、讲求实际的基督教,很配得上路德声称正从巴比伦的婊子手里拯救出来的那位基督。但是就连这个土生土长的产物,也沉沉地压在德国人的身上,是不是呢?
德国人在基督教欧洲始终不大自在,始终没拿定主意,自己算江达尔人呢,还是算罗马人,是北方来的破坏者呢,还是彬彬有礼的西方人。他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摇摆晃动,一会儿扮演这个角色,一会儿扮演那个角色。就他身上的江达尔人性格来说,基督教的悔恨之心和英国人与法国人的自由主义都是胡说八道;启蒙运动的理性与条理是人类本性的矫揉造作;毁灭与统治是实际所需要的;屠杀是古代的一种乐事。经过好几百年路德的约束以后,粗暴鲁莽的德意志声音在尼采的口中再一次大吼出来,对基督教温顺的教义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尼采十分精确地把这一大套宽厚仁慈和悔恨之心全怪到犹太教上面。他十分精确地预见到基督教上帝未来将灭亡。他所没预见到的是,获得自由的汪达尔人在精神错乱的工业化的报复中,竟会动手把一千一百万个基督钉到了十字架上。
暧,乱涂乱写啊!我又看了一遍用铅笔匆匆写成的这几页,我的心情感到沉重。我忽略了这份日记,这不足为奇;我的渺小的智力应付不了我如今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理论,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不对社会主义追本穷源,说明这两个运动如何集中到了希特勒身上;不给予俄国革命的威胁应有的重要性,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
在这一大篇随随便便的涂鸦中,我有没有真正接触到德国人呢?我这个卑鄙的犹太人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戴上了经匣,而他却用铿铿作响的部队和轰鸣的空军机群在欧洲各地出击;他和我实际上是不是都顺从着人类的同一种冲动,想要保全受到威胁的自身呢?他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想杀我,因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对原始的德意志精神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战、谴责和阻碍?再不然,这一切是不是一种无聊的妄自尊大,是不是一个毕生开明的人士疲乏过度的脑子的幻想呢?这个开明人士想在奥斯威辛,在美化运动中找出一点点意义,想在我自己和卡尔。拉姆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即使他杀了我,根据达尔文主义的分类,如果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的话,我们还是同胞。
娜塔丽回来了!
次日上午。
事情比我所想的还要严重。她已经深深地卷了进去,回来时人很疲倦,可是兴高采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些集会一直在辩论挫败美化运动的方法,他们想向红十字会的来宾暗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情,而又不使党卫军警觉起来。她认为他们已经想出了一种方法。在每一个停下来参观的地方,一个负责的犹太人对红十字会方面的任何评论都说出同一句预先安排好的答复:“哦,是的,这一切全是崭新的。还有不少可看的哩。”
我猜他们是经过不少争论和修改才把这方法制订出来的。他们逐字逐句表决。他们深信,这样一字不差地重复回答,会使来宾们觉得是一个信号。犹太人将随随便便地把这句话说出来,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色,可能的话在党卫军听不到的地方说。他们的希望——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幻想是,来宾们会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是崭新的、捏造的装置,而且因为“有不少可看的哩”这句话,还会走到安排好的路线以外去。
我耐心地听着。接下去,我告诉她,她正滑进犹太区特有的梦境中去,危及她自己和路易斯的生命。德国人是饱经训练、警惕心很高的监狱看守。来宾们将是温和殷勤的高级福利人员。美化运动是德国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应该提防的最为明显的事,正是犹太人向来宾泄漏秘密的这种计划。我这样辩论着,但是她反驳说,犹太人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进行还击。既然我们没有武器,只有头脑,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的脑力。
接下去,我采取了这个激烈的步骤,透露出班瑞尔揭发的奥斯威辛的情况。我的用意是使她大吃一惊,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她有被流放的危险。她当然十分震惊,不过并不是吓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种传说的确一直在四处流传。可是她并不是象我料想的那样接待这个消息。她说,那么更有理由该去唤起红十字会人员们的猜疑;再说,班瑞尔的消息好歹一定有点儿夸张,因为乌达姆收到了他妻子从奥斯威辛寄来的明信片,她的朋友也从二月遣送走的亲戚们那儿刚收到一些明信片。
我重复了一遍班瑞尔所告诉我的话:奥斯威辛的党卫军维持着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以防红十字会万一设法进行磋商,要求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参观的话;每个人到达奥斯威辛之后,全得写一些明信片,注明几个月以后的日期;而特莱西恩施塔特营则定期清除掉老的和小的、有病的和体弱的人,把他们用毒气全体毒杀,以便为特莱西恩施塔特进一步遣送去的人腾出地方。乌达姆无疑正收到一个已经焚化了的女人的信件。
接下去,她很肯定地讲,她的团体通过布拉格传来的小道新闻听说,根据德国军方的情报,美国人已经决定五月十五日在法国登陆。这很可能会在欧洲各地激发起起义,导致纳粹帝国的迅速瓦解。总而言之,党卫军军官就会为自己的脖子发愁担心,那么进一步的遣送就不大可能会进行了。
面对着这种已经变为错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法进行辩论。我劝告她,如果她打算把这件事搞下去,至少传话给班瑞尔,把路易斯弄了出去。这话她不肯听;她不承认她正在使路易斯陷入比他已经面临到的更大的危险;后来,她变得十分急躁,于是走去睡了。
这不过是几小时以前的事。她醒来后,情绪好点儿,为自己表现出的暴躁向我道歉,然后出去了。她一句没再提路易斯的事,我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她新发现的犹太复国主义,只有为这感到高兴。就她来说,这似乎是维护受到威胁的自身的途径,正象我在从前的宗教信仰中所找到的那样。一个人倘若不是一个同谋者或是一个黑市商人,在犹太区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点儿这种倔强精神。但是假如她的团体里混进了一个告密的人,那可怎么办?何况利用木偶破口烂骂一事已经载在党卫军那儿她的档案上,那样一来就会是她的结局。
我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把犹太人送回不友好的阿拉伯人居住的中东那片荒地上,我对这一见解依然极其怀疑。不错,当欧洲这场浩劫还不过是象人的手那么大的一团乌云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确就预见到了。但是这么一来,他们提出的梦幻般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可行的或正确的办法吗?不一定是。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只有极少数梦想家曾经到巴勒斯坦去。就连他们也是被迫害屠杀驱逐到那儿去的,并不是因为那片干旱的圣地吸引着他们。
我承认,现在我对这件事,或是对我先前的任何见解,全不十分肯定了。当然,犹太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表明自己身份的手段,不过我把民族主义看作是现代的祸根。我就是不能相信我们可怜的犹太人竟然计划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拥有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一个议会和一些部长,还有疆界、海港、航空港、大学等等。这是多么美妙和空虚的幻想啊!让娜塔丽这样幻想着,如果这可以帮助她熬过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这场苦难的话。她说,倘使有一个象列支敦士登那么大小的犹太国,那么所有这些恐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又说非得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来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这是救世主的语言。我所担心的只是,这种新的热病般的激情会战胜她通常有的强韧的判断力,也许会使她轻率行事,结果毁了她自己和路易斯。
第七十九章
隔着关闭的卧房门,那声音听起来就象是哭泣,但是罗达难得哭泣,因此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朝前走到客房里去,他如今就睡在那儿。时间已经很晚了。晚餐后他在书房里坐了几小时,为自己跟彼得斯上校的会面起草一些登陆艇文件。这是件他并不怎么想干的事,但是关于优先权的冲突迫使他不得不干。他脱下衣服,洗了个淋浴,把临睡前喝的一杯搀水的波旁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后临上床前又到罗达房门口站住脚听听。声音已经变得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