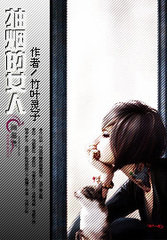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位母亲突然阴沉而疑『惑』地盯着他,好像他并没有说实话的样子,“什么叫不当回事?”她严厉地问道。
“确实有很多人不像话。”他回答,不得已地继续谈下去。“他们叽叽喳喳、格格傻笑。别当他们在那儿就好得多了!实质上,他们并不存在,他们并没有在那儿。”
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紧盯着他。
“是啊,我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她尖刻地说。
“没什么好想的,这就是他们不存在的缘故。”
“好!”她说,“我也不愿往那儿想,不管他们是否存在,他们在那里,只是我知道期望我去认识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谁都不能因为他碰巧来了就期望我去认识他,我只要转开身,他就等于根本没有出现。”
“完全正确。”他回答。
“难道不是吗?”她又问道。
“正是。”他又回答,接着一阵短暂的沉默。
“只要他们在那儿,我就厌烦。”她说,“我有好几个女婿,”她自言自语状地说,“现在劳拉也结婚了,又是一个女婿。我真是分不清谁是约翰谁是詹姆斯。他们走过来叫我妈妈,我知道他们将说什么,‘妈,你身体好吗?’我应该回答‘从任何意义上讲我都不是你们的母亲。’但又有什么办法,他们在那儿。我有自己的孩子,我能从别人的孩子中分辨出谁是我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好象忘记了自己是在跟他说话,忽然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她有些恍惚地环顾了一下房间。伯基猜不出她在找什么、想什么。很显然她注意到了她的几个儿子。
“我的孩子们都在吗?”她突然问。
他笑起来,有些吃惊,可能还有些害怕。
“除了吉拉尔德之外,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他回答说。“吉拉尔德”,她大声说,“他是他们当中最不像话的一个,你现在也决不想再看到他一眼,对吗?”
“是的。”伯基说。
这位母亲目光有些呆滞地盯着她大儿子看了半天。
“唉”她令人费解地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股很重的挖苦味道。伯基感到害怕,好像他不敢去领悟。克瑞奇太太走开了,把他忘在一边。马上她又回来了。
“我希望他能有个朋友”她说,“他从来没有过深交的朋友。”
伯基看了看她那注视着他的蓝『色』的双眼,他看不透它们。“难道我是我兄弟的看守员吗?”他近乎粗鲁地自言自语道。
然后,他稍稍吃惊地想起来了,那是该隐的喊叫。吉拉尔德如果是什么人物的话,那就是该隐。有些事完全属于意外,即使是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后果也不应该由当事者负责承担。在小时候,吉拉尔德出于意外杀死了他的弟弟,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当事者的生命中就会被画上污点,到死都洗不掉呢?一个人可以在意外中生存,也可以在意外中死亡。吉拉尔德不也是这样吗?每个人的生活不都是存在于偶然事件吗?难道只有种类、种族、种属才能产生普遍的联系吗?难道世界不存在什么偶然事情?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着普通意义吗?真有吗?伯基站在那儿一直在思索。他把克瑞奇太太给忘了,就象克瑞奇太太忘了他的时候一样。
他不相信有偶然事情存在,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克瑞奇的一个女儿走过来说:
“您不想过来把帽子摘掉吗?亲爱的妈妈。我们一会儿就要坐下吃饭了,而且是个正式的场合,亲爱的,是吗?”她挽起母亲的胳膊,然后走开了。伯基马上就跟他身边最近的一个人说话。
午餐的铃声响了。男人们抬起头来看着,但都没有移动,屋子里的女人们似乎不觉得铃声对她们有什么意义。五分钟过去了,年老的男仆克罗特有些愤怒地出现在门口,他寻求帮助似的看着吉拉尔德。吉拉尔德从书架上顺手拿起一个大螺号,旁若无人地大声吹了起来。这是一种很怪的震慑人心的声音。这召唤声有很大的魔力,大家都好像听到什么信号似的快步走过来,蜂拥至了餐厅。
吉拉尔德等了一会儿,是想让他妹妹做女主人,他知道他母亲决不会关心自己的职责的。但他的妹妹只是自顾自地挤到自己的座位上。因此,这位年轻人只好自个儿指挥着客人们就座。当人们都在注视着递来传去的餐前拼盘时屋子里出现了一会儿平静。在这静寂之外传出一个十三四岁长发披肩的小姑娘从容镇静的声音。
“吉拉尔德,你在吹那该死的螺号时,你把父亲给忘了。”“是吗?”他回答,然后对大家说,“父亲躺下了,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到底怎么样了?”一个已婚的女儿问道,她的眼睛却在看着那块高耸在桌子上的结婚大蛋糕,蛋糕上的假花正在往下掉。“他没有什么病痛,就是有些累而已。”威妮弗雷德说道。——这就是刚才那个长发披肩的小姑娘。
酒斟好了,大家便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头发卷曲的母亲坐在桌子的最上端,伯基坐在她旁边,她不时地将身子向前拥去,用尖利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不时对伯基低语。
“那个年青人是谁?”
“我不知道。”伯基慎重地回答道。
“我以前见过他吗?”她问。
“我想没有。我没见过。”他回答说。然后她就满意了。她疲倦地闭上眼睛,安详的神情流『露』脸上,就像是一个安息的皇后。接着她醒过来,脸上泛着笑容,像一个开心的女主人。她很有礼貌地屈身,好似对每个人都表示欢迎,很是高兴,可阴影又回到她的脸上,『露』出老鹰一般的神『色』,她好像一头野兽陷入了困境中,斜视着人们,对他们愤恨之至。
“妈妈”,黛安娜,一个比威妮弗雷德大点的漂亮的姑娘对她说,“我想喝点酒,可以吗?”
“是的,你可以喝。”母亲有些机械地回答说,因为她并不介意这个问题。
于是,黛安娜就让仆人给她倒酒。
“吉拉尔德不应该限制我。”她很平静对在坐的每位说。“好吧,黛”。她哥哥和蔼地说。她喝着酒,有些害怕她哥哥。屋子里大家无拘无束,几乎要混『乱』不堪了。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反抗。吉拉尔德不是凭授与他的地位而是凭着自己的感召力在发号施令。他的声音有些特别,和气又透出支配的力量,能把比他小的年轻人震住。
赫米奥恩正在和新郎就民族问题进行讨论。
“不,”她说,“我认为呼吁爱国主义是一种错误,这就像一家生意人和另一家进行竞争。”
“可你也不能完全说成那样,对吗?”吉拉尔德说道,他很喜欢和别人争论。“你不能把种族和做生意相提并论。是吗?——而且民族种族相关,我认为,我认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一阵子缄默。吉拉尔德和赫米奥恩之间总有一种奇怪又不失礼节的敌意。
“你认为种族和民族相同吗?”她思索着问道,面带木然和踌躇。
伯基知道她在等他发表意见,便很有责任感地说道:“我认为吉拉尔德是对的,种族是民族的重要成分,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
赫米奥恩又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盛气凌人似乎要把局面搞到僵持的地步。
“是的,即使是这样,呼吁爱国主义难道是人们本能的一种要求和呼吁吗?更确切地说,它难道不是想占有财产的这种本能的要求吗?这种商业的本能的要求吗?这岂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含义?”
“可能是。”伯基说,他认为这场争论不合时宜。
可吉拉尔德开始准备迎战。
“一个种族可能有着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也是必然要有的。它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必须要准备粮食。为了准备这些粮食,你就必须和别的家庭,别的国家进行竞争。我真看不出人们不这么做会有什么法子。”
赫米奥恩再次停顿了片刻,在回答以前就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不,我认为无论何时激起人们的争强好胜心总是不太好的,人们会互相仇视,而且越来越厉害。
“但你不可能完全消除竞争『性』。”吉拉尔德说,“这对刺激生产和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不”,赫米奥恩又说,“我认为人们可以消除它。”“我必须说,”伯基说,“我讨厌竞争精神。”赫米奥恩咬了一口面包,同时用双手慢慢把面包从牙齿间拿出来,缓慢而又带着嘲讽。她转向伯基。
“你的确是恨它,的确。”她亲切而感激地说道。
“是讨厌。”他重申。
“是的。”她放心又满意地自语道。
“但是,”吉拉尔德坚持道,“你不愿意让一个人夺走他邻居所用以生存的东西,那为什么又愿意让一个国家抢走另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呢?”
赫米奥恩咕咕哝哝了好一阵子,然后才简单而不在乎地说:“这并不总是一个财产问题,对吧,这不完全是商品的问题吧?”
吉拉尔德对她的说法很感气愤,因为她暗示他的说法是庸俗唯物主义。
“是的,或多或少吧!”他反驳说,“如果我把一个人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那顶帽子就成了人类自由的象征,当他为帽子而战,那么他就是为了自由而与我战。”
赫米奥恩有点尴尬。
“是的,”她气愤地说,“但是由假想的例子来争论并不能真正地说明问题,并不会有人来把我头上的帽子摘掉是吧?”“只是因为法律阻止了他。”吉拉尔德说。
“不只是法律。”伯基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想法上的问题。”吉拉尔德说。
“或者说帽子的问题。”新郎笑着说。
“如果他真想要我这样一个帽子。”伯基说,“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决定哪一部分对我的损失更大,要帽子还是要我的自由。如果我被迫做出决定,那么我就失去后者。重要的是哪一个对我更有价值,要么选择令自己高兴开心的行动自由要么选择我的帽子。”
“是的,”赫米奥恩奇怪地望着伯基,“是啊。”
“但你想让别人从你的头上摘下帽子了?”新娘问赫米奥恩。这个高大的挺着脖子的女人把脸慢慢地转过去,好像这位新发言者给她灌了麻『药』似的。
“不,”她用一种低沉狠毒的声音说,声音中好似带有笑声,“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头上把帽子摘掉。”
“你怎么来阻止呢?”吉拉尔德问。
“我不太清楚,”赫米奥恩慢慢地回答说,“可能我会杀了他。”在她的口气中有种奇怪的笑声,举止里也透出一股危险又令人信服的幽默。
“当然,”吉拉尔德说,“我可以看出伯基的观点,这是个关于帽子和心情平静哪个重要的问题。”
“是身体平安。”伯基纠正说。
“好吧,随你便。”吉拉尔德回答说,“可在此事上你怎么来为一个国家做出选择呢?”
“上帝保佑我!”伯基笑道。
“是的,但假设你必须做出决定呢?”吉拉尔德坚持说。“都一样的。如果国家的头顶上是顶五先令硬币的旧帽子,那就让那些偷偷『摸』『摸』的绅士拿去好了。”
“可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能是一顶帽子?”吉拉尔德依然坚持说。
“我想那一定是。”伯基说。
“我可不敢肯定。”吉拉尔德说。
“我不同意,鲁伯特。”赫米奥恩说。
“好吧。”伯基说。
“我宁愿选择国家这项旧帽子。”吉拉尔德笑道。
“你戴它就像傻瓜。”他的那个仅有十几岁的妹妹黛安娜冒失地说。
“哎呀,我们净谈了旧帽子的事了。”劳拉·克瑞奇喊道,“别谈了,吉拉尔德。我们就要祝酒了,我们来祝酒吧。碰杯——碰杯,来,来,祝词吧!”伯基考虑着种族和国家灭亡的问题,盯着他那充满了香槟的玻璃杯,气泡在杯中破碎。斟酒的人退走了。伯基看着已倒好的酒,突然觉得口渴了,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屋子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微微紧张的气氛,他警觉到了,感到有点不安。“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故意这样做的?”他扪心自问。于是他含糊地认定,他是“无意中地故意”这么做的,他转身看着身边那雇佣来的仆人,那仆人冷漠而又悄悄地走开了。伯基觉得自己讨厌干杯、讨厌仆人,讨厌聚会和所有的人。然后他站起来,准备祝词,但内心有些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