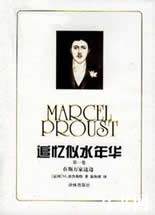惜白华-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人一路走着,走到一半,霍鋣却是停在了小山丘的半山腰上,又十分悠闲的坐了下来,东方绾也不知这位尊神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灵丹妙药,于是她便只站在霍鋣身后没有上前。
霍鋣见她愣在自己身后没动便又拍了拍自己身旁的空地示意让她坐过来。
东方绾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又乖乖地坐了过去,两人就这么坐了好一会,霍鋣也始终没有开口来教诲她,东方绾也是觉着奇怪,想着这位“爷”许是睡着了,也是,连自个儿叫学生下学留下都能转眼便忘记,竟跑去品什么茶、下什么棋,睡着对于这位“爷”而言许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样想着东方绾便轻轻唤了一声“先生”,心里想着若是霍鋣不应声,她便可以悄悄离去,次日再碰见他便与他讲:“昨儿个先生许是讲学疲累,学生虽也很想听听先生的教诲但却是着实不忍打扰,于是便自己离去了。”东方绾觉着自己的这套说辞简直就是天衣无缝,诚然是找不出任何破绽的,可不料她这声“先生”刚唤出口,霍鋣就应了一声“何事?”
闻声东方绾一急又找不到别的话搪塞,于是就又犯了她的老毛病,行事说话不经脑子的老毛病,与其说是不经脑子,倒不如说是与人打架养成的习惯,所谓先下手为强,三思而后行什么的等打完再说也不迟。她说的是:“先生,你为何叫‘爷’?这名字是不是有些略……粗俗了……”
霍鋣看了一眼东方绾,缓缓地:“把手伸出来。”
“伸手?完了完了,这下恐怕是躲不过了,都怨自己这不灵光的灵台”东方绾心中这般想着,因为这情景于她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每每她惹出了什么乱子亦或是在秦夫子讲学中“小睡”时,秦夫子就会拿他那把厚厚的戒尺重重的抽打她的手掌心,然后第二天她那只原本纤细柔软的玉手便会肿的像她爱吃的豆包一样“珠圆玉润”。
但事已至此,她已是无力回天,只好巴巴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等待着灾难的降临,一边忧伤的感叹一边在心中叨叨着:“若是右手打肿了,往后先生布置的课业便可以以此为由推脱掉了,怎么着也不能白白的让这手变成豆包。”
可未料到的是,霍鋣并未拿秦夫子那把厚厚的戒尺抽打她的手掌心,只是一只手轻轻地握了她那只柔软的小手,而另一只手正在她的手掌上一笔一划的写着什么字。
正当东方绾捉摸着霍鋣究竟在她手上写了个什么字的时候,一阵凉凉的微风拂过,吹起霍鋣未被束起的墨丝,那墨丝掠过东方绾的脸,让东方绾觉着很痒,于是她便想抬头瞅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脸上飞来飞去,可她方一抬头便撞上了霍鋣那双漆黑的眸子和他那张俊朗得不可方物的脸,又恰逢日落西头,那映在霍鋣脸上晕晕的余晖和他那被风轻轻撩起的墨色长发,看得东方绾有些愣了神,就连霍鋣身上那股淡淡的墨香也是那般的好闻。
东方绾一向喜欢生的好看之人,无论男女,就如她刚来东来书院那会子就与安觅、秦忆她们颇为亲近一点,只因了她们二人皆是一等一的美人,至于子见嘛,虽说生得也是不错的,可总是那么一副怨妇般的脸,活生生地就像个嬷嬷,所以总是不受东方绾待见的,可霍鋣这张脸,即使总是冷冰冰的也还是十二分的好看,唉,这世间恐怕是没有哪个女子与这样一张俊朗的脸离得如此之近还能够“坐怀不乱”的了。
“先生,你生的可真好看。”方才说完这句话,东方绾就想抬起手来打自己一个巴掌,一来是为了让自己这不怎么灵光的脑子清醒清醒,二来是为了让自己长长记性,这种说话不经脑子的毛病她犯了已不是一两次了,每每她“犯病”时总会在心里说“下次要留心,下次留心便好。”可每每她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
霍鋣微微牵了牵嘴角,似是想着些什么道:“你初见我时,也说过这样的话。”
此刻此时的东方绾正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因此也并未听清霍鋣说了些什么,好一会儿回过神来才又愣愣的应了声“啊?”随即又反应过来这个“啊”字貌似有些过于随意了,于是就又恭敬地补了句:“先生,你方才与学生说了什么?”
霍鋣似是有些无奈:“无事。”
东方绾见他这般无奈的模样,便再也没敢吱声,只在心中想着,这位尊神许是觉着自己已经是一块朽木,别说是雕就是劈怕也是劈不开了。
二人又是半晌无言,直到日隐于山霍鋣才又开了口:“你可以离去了。”
“真……,可先生还未罚学生,学生在讲学时睡着实属不该。”东方绾口不应心的说着,可心却早已是飞腾到了九霄之外。
霍鋣笑了笑,看着东方绾:“怎么,你想让我罚你?”
“不……不……”此时的东方绾也不晓得该如何回话才是,一是她万万没料到霍鋣会如此问她,若是换作其他先生肯定只会道一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继而便让她离开了;二是,霍鋣笑起来实在是好看,让她忍不住的想要多瞧那么几眼,因而此时她的脑子并不像平日里反应的那般灵光。
霍鋣见她支支吾吾,半天不语,便又笑道:“今日见你与我说话时有走神,想必是等我许久有些乏了,依你这性子,往后要受罚的地方怕是少不了,若每次都要我来罚你,我也着实是累得很,惩罚我先与你记上,等哪次我得了空一并罚你便是。”
“……”东方绾无言,只觉着自己着实是多此一举而这先生也着实是凶恶万分,想来这两个月自己并不会好过便是了。
作者有话要说:
☆、勤问堂
第二日一早,安觅方一走进学堂就瞧见东方绾没精打采的趴在书桌上,“绾绾,你怎么了?”
见是安觅,东方绾懒懒地的应了声:“无碍,吾只觉心生疲累。”
安觅一听便着了急,一边拉过东方绾的手一边将她那只手翻来覆去的瞧着:“怎的,那个霍鋣尊神罚你了,手又肿了么?”
“我听说那先生还要在此处呆上两月。”东方绾还没来得及回安觅的话,子见便抱着一摞红木盒子呼哧呼哧地从屋外走了进来。
见子见抱着那一摞不知装着何物的精致盒子,安觅奇怪地问他:“你那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今早碰见秦夫子,他让我把这些劳什子的东西搬到学堂里来,真真是累死我了,虽然我生得高大威猛、玉树临风,可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啊!”
“……”东方绾和安觅二人一时无言,果然与司徒川走得近的人最终都会落得个自恋到无法自拔的下场。
见她两不说话,子见又继续道:“对了,听秦夫子说,那位霍鋣尊神原本只打算在东来书苑讲学一日,可昨儿个不知因了什么缘由,突然与秦夫子说要在此处多留两月。”
“这是为何?”闻言安觅是颇为的不悦,要知道这多了一位先生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份课业。
“我也不知,但听秦夫子说,尊神许是为我们东来书苑勤勉上进的学风所打动了。”子见对于这位新来的先生倒是无甚感想。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儿,其他学生们也皆已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学堂里,而随着学生们一并走进来的还有满面春风的秦夫子,他方才一脚迈进学堂就颇为得意地对众人道:“大家且先坐下来,我有话要与你们讲。”
以往,秦夫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定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么是有课业要么是有小考,还有一次竟是要他们去农间种田,谓之:身体力行,事必躬亲。所以,一听见这话,东方绾和安觅就颇为不悦。
秦夫子满面春风:“大家可都瞧见了那四个红木盒子?”
“……”偌大的学堂里学堂里无一人应声,看来不悦的并不仅仅只有东方绾和安觅。
见无人应声,秦夫子又自顾自地继续说着:“你们可知那些盒子里装的是何物啊?”
“……”整个学堂里依旧无人想要理睬秦夫子,恐怕这整个学堂里心中甚为欢喜的也只有秦夫子一人而已。
“咳……”秦夫子清了清嗓子,郑重继道:“此乃九天玄女所制的琥珀荷叶酥。”
一听这话,学堂里的学生们个个皆是惊异不已,天界人人都知道这九天玄女所制的糕点乃是天界一绝,且这九天玄女生性清高,天界诸神也只有在西王母娘娘的寿宴上才能有幸得以一尝,而至于这九天玄女为何会如此厚待秦夫子,其中原委便也是因了这九天玄女也曾是这东来书苑的学生,自然也是受过秦夫子不少的教导。
此刻众人的目光皆已是齐刷刷地落在了那些个红木盒子上,尤其是安觅,她早已是死死地盯住了那些盒子,仿似随时准备进入一场“大战”之中,而就在众人都按耐不住的当儿,唯有一人依旧是“正襟危坐、处变不惊”,那人便是魔族帝姬东方绾,因为她压根就不知晓这九天玄女是何人,更不用说这什么琥珀荷叶酥了。
见众人如此吃惊秦夫子很是满意的捋了捋自个儿的胡须又继续道:“我今次要把这四盒糕点赠与二人,这二人可谓是我东来书苑众生的榜样。”
安觅不屑地轻哼了一声,小声叨叨着:“左不过是奖励给那些念书勤勉上进的学生,唉,吃不到糕点了,这可真真是天妒英才”
安觅方才叨叨完,秦夫子却是出乎意料的开口道:“安觅,东方绾,这些糕点便赠与你们了。”
听见此话东方绾、安觅二人皆是一惊,不明所以的互相对望了一眼,而后皆是以同样不解的眼神望向秦夫子。
见东方绾和安觅皆是满脸的疑惑,秦夫子则是十二分怜爱地望着她们,问她们道:“你们可还记得你们在勤问堂做了些什么?”
勤问堂,她们自然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三重天西面除了东来书苑还有好些个其他的学堂,譬如什么尚学书斋,五味书苑等等,于是这些个学堂里的先生们商量了一番,在途经几个学堂的路上设了一个勤问堂。
所谓的勤问堂,讲的便是一个“问”字,凡是学生们有什么不解之处皆可以在这勤问堂里写下,路过的先生们或是其他有见解的学生们均可在此为人解疑答惑,而至于东方绾和安觅在这勤问堂里干了些什么事她们两自然也都是心知肚明,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依她们俩这性子,这事儿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助人解惑、与人为善的好事儿。
这说来又是话长,自从这勤问堂设立之后,倒真是有不少勤勉上进的学生们在此地将自己在课业上的不解之处一一陈词于书,而东方绾和安觅这两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却是来此处以捉弄旁人为乐的,说白了,也就是对于旁人所提出的疑惑乱说一通,但她们这乱说却也是讲究学问的,就算是胡言乱语也要胡言得令旁人深信不疑。
譬如,有一个尚学书斋的学生想作一首诗来赞颂自己的夫子,但惜这位兄台的文采着实令人“难过”,才刚写了开头就不知该如何继续接下去,那诗的开头如此写道:世间只有夫子好,其爱无私又崇高。于是东方绾便发了“善心”接了下句:有夫子的学生,课业少不了;有夫子的学生,处处是烦恼;有夫子的学生,手肿似豆包。
转而就到了第二日,东方绾发现诗的下面多了一行字,其写道:恕我冒昧,此诗是否略有不妥,不仅字数与我前句长短不一,而且不仅不像是在夸赞夫子反而更像是在贬低夫子,且恕我愚昧,这最后一句又是何意?
东方绾见此便又回了他:正所谓意不随形,意乃诗的最高境界,若诗皆讲究字数一致、形式一致,又岂可道出真心实意?而此诗看似是在贬低夫子,实则是欲扬先抑,若夫子不如此苛待学生,学生又怎会勤勉,而夫子着实是可怜,如此用心以助学生却还要被说成是苛刻之人,然,夫子为成学生之名而不惜牺牲自己之名,良苦用心至此,诚天地可泣啊。
转而又过了一日,只见诗下写着:原是如此,兄台用意颇深,在下深感受教,今次我便将此诗呈予夫子,也好让夫子同乐。后来,便再无后来了,东方绾也并不晓得那位兄台如今过得如何,但想必他也并不十分好过。
就在东方绾和安觅深感疑惑以及惶恐之际,秦夫子又继续得意而怜爱的说了:“有好些个学堂里的夫子们都说经常瞧见你们在勤问堂里为人解疑答惑,而且一呆就是一两个时辰,学堂里的夫子们皆是对你们大加赞赏,人人都说我们东来书苑的学生不仅勤勉上进连品格也是如此的高尚。”
见着秦夫子那满面春风又对她们一脸怜爱的样子,东方绾和安觅自是哭笑不得,使劲地憋了笑,这天下竟有这等好事,真真是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秦夫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