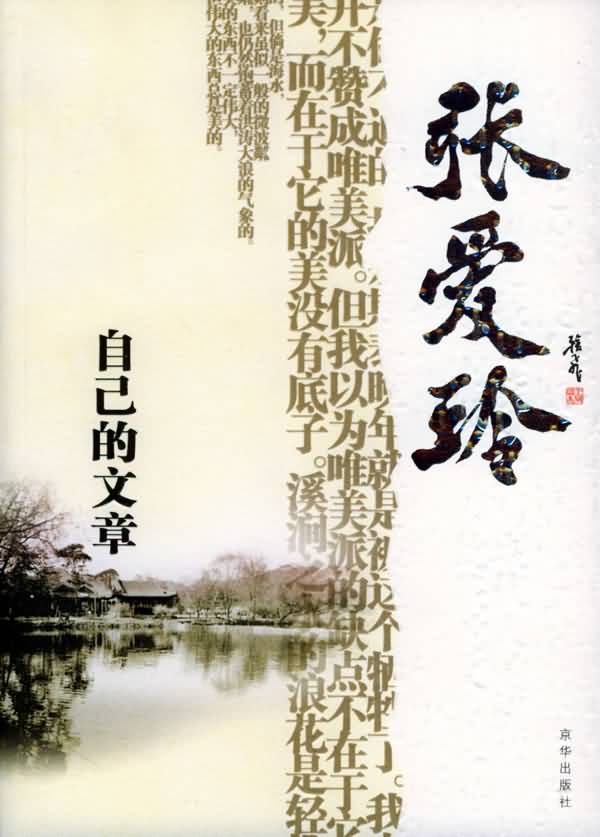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8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红潮简直溢出了严壮父满脸的黑胡碴子。段德昌替他解了窘。说:“听说柳女士与方焕作了斗争,来投奔红军,严师长还不想要,你不要那我要。”
贺龙说:“胡来!怎么不要?革命力量愈壮大愈好。严师长,留下柳女士。”
严壮父立正,说:“是,军长。”
柳真清留在了鸡鸣村。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柳真清住在了一户名叫马有良的富农家里。马有良两夫妇加一个女儿过日子。儿子成家后另立了门户。本来苏维埃的工作同志们希望柳真清与贫农同住同生活,一来是贫农没人敢请这么漂亮洋气的柳真清同住,二来柳真清多少也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愿意住一个干净宽敞些的家庭。马有良的家庭很符合柳真清的愿望。另外也不违背政策,马有良夫妻是有名的勤劳能干人,靠勤劳能干发的家,算不上土豪劣绅。
每日里粗茶淡饭,睡的是土布卧单,忙的是干革命办平民教育,看到的是一张张信赖人尊重人的朴实笑脸,柳真清的身心都十分舒展,十分快乐,倒还比在沔水镇白胖鲜润起来。
红二军第十八师就驻扎在鸡鸣村背后。当严壮父明白柳真清果真留下来之后,以为她是来从军的。
柳真清问:“女兵要拿刀枪杀敌人吗?”
严壮父说:“当然。但一般不需要。一般女兵当军医。”
柳真清说:“军医更是天天看见血,我不行。”
“那你做什么工作呢?”
“我办平民教育呀。”
“你还是教育救国论。还是一杯温开水。”
“我只会办教育嘛。我看教育就是重要。你我不受教育,会懂革命道理?还不只会做小姐少爷。”
一番争论,柳真清赢了。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持她的建议。方方面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所茅草做盖,泥巴做墙的平民学校在鸡鸣村诞生了。
柳真清请严壮父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列宁学校。
鸡鸣村的穷苦孩子全部免费上了学。柳真清给小学生开了国语,算术以及地理课。自编教材。废除了开口就背三字经的陈旧教学方式。同时,列宁学校还是贫民夜校。柳真清夜晚教贫民们识字,读书,唱革命歌谣。尤其是柳真清唱的歌谣,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风靡了整个江汉平原甚至传到了鄂豫皖边区。
至今都有人清楚地记得那些歌谣。之一是《诉苦歌》:
辛苦一块田,死活奔一年,粒粒来粮血汗换,
农友呀,地主(他)来吞占。
之二是《贫农歌》:
贫农真可怜,缺油又缺盐,勤扒加苦做,
无吃又少穿,日子似黄连。
之三是《妇女解放歌》:
叫声我姐妹,不要把急着,黑暗地狱努力来打破,
再走光明道,姐妹才快乐。
柳真清还固执地脱掉了仆妇的服装,穿上了自己的旗袍,脖子上扎一条白丝绸围巾。她认为一个教书先生应该拥有整洁端庄文雅的外表。严壮父担心柳真清招来非议,却不料大家都喜欢看她这副打扮,鸡鸣村的农民则引以为荣,在别的村里十分自豪。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柳真清的名气几乎与严壮父同等了。
严壮父这一年在全力以赴搞土地革命。不停召开各种会议,起草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拟定各种计划,有了战事则立即率部奔向战区,以确保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土地革命顺利进行。
他们各自忙着各自的工作,常常在路上擦肩而过却没工夫停下来说几句话。柳真清趁人不注意便给严壮父送去一个顽皮的笑脸,意思是当初你还不要我呢,现在我干得怎么样?
柳真清和房东马有良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融洽的日子一长,他们就势必关心起柳真清的婚姻大事。常敦促说:“柳先生,你该成婚了。”
柳真清就抿嘴笑。问:“和谁成婚?”
“和严师长呗。是不是你们还缺个媒人?”
柳真清说:“我不知道缺什么。”
柳真清无法诉说。无处诉说。有许多夜深入静的时候,柳真清想念着近在咫尺的严壮父,可她知道他正在忙工作,他不会来看她。严壮父只有剑胆,缺的是琴心;只有侠骨,缺的是柔肠。这深刻的遗憾使得柳真清从不主动对严壮父表示她需要什么,她倒想等着看看严壮父何日向她求婚。难道他不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男人吗?
8
我们后人研究历史,总是非常之认真,非常之郑重,然而历史却自然潇洒,常开玩笑,令人为之瞠目,为之结舌。正当洪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成功,土地革了命,严壮父等一大批革命者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按繁复的政策文件条款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词堂、庙字、教堂等等,又按同样繁复的政策文件条款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工人、退伍士兵、土豪劣绅家属、无反动嫌疑者、富农、地主——总不能地主一点地也没有;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所有种田人都举起了犁耙准备大忙春耕生产,严壮父也准备睡它两夜好觉之后去找柳真清,向心爱的姑娘表达衷心的歉意。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一批肩负改造苏区党和红军重任的党代表奔赴基层。啸秋是湖北人,就被派到了湖北,某一日,一路顺利到达洪湖。
这天傍晚下了一阵细细的春雨。柳真清感觉有些凉,便戴上了一条湖蓝色丝巾去列宁夜校上课。来苏区之后,柳真清不但没有穿上草鞋,让腿上滚一些黄泥,反而比从前讲究了许多。她希望严壮父总看到一个漂亮的她。她漂亮吗?严壮父从来没评论过没赞赏过,似乎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一样毫无审美意识。柳真清不相信严壮父真的忘记了美。
柳真清深怀着这种不合时宜不可告人的遗憾沿着湖边小路去工作。工作是愉快的,是可以令人忘忧的。现在夜校学生爆满。外乡的许多青年农民步行三四十里路赶来听课。
柳真清一进教室,教室里立刻掌声雷动。柳真清微笑着做了个请安静的手式。
“现在我们上课。”她说。
学生中有人喊了一声:“我们要唱歌。”
课堂零零落落地呼应道:“对。我们要唱歌。”
“今天我们的课程应该是识字。”柳真清沉静地扫视着课堂,说:“谁要唱歌?站起来让我问个道理。”·
农民们嗤嗤窃笑,没人敢站出来。夜校初开时,学生基本是鸡鸣村人,都指望学习认字,以后不受人哄骗,上起课来又认真又憨厚,根本不敢老盯着柳先生的脸。时间一长,柳真清的名气一响,四里八乡的人都慕名而来。虽然列宁夜校只收贫雇农,可贫雇农毕竟也是良莠不齐,许多人因为懒,因为赌而贫困,穷了之后便娶不上媳妇,光棍一条,做人家的雇工,流痞习气学了不少。他们来报名上夜校,政策上拦不住。其实上夜校就是为了看柳真清,每逢教唱歌,课堂上便有人眼睛瞪得像猫一般放绿光。
柳真清出身豪门,本来就是在改造自己,贫雇农当时是苏区最红的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柳真清不大好批评指责他们。也不敢向上面反映,怕消息传到严壮父那里给他添麻烦。
有两次放学路上柳真清受到了骚扰,房东马有良就常在半路上接她回家。马有良家劳动力少,他农活太忙,柳真清想了个办法:带上迷糊。迷糊是只看家狗,对柳真清很不错。只是在春季把握不住自己,闻到母狗的气味就忘记了职守。这天柳真清出门也是唤了迷糊的,还没走到湖边,树丛里有母狗哼卿,迷糊就毫不犹豫冲进了树丛。为此,迷糊屡遭马有良呵斥,还剁下了它的一截尾巴埋在堂屋里。可效果并不明显。
不过,光棍也罢,迷糊也罢,所有这一切烦恼都抵不上新生活给柳真清的快乐。新生活使她自信自强,她懂得干事业是会有些小困难的,她不怕。
柳真清的严肃压倒了教室里的歪风邪气。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窮”字。
“农友们,这个字念穷。穷苦人的穷。穷——”
农民们跟着念:“穷。穷。穷。”
“看这个窮字,上头是个穴,穴就是石洞,土室。下面左边是个身,指人的身体。右边一个弓,弯腰的意思。一个人住着弯着腰才钻进的石洞,他没有房子,这就是穷。然而,地是我们穷人开,屋是我们穷人盖,树是我们穷人栽,我们为什么没房子?为什么受穷呢?”
哗地又是一片掌声,许多农民拍着脑袋,茅塞顿开的样子。
教室的掌声停下之后,教室门口的一个掌声却依然热情地鼓着。柳真清提着马灯到门口一看,马灯差点脱手摔掉。是啸秋。
啸秋依然鼓着掌,朝柳真清亲切地微笑着。
“啸秋!你是啸秋吗?”
“我是啸秋。真清,继续上课吧,农友们等着你呢。”
“可是啸秋,你怎么来了?”
“待会儿你尽情地问。现在请允许我进教室听课,你的课讲得真好!”
啸秋进了教室,挤在农民中间坐着。柳真清重新开始讲课。她发现啸秋一直用手托着下巴仰望着自己,一动不动,聚精会课,仿佛进入无人之境。
9
一连四个夜晚,啸秋在开完会之后都赶来接柳真清,送她回去。他们慢慢向前走,还经常停顿一下,因为柳真清太兴奋了,她有问不完的话。
啸秋有问必答。但从不主动提问。在柳真清蝶蝶不休说话的时候,他观察着她,分析着她,了解着她。长期的革命生涯已把啸秋锤炼得十分沉着老练。
中国这么大,世道这么乱,然而,他们居然重逢了。十一年前在学生运动中浪漫地相识,自然形成四人小组,尔后天涯海角,各奔东西,十一年后的春天却有三个人汇聚到了洪湖地区,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故事。柳真清被这奇遇弄得高度兴奋。
她说:“我真想写部小说。”又说:“我们把文涛弄来吧。”
柳真清轻盈地蹦跳着,随手扯着柳枝茅草。遇上了高兴的事,有文化的女人就和没文化的女人一样思维混乱了。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经常反复问一个问题,经常异想天开提出无理要求。
“壮父知道你来了吗?”
“当然知道。”
“哦当然,你是党代表呢。他还在忙什么?怎么见不到人影?我们三个人应该聚一聚,你说呢?”
“应该。”
“我们应该把文涛弄来。”
“你已经说过这话了。”
“不行吗?”
“显然不可能。”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可能不结?”
啸秋呵呵一笑。
“毛泽东什么模样?”
“高大,仪表堂堂,一口湖南土话,爱吃辣椒。”
“要是不说土话就好了。”
惹得啸秋又发了笑。
第五天啸秋挤了个时间,约柳真清划一条小划子,进了芦苇荡。啸秋开始对柳真清讲话了。
“首先说你要告诉我的一件重要事情,什么事?”
柳真清说:“文涛让捎句话你,她说她想念你。”
“见鬼!她脸皮真厚。”
“啸秋,你竟然这么对待文涛的一片痴情!”
“我要一个资产阶级少奶奶的痴情做什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好罢,那我还是个资产阶级的小姐,你难道不是大少爷出生?”
“那都是从前的我们。我们是家庭的叛逆者。和文涛决不能等同!你怎么还像个小姑娘,还是一团糊涂!”
啸秋叉着腰,挺立望长空。他这副庄严的样子使柳真清开口不得。啸秋的情绪平缓了下来,但依旧十分郑重,眉心里结了个深刻的“川”字。
“真清。我观察了你几天,发现你处境很危险。”
柳真清腾地从土埂上站起来,“我?危险?”
“你看你,居然一直穿着绸旗袍。连地主婆的旗袍都被苏维埃撕碎了,你还穿,你的立场站在哪一边了?”
“可我喜欢穿旗袍。”
“对。这就是潜伏在你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啸秋。”
“我再问你:你申请入党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要思考,不要说假话,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没有贡献……”
“够了!这一切全是借口。”
啸秋激动地痛心地抓着他的头发,做着手势,说:“真清哪真清,你到底是来参加革命还是来修正革命的?你住在富农家,穿着旗袍,戴着丝巾,不写入党申请,连地主富农都称赞你好,你想想!想想!你在滑向哪条路?”
柳真清懵了。随着啸秋的深入剖析,她的鼻尖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最后,她实在不敢听不去,捂住了耳朵拼命摇头。
啸秋等待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