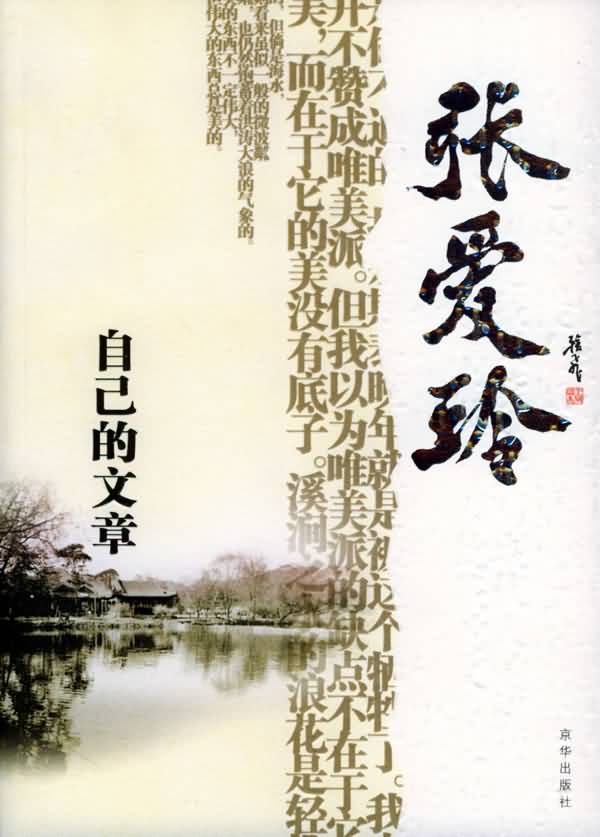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空间里去了。徐灵还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如果从她的手底下出来的人不是完美得像刚出炉的面包,她是不会罢手的,徐灵是一个艺术家。是天才的唯美的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美发师。所以徐灵就和所有天才的艺术家一样,恃才傲物,一般看不上眼的顾客她绝不亲自动手。平日里她也只是在一早一晚接待几个固定的老顾客,这几个老顾客基本都是要做高技巧发型和全套服务的。全套服务就是从洗剪烫到焗油到做发型做面膜加上按摩,付费十分昂贵。但是现在有些人就是喜欢昂贵。昂贵可以使人获得自己很有身份和价值的感觉。
起初徐灵来到长堤街开发廊,大家一见她这种姜太公钓鱼的清高姿态,又见她随意使唤徒弟的做派,都以为这个女人是一个毛病人,她的发廊一定是开不长的。现在做生意,首要的就是要会哄顾客,要笑脸相迎,要十分地巴结。殊不知一般规律是针对一般人的,有的人天生就卓尔不群。一晃几年过去,徐灵的生意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日渐地兴隆,徒弟从三五个增加到了八个,近来又买过了隔壁的一家文具店,把发廊扩大了,装修一新,到处是明亮的镜子,窗子上垂挂着雪白的空花纱帘和风铃,风铃不时地叮当叮当,把发廊浓郁的香气送出老远老远。连歌星和电视剧演员都闻香来找徐灵,她的生意能够不好?
不过徐灵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小康乃至小康偏上是没有问题的,发大财也是不大可能的。这当然也是她的性格特点使然。卓尔不群,落落寡合,迷恋技艺,眼梢子瞅人,大多数人就不会买你的账。众人拾柴火焰高,脱离群众,你能够火到哪里去?徐灵知不知道这一点呢?徐灵知道,她心里明镜似的。徐灵十三岁就出来了,十六岁就出师了。她跟着师傅闯荡江湖走过了数不清的地方,二十岁就自立门户。徐灵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都疯狂挣钱,她把挣的钱炒股票,投资房地产,赚赚赔赔,最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徐灵明白了钱是赚不完的,货币是流通的,为赚钱而赚钱没有什么意思。
徐灵酷爱她的手艺。徐灵酷爱美发店的香气。徐灵酷爱把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创造成一个漂亮清爽的人。所以徐灵来到武汉。武汉离她的家乡广济比较近,回家非常方便。从广济带徒弟来也非常容易。徐灵只带广济籍贯的徒弟。徐灵深信广济人是天生的理发师,别的人则不灵。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湖北在近一百年里走遍了天下的人是天门挑牙虫的,洪湖唱三棒鼓的和广济剃头的。与她的师傅一样,徐灵这辈子肯定也只是收授广济的徒弟。徐灵年近三十了,她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她想发现和培养接班人了。她想轻松一点了。她想物色一个城市的好男人成一个家了。这一切都比仅仅是挣钱要重要得多。
徐灵并不认为自己在城市做发廊妨碍了他人。但是徐红梅对徐灵深恶痛绝的样子好像徐灵极大地妨碍了她。徐红梅不仅自己绝对不上徐灵的发廊理发,还不让她的丈夫和儿子上,还鼓动邻居街坊冷落徐灵的发廊,恶毒他说她的发廊是“鸡”窝,说徐灵是“鸡”。徐灵不是“鸡”,她的发廊也不是“鸡”窝,几年生意做下来,大家谁都了解这一点。徐灵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她不想做违法生意,一点都不想,黑道太麻烦太危险太肮脏了。可是徐红梅还是到处说徐灵是“鸡”,说她的发廊是 “鸡”窝。徐灵记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徐红梅,她们甚至从来没有搭过腔。可是徐红梅就是顽固地认定徐灵和她的发廊是“鸡”和“鸡”窝。而且徐红梅在人前背后始终坚持称呼徐灵的乡下名字徐想姑,难道徐灵不愿意叫徐想姑也不成吗?终于徐灵被惹恼了。徐灵在她的发廊关紧了大门之后一拳头捶破了一只玻璃茶几,她对她手下的人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徐红梅她妈的个老X !”就是这样,徐灵和徐红梅较上劲了。徐灵整日坐在她的发廊门口,把徐红梅一家三口的情况尽收眼底。闻国家是徐红梅的丈夫。闻国家与徐红梅这对夫妻正是俗话所说的“好汉无好妻”的典型写照。闻国家方脸阔耳,虎背熊腰,见人总是一脸笑。徐灵的第一个感觉和后来日渐强烈的感觉就是:徐红梅这么一个刻薄的邋遢的女人,哪里配得上闻国家?
3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长堤街的徐红梅就是这样生活着:夜晚的一觉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半,就地摁开单放机,跳跳健身舞蹈,然后坐在自家大门口,望着大街上形形色色、匆匆忙忙的脚心潮起伏,尤其激起她愤世嫉俗情绪的是大街对面的徐想姑晃动她二郎腿的得意与放肆。在上午这一段重要的时间里,徐红梅虽然人比较邋遢,眼睛发直,可她身体里面的一切都在激烈地跳动:心,脑子,血液,穴道等等。总之徐红梅感觉到这个时候她非同寻常,许多平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想法纷纷地冒了出来,如果不是她竭力克制,想法们一定会从她嘴巴里脱口而出。这种情形使徐红梅联想到了她对诗的理解。
早在她读中学的时候她曾经喜欢过讲解诗歌的语文课,“喷怒出诗人”这句名言给了她非常深刻的印象。想不到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尘封,如今这句名言蓦地触动了她的心。徐红梅初次体会到了名言的英明和伟大,因为徐红梅在这心潮起伏、愤世嫉俗的时刻里,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她渴望仰天长啸,或者胡乱地嚷嚷一些长短不一的语句,这肯定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的感觉了。徐红梅遗憾的是她不是诗人和作家。尤其关键的是过去她从来没有重视过诗人和作家,她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她认识到这些人的重要性。可没有想到的是重要性突然地就来了。徐红梅恍然大悟:原来生活绝不仅仅是吃了睡睡了吃。觉悟来得大概晚了一些。徐红梅问自己,她现在去写诗是不是好比五十岁学木匠八十岁学吹鼓手呢?但徐红梅越是克制自己,写诗的欲望就越是强烈。管他妈的,写吧!徐红梅每天都要冲动一番。最终导致徐红梅没有动笔,而是继续日复一日坐在自家大门口心潮起伏的唯一原因,那就是徐红梅没有找到她的钢笔。在徐红梅的印象中,她年轻时候用过的钢笔好像长期呆在某只抽屉的角落里,当她满有把握地去拿,结果哪只抽屉里也没有。找一样你以为在某处的东西而它不在某处,这很容易挑起人为了维护自己记忆力的体面而产生的好胜心,很容易一个劲地寻找下去,一直弄得自己恼羞成怒。
徐红梅一旦骂骂咧咧地翻箱倒柜,就把诗啊文的全扔在了脑后直至次日的上午。一般的上午,徐红梅都是以心潮起伏愤世嫉俗而导致诗兴大发开始,以在布满灰尘的抽屉角落搜寻钢笔而告终。
在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徐红梅必须去莱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做饭。他们正在念高中二年级的儿子要回家吃午饭。儿子要吃午饭这件事情就不用多说,这件事情绝对地至高无上。儿子的吃饭问题是他们家的希望工程。是直接与儿子将来能否考上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要高考,先补脑。这些狗屁广告我们以为我们在嘲笑它,其实它已经从我们的嘲笑中钻进了我们的生活。徐红梅的丈夫闻国家说了:徐红梅你退休没有关系,你退休让我们儿子吃上了好饭,值得!徐红梅想:当然值得,一个大城市的英俊少年——他是她的儿子。徐红梅很骄傲。徐想姑再会剃头,再装成城市人又有什么用?将来她的孩子就是上不了武汉市户口。她是乡下人,她的孩子也是乡下人。他们根本还是乡下人。所以徐想姑的得意与放肆是没有用的。别说生育孩子了,就是在城市里找一个城市丈夫都是没有门的,没有哪一个正常的城市男人愿意自己将来的孩子是农村人。徐想姑再年轻再漂亮又有什么用?所以,儿子是徐红梅的现在,此刻,后方,退路,未来和一切。所以,徐红梅一到时间就会放弃一切私心杂念去买菜做饭。然后就倚在大门口等待着儿子。她的儿子骑着一辆山地车像小豹子一样窜到家门口,徐红梅就会充满母爱地夸张地咋呼起来:“你这臭小子,把车骑得跟飞一样,不怕吓死你妈呀!饿了吧饿了吧,啊?”一般徐红梅的儿子是不会吭声的,男孩子只管扎着头往家里去。有时候也极不耐烦地小声吼上一句: “嚷什么嚷啊!”不过徐红梅是不理会儿子的。徐红梅喜欢这样的感觉。只可惜徐红梅冲动和积蓄了一上午的诗兴和诗句就像浪花扑打在石头上,只有破碎与飞溅了。
下午的时间徐红梅睡午觉。一觉就睡到了做晚饭的前夕。徐红梅的邻居有许多人约她去打麻将,徐红梅均婉言谢绝了。其实徐红梅不打麻将的真实原因第一是害怕输钱,第二是感觉掉价。徐红梅认为自己至少还不属于社会上那种闲得只有靠打麻将混点的人。
徐红梅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共青团委员,后来又是厂里的工会干部,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打麻将的害处,也曾经配合派出所到处地抓过赌。徐红梅对与她关系比较密切的女邻居孙淑影说了心里话。她说:“你替我想一想吧,如果现在我就这么轻易地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了,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孙淑影是麻将迷,听了徐红梅的话很生气,又碍于情面不好说什么,把脸子默了半天,才说:“唉,徐红梅呀,我真是替你委屈,怎么就没有机会让你做个什么真正的官呢?要真是做了,现在脸皮也就厚了,打个牌算什么呢?”徐红梅的一肚子委屈也被勾了起来,她执了孙淑影的手,衷心地感叹道:“就是啊。”叹完想想,又仿佛觉得孙淑影的活并不很真诚。待徐红梅正要进一步地琢磨的时候,孙淑影早就抽出自己的手走掉了。
4
城市老平房里头漫长而晦暗的下午很适宜睡觉。徐红梅披星戴月跑月票跑了二十三年,欠下了不少的瞌睡,倒也一躺就睡着。徐红梅中年发福,睡觉好打个不大不小的鼾,她的鼾声充分证明了她是一个战胜不了孙淑影的憨厚女人。就看她是不是真的能够动笔写诗了,人把脸不要,百事可为。说不定徐红梅在写诗方面大器晚成,一鸣惊人呢,这种先例世界上也不是没有过。
终于有一天,徐红梅吃了午饭以后没有瞌睡了。她的觉睡够了。徐红梅在床上躺了半天,发现自己一点睡意没有。她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徐红梅终于慢吞吞地爬了起来,去找出门穿的衣服。不知为什么徐红梅一点都没有想到可以利用下午漫长的时间寻找她的钢笔。而是非常地想去逛街。徐红梅掰着指头划算了一番,发现自己虽说是正宗的武汉市人,其实还有很多街道没有逛过,很多商场没有去过,很多新鲜名堂没有见过,很多东西没有吃过。既然徐想姑一个乡巴佬,都搞得像见多识广的俏皮模样,既然人们都说现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机会多如牛毛,徐红梅想,那我倒要去看看。
徐灵把自己精心打扮得跟画出来的人儿一样,坐在她的发廊门口,跷了二郎腿,欣赏大街上的风景同时也向大街坦率地展览自己。徐灵悠闲地,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烟,香烟是她的装饰品,装饰她的手指,嘴唇和态度。她还同时不停地晃动着她的脚。她的脚趾头涂成紫红色,光滑滋润,流光溢彩,脚上套着一双翠绿镶金边的高跟拖鞋。大街上过往的人中不时地有人瞟她的脚,然后再瞟她的人。徐灵相信自己人也是不错的。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是不需要语言的,见多识广的徐灵心里什么都明白。徐灵泰然自若地吸烟,用红红的嘴唇将轻烟缓缓地吹向大街,她的神态里有几分卖弄,有几分讥诮,有几分满足也有几分渴望。她就是这么每天地面对世界,等待和寻找着她想要的机会。
有一件在街坊邻里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终于在闻国家和徐灵之间发生了。闻国家的自行车在徐灵的发廊门口掉了链条。闻国家无奈地从自行车上下来,抱着胳膊时,左右观察自行车。坐在发廊门口的徐灵高兴地说:“链条掉了。”
闻国家点了点头,抱怨说:“是的,链条掉了。骑了不到三个月的新车,链条掉了六十次。你说现在这质量叫什么质量?”
徐灵说:“六十次?夸张吧?”
闻国家说:“我夸张干什么?又没有谁发我奖金。”
徐灵生动地笑了起来,说:“哟,做了几年的邻居,还没有发现闻先生这么幽默。”
闻国家忽然意识到他与徐灵搭腔了。闻国家赶紧闭上了嘴,去捣弄他的车。徐灵也意识到闻国家不想与她说话了。闻国家怕人看见传到徐红梅的耳朵里。但是闻国家毕竟一不当心就搭了她的腔,这就证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