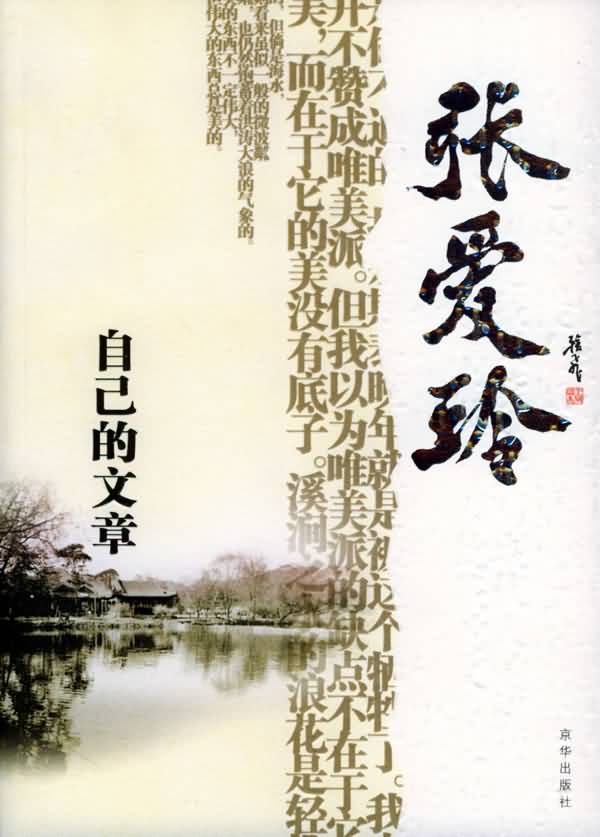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18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管我们如此说,他们还是掩上了门。片刻之后,门大开,肖老师景护士长衣冠齐整地在门口迎接我们。肖老师是长裤子和带折叠痕迹的绸衬衣,景护士长是漂亮新潮又不失庄重的连衣裙。夫妇俩虽然仍穿拖鞋,但都穿上了袜子。
在握手,你好他好的热烈气氛中我们被让在客厅的圆桌两旁坐下。顷刻间桌上堆满了切开的西瓜,冰冻的汽水,冰冻绿豆汤和香烟、烟灰缸。十几年过去,看来肖老师的家庭与时代一起在进步。住房条件从原来的一问房进步到两室一厅,客厅铺着拼木地板,打了蜡,黄澄澄光可鉴人。一台双开门大冰箱一尘不染,装饰着桃花台布。大彩电正在演播某部港台武打片,红红绿绿闪闪烁烁,只是声音被肖老师限制了。
吃吃吃!景护士长说。她又反复自言自语:真是大叫人高兴了。
肖老师说:可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住的虽不远,但从时间来说,是太远太远了!
我问:肖景呢?
他们答:上夜班去了。
肖景十九岁了,初中毕业后上了护士训练班,现在在医院当护士,肖老师谈女儿谈得和天下的父亲一模一样慈祥和自得。
我和丈夫对望一眼。我觉得我的心像一只天平,一头沉甸甸实实在在地放了下来。哦,肖景不是巴音,另一头同时又悬了上去:谁是巴音?
景护士长说:那天你们怎么没来?我热了肉汤饭菜,你们却一直不来。我让肖景去叫你们,你们猜出了什么问题?肖老师想不起你们的门牌号码了。
我说:同样,我们下了楼,我就是说不清你们住哪一栋了。
肖老师理直气壮了:看看,她们娘俩还使劲埋怨我,说我人老了。其实人类有个共同的特点:在短期内容易忘记最重要的事,是不是你又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突然记忆复苏了?
我说:是,在副食商店,天在下雨,我穿着拖鞋。
肖老师更加理直气壮:怎么样?我近年正在研究一个与此相关的人体生理现象课题。怎么是老了!
景护士长说:他这个课题是联合国资助的。
我问:资助的是美金吗?
肖老师夫妇不大好意思地笑了。
景护士长说:美金不美金的没什么说头。有出息的还是你。写文章到处发表,真不简单!我们一直拿你当榜样教育肖景呢。
我谦虚,说:哪里哪里。
谈话陷入双方当面互相吹捧的泥淖,大家都别扭,谈话僵住了一刻。十几年不曾有机会真正晤面,以为都有万语千言,可是事实上都只有浮在表面的一套话。我丈夫不失时机地起身告辞:二位老师,我们要走了,家里还有孩子呢。
他们说:哦,有孩子在家那就不留你们了。今后常来呀。
我们说:常来常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家坐坐。
他们说:一定去坐,唉呀,送西瓜干什么?
夏天吃个瓜嘛。小意思,夏天吃个瓜。含笑送客,含笑劝主人留步,平庸的礼仪损害了真诚。我何苦今日费心费神走这一趟!我停住脚,说:哦对了,我想看看肖景的照片,今天我主要想看她。
景护士长略一犹豫,说:行,行,那就再请进吧。
我丈夫说:下次吧,免得又换鞋麻烦他们。
我说:你不懂,我最喜欢肖景了,她小时候我经常给她梳八条辫子。我指着一间虚掩房门的房间问:那是肖景的房间吗?
肖景的房间打开了。最醒目的是她床那边的一面墙。墙上全是港台歌星的彩色剧照,每张剧照下面写着歌星的名字和他们的年龄,血型,星座,身高体重,鞋子尺码及格言。另有彩笔在歌星的脸前注明对该歌星的评价。童安格:深情专注;梅艳芳:性感多变;姜育恒:淡泊孤寂;草蜢:活泼热烈;郭富城:歌舞并茂。在郭富城画像的四周,围绕着许多钢笔写的话:把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请允许我给你一万个kiss!望着这一帮歌星的是一个女孩,她的像片足有两页开的日报那么大。下面写着:巴音,明天的巨星。
巴音身着长裙,坐在某幢高楼的水箱上。她的长发飘起,裙裾掩足,下巴朝远方微翘。数不清的楼房全都在她身后,显得很渺小。
巴音!
白云苍狗谣
1
星期四,政治学习,停止办公。许多年来全国许多正规单位都是这样,流行病研究所也不例外。
星期四一般由李书记掌握。冬季李书记因哮喘病住院,冬季星期四就由党办张干事掌握。
星期四这一天早晨下雪了。所办的刘干事爱雪,早早便踩着雪上了班,在院子里扫雪。党办张干事不爱雪,所以尽管是提前上班的,比起刘干事还是晚了一步。
“早啊。”刘干事说。
张干事说:“你才早呢。”张干事说话的神态口气完全像婆婆对不称心的媳妇那样又冷又酸又毒。刘干事扫雪把自己扫得两颊绯红,且还穿着裙子!张干事便没有插手所里的公共卫生。
张干事写得一手好字,在小黑板上漂亮地写上了“全天政治学习停止办公”,然后很尽职地将小黑板稳稳当当架在了所的大门口。来上班的人看见黑板都有几分兴奋,大声吩咐敲着碗去食堂吃早点的小单身们多买些馒头。小单身们则大大咧咧地说:“行啊。你们快生炉子去吧。”
上班电铃响过之后,全所大小六个科室就开始生炉子。五层楼的一栋办公楼,每层楼都在劈木柴、冒浓烟。全所失了火似的。
张干事就去找了汪所长。
“汪所长,他们都在生炉子。”
汪所长说:“是啊。武汉这么冷的天,不给我所装暖气,我要找卫生局去!”
张干事说:“这又是一个问题。我是说各科都生了炉子,都买了馒头,待会儿一定又是围着炉于吃烤馒头。”
汪所长笑了:“烤馒头可好吃哩。”
张干事和汪所长相处了三年,还是有很多时候闹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从外表上看,汪所长倒真不像个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鸭舌帽、乱鬓角、两颧枣红,一双迎风流泪的眨巴眼,满脸体力劳动者的粗大皱纹。
张干事没有随着汪所长笑,正色说:“我是说政治学习风气不好的问题。去年冬天就开始吃烤馒头,今年成了风。”
“哦。”汪所长立刻严峻了。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会出漏子的!刘干事你别笑,你年轻经历得大少,你不信吧?我信。张干事信。只怪我业务上的事太多了!张干事你抽个时间去向李书记汇报汇报,我建议尽快开个支部会议,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防微杜渐。”
汪所长说到这里一拍脑袋,想起今天局里还有个重要会议,连呼迟到了迟到了。刘干事赶紧拿起电话要了司机班。所谓司机班也就由两个司机组成。一辆流行病调查追踪车,一辆消毒防疫车。司机在电话里说今天政治学习不办公,刘干事说你少来这一套。汪所长接过电话训斥一句:“胡闹什么!”司机这才服了。
临下楼汪所长语重心长地对张干事说了一番话:“你看看,自由化都在冒头了。今天的学习你要抓好啊!”
张干事点了点头。张干事就是喜欢这种工作气氛。李书记曾提示过她,说汪所长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耍滑头。张干事想的却不一样,让别人溜走吧,让她来抓工作,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一股浓郁的烤馒头香味从一楼洋溢出来。一楼的流病室是所的核心科室,有二十余人,占了全所人数三分之一。历届领导要抓都是抓它。
流病室的大办公室里有一只极大的取暖炉,炉膛内至少塞了十块蜂窝煤,连炉壁都被烧红了。炉子上坐了一壶突突冒汽的开水,四周堆了一圈馒头,馒头二两一个,胖嘟嘟的七八个馒头被烤得吱吱作响,色泽焦黄。全科人以炉子为中心辐射状坐着,一边掰馒头吃一边轮流念报纸:一人只念一小节,念完即传给下一个人,如果这人只顾吃馒头忽略了接报纸,就要受罚。惩罚是给每个人茶杯续水和掏炉灰上煤。这么一来,室内气氛还是紧张而活泼的。
张干事在流病室门外听了好一会儿,终于掀开帘子走了进去。有人看了看张干事,但没有人停止动作。
“我想提醒一声现在正进行的是政治学习。”张干事将手抄在裤口袋里说。
大家互相瞧瞧,又瞧中年护士杨胖子。
杨胖子说:“我们在吃馒头,是为了坚持学习。我们胃疼,胃酸分泌过多,长期下基层工作造成的。”
张干事说:“胃疼该吃药。”
杨胖子说:“对极了。那我们这就去看病。我们是工伤,所里规定工伤可以随时去看病。”
张干事盯着杨胖子的眼睛,恨不能一针见血捅穿她的那张刁皮。张干事这一生工作过五六个单位,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个把类似杨胖子的肥胖中年妇女,这类女人极端自私、泼皮刁蛮、爱出风头、死不怕丑。张干事到处和她们发生尖锐矛盾。
“站住!”张干事说:“工伤看病也得向科室负责人请假。”
“黄头,黄头。”杨胖子朝唯一坐得老远的组长叫嚷起来。
黄头放下做记录的钢笔,哆哆嗦嗦取眼镜戴眼镜忙个不停,他有三副眼镜随身携带,分管远近距离和放大。
“行了别闹。胃疼就用馒头中和一下。”黄头说。
有人乐得吹了一声滑稽的口哨。张干事应声转身,一排年轻人漠然望着她。张干事痛心疾首说:“你们都是大夫!知识分子!都受过高等教育!”
杨胖子说:“张干事,用不着您提醒,他们都不是弱智儿童。”
张干事越过众人头顶,说:“黄教授,您出来一下。”
黄头被张干事带到小雪纷飞的院子里。
“您是教授,是头头,怎么能支持吃烤馒头?”
黄头愁眉苦脸望着雪粒。骤然从温室出来,他有点冷,一冷就毛细血管收缩,面部苦黄苦黄,一滴清鼻涕呼之欲出。
“张干事,请您别叫我教授,我是副教授,这是之一。之二,胃疼不吃点东西难道真让他们去看病?”
“显然是假话,是借口。要是毛主席在世,人们敢这样?”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张干事被黄头的书呆子气弄得无可奈何。杨胖子却在流病室的玻璃窗后恣意点评张干事。“你们看她那张干巴苦黄的老脸!还是中共党员,还想当书记,本身形象完全是个饥民,整个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满。啧啧,好烦人嘛。”
张干事回党办时预感到所里会出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此涣散,不出问题才怪。张干事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痛苦地考虑:作为党员,副科级干部,她应该管,但她没有权。李书记有权却又有病。她的事业怎么总是如此坎坷呢?
2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老王无视所门口的小黑板闯了进来。收发室老头“嗨嗨”两声没喝住,追在老王身后吆喝。
老王径直找到流病室。有人立刻告诉他:“今天不办公,政治学习。”
一群人懒懒裹着白大褂,歪在火炉边吃烤馒头的政治学习形式使炼钢工人老王非常气愤。
老王吼道:“你们不办公老子要你们办公!这是什么政治学习?学习吃烤馒头!谁是头头,出来!”
流病室全体人员都火了。冲上前纷纷质问老王是什么人?为何如此蛮不讲理?并且众志成城不让黄头暴露。黄头自以为堂堂一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能忍辱偷生的,所以力排众人从人缝中挤了出来,换上近距离眼镜,仰视着老王,说:“我就是科室头头。你在我们这儿闹什么?”
“我闹了?”老王反问。老王一把捏住黄头胳膊把他拉到院子里,说:“老头,你听我告诉你一件事再下结论。”
流病室的人见自己的头儿被抢,一窝蜂拥到了院子里。楼上有的科室听到了动静。从走廊上往下探头。马路上的行人也都闻风而来。
原来老王的儿子在某幼儿园大班,那个班近期发生了两例急性黄疸型肝炎。流病室得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派杨胖子、黄中燕两位护士去幼儿园给那个大班全体幼儿注射了胎盘球蛋白以增加抵抗力。问题在于老王的儿子回家告诉父母:一个胖大夫只摸了摸他的屁股,没给他注射。经幼儿园保健医生检查证实:幼儿屁股上的确没针眼。
老王就此事作了调查,发现胖大夫从幼儿园出来后,离开了同事,偷偷赶到某小学为其儿子注射了那支球蛋白。
听到这里,众人哗然。流病室人自知理亏,三三两两
往后缩。
黄头虽然年已半百,一辈子也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