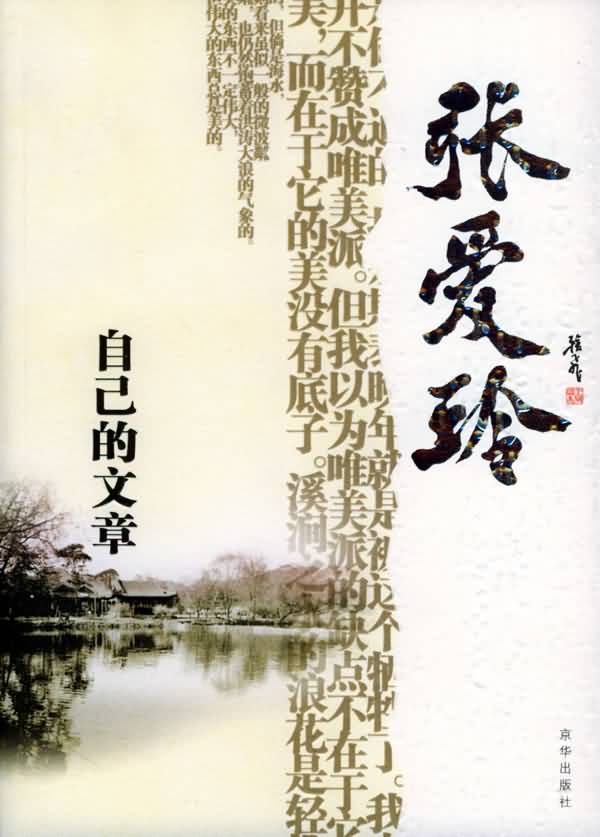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18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
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
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
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
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
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
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
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
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
“同志你贵姓?”
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
“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
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
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小块。
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
“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
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
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也还是到武汉看我。我们是朋友了。
拨通了电话。我说:“喂,我找老阿山。”
“请问您哪位?”北京人,说话文明礼貌。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老阿山吧?”
“我是,请问小姐芳名?”
老阿山没听出我的声音。为调动我们曾通过多少电话。那时候我只对着话筒呼吸他就知道是我。
我想多说几句话看看。我说:“我的名字叫红。”
“噢,林燕红。燕红。你好。”
我叹了一口气。
“小姐您别叹气。我知道您是谁,可我不敢说。我不敢相信您会给我打电话。”
老阿山肯定又错了。老阿山在小姐世界里邀游,眼花缭乱。
“红霜!红霜小姐您好!”
我说:“多好的记性。”
老阿山如释重负。说:“怎么会记不住您呢?那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有几个漂亮小姐?就您一个。”
我为老阿山高兴。一个专业性杂志的编辑混到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了。我笑了几声。
“对不起,小姐。您到底是谁?请高抬贵手。我们导演成天和演员打交道,女孩子太多了。如果您也是要求上片子的小姐,请直接报姓名,否则我只好挂电话了。”
“恭喜你成导演了。你挂电话吧。”他不挂我倒准备挂了。
“啊!听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
我不挂电话了。我说:“老阿山,你呀,变化可太大了。”
“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伤心地说:“我没开玩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