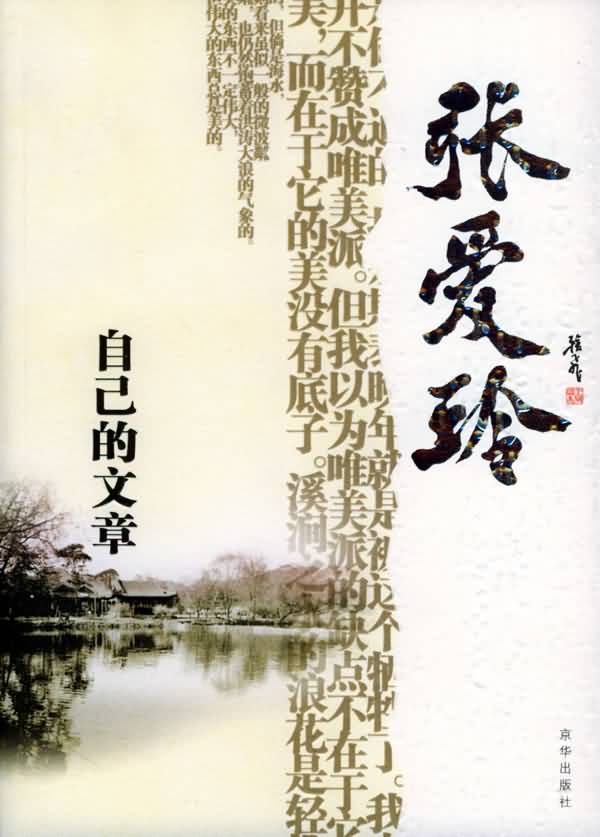刘墉文集-第9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螳螂总是单独猎杀、自己享用,所以比群体合作的琪塔更孤寂。
想起老诗人纪弦的〈狼之独步〉——
我乃旷野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
车,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夭地……
对了!还有哪位诗人,说“故乡土、故乡土,掬一把故乡土……”?这螳螂不吃不喝,
是不是有了乡愁,或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时,是不是该用古人的方法,吃一点故乡带来的泥
土?
它的故乡,太容易了!不就在窗外吗?
我突然触动了灵感,也产生了“同情”,决定为它带一点故乡的风土来。
走到当时抓到它的那株牡丹旁,摘下两片叶子。上面还有露水呢!多棒!正是它的家乡
风味。
打开盒盖,把叶子放了进去。对着在一边观看的女儿说:“它想家了,所以给它放叶子
进去。”又拉着女儿,绕着放在地毯上的玻璃盒子转。一边转、一边唱:
“捧一把故乡土啊、故乡土!饮一掬故乡水啊、故乡水……”
绕了两圈,跳个舞、打个转,我放下女儿的小手,说:“爹地要出去抓虫了!书上说螳
螂只吃活的虫子,它现在不想家了,不生病了,也有胃口吃东西了,爹地要给它找好东西吃
了!”
我以跳舞的步子,一步一跳地到后院,跳到花圃,觉得很开心,好象自己这一跳、一
唱,便回到了故乡,又觉得自己成了螳螂,在玻璃盒子里,唱故乡的歌、吃故乡的食物、穿
故乡的衣服。
才一下子,就抓到一只黄蜂(Wasp),黄蜂跟蜜蜂不一样,蜜蜂身上比较圆有点笨。黄
蜂身子比较长,颜色也鲜艳,尤其黄黄的肚子上还有着黑色的条纹,就像老虎,所以中文就
该是“虎头蜂”。
虎头蜂进场候教了!我的信心十足。第一,我的第六感让我知道,有了故乡的树叶,螳
螂的心好多了;第二,虎头蜂比昨天的大黑蜂小得多,又比前天的蜜蜂美丽,丰乳细腰肥
臀,十分性感,螳螂一定会喜欢。
虎头蜂开始使用它的“氧气配额”了,嗡嗡地东撞、西撞,撞着撞着变成攀附,攀在盒
子旁边休息,又沿着盒子爬来爬去。
这螳螂也爬来爬去,倒不是为了捕食,而是莫名其妙地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这笨蛋居然好几次跟虎头蜂面对面地碰上,甚至憧到了鼻子,它却不下手,还
一扭头、躲开了。难道它们竞是“小同乡”?
在这小小世界里,好像有两个漂泊者,不断转来转去,当然也可以说是两位落难者,突
然不知怎地掉到了另一个空间,于是什么都不顾了,只想找路出去。
对!它虽然来了三天,又有了故乡的树叶,还是在想家。想家就不能安心。它实在太笨
了,为什么不懂“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道理呢?这就好比人,对前一个家的心不死,就不能
享受下一个家的快乐。对来生不断地瞩望,也便不能把握有限的今生。连武陵人,都没能留
在“桃花源”。
看看!美食当前,有酒当歌,既无风、又无雨,住在玻璃屋里,这是多么美善的“桃花
源”啊!只要沉下心来,细细看看周围,就能乐不思蜀了。
还是虎头蜂聪明,你瞧!它不飞了,也不再忙着找出路,它躲到了大黑蜂的身边,如同
一只小黄狗躲进大黑熊的怀里。多么温暖而有安全感啊!大黑蜂浑身长满了细细的绒毛,我
几乎可以感受到那种柔软。
看!虎头蜂紧紧偎在大黑蜂的六只脚之间,开始它的午餐。
大黑蜂的脚上挂满了黄色的花粉,在小小的虎头蜂看来,应该像是六大盘佳肴。多好
啊!不必辛苦地在花间奔波,只要偎在这死去的大黑蜂间,就能拥有这么多现成的食物。
何必想强敌当前呢?何必想明天或后天的死呢?又何必想“义”与“不义”呢?自己活
着最重要。
傍晚,我又丢进了一只大蚂蚁和苍蝇。我对“它”是完全失望了。连这只蚂蚁和苍蝇,
我也不奢望它会去抓。毋宁说,这两只“小丑”,是我给它的最后的晚餐,也是给它的讽
刺。
吃了!你是为活一条狗命,而“马食鸡早”;不吃,你是连最下三滥的小鬼,也应付不
了。你是可怜的英雄,不再能夺权,甚至不再跳得上马背,又一时死不掉;便赏你个闲差
事,坐坐冷板凳,混口饭吃吧!
夜里,再去看这家伙一眼。蚂蚁在爬、苍蝇在飞,虎头蜂躺在大黑蜂的怀里,在睡。
“它”的头靠在盒子的一角,已经抬不起来。
第二章 少年杀手的蜕变
蜕变
八月三十—日
早晨没去看它,猜它已经死了。古人说“疾不问、死不吊”,大概也是同样的心理吧!
即然知其必死,药石网效,既然病者已形容枯槁,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既然英雄已经拿
不起武器,倒不如让他自己安安静静地去死,也给我留下“当年美好”的回忆。
想起张爱玲,从一九七二年开始隐居,又不断地搬家,不打电话,甚至很少写信、很少
正眼看陌生人。伟大的作家居然不再有桌子,只用几个纸盒当书桌。也不再有书架,甚至连
自己的作品都扔到一角。
当然也可以这样想,既然已经不是作家,又何必用书桌;既然作品已经完成,且不打算
鉴往如来,又何必回头看。既然在人们心中早留下美好的才女印象,又何必用憔悴的容颜去
破坏?
这螳螂虽然不太像螳螂,更称不上什么英雄。但螳螂毕竟是螳螂,那相貌自然雄武,教
人起敬。如同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的狮子,虽然无胆,毕竟是只狮子,是狮子
就多少有些与生俱来的尊荣,应该以狮子的礼来对待,不可对之吐口水,应该用上等棺木。
嘿嘿!想起溥仪,末代皇帝,讨了不少老婆,后来被分配看管花园,但怎么说,他还是
博仪,没被当做普通人,而有了特别的待遇。再看看,许多名人、伟人之后,管他上不上
路,不也被认为该有些特别的气质,该享些特殊的礼遇吗?
一念及此,我想还是该去探视一下这没种的螳螂,为它办个小小的葬礼。我一边走向书
房,一边想:其实很简单,像阿玛迪斯一样,把玻璃盒子打开,往抓到它的那个树丛里一
倒,就解决了,而且算是还葬故乡。至于那只还没死的虎头蜂、大蚂蚁和苍蝇,既然硬是走
运,遇上个笨主子,没被咬下头来,而且日日等杀地拖到今天,还能留得一口气,就应该被
释放。
所以,为主子办丧事的时候,也正是为犯人办喜事的时候,许多政治犯不都这样吗?说
话得罪了圣上,甚或只是为主子捶重了些,就被拖出去关了。这主子死,不是天大的好事
吗?
这下可以了解了,太子诞生可以大赦天下。新主子登基,也可以大赦天下,看来都是喜
事,其实大有不同,何必说“新主子登基”?应该称“旧主子下台”。旧主子即然下台了,
许多功过都可以重新认定,许多忠奸也可以再来评估。何不表示宽厚,将“旧主子”关起来
的人犯,一并赦了吧!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祖宗爷爷奶奶!我的主子死了。我有救了!”那虎头蜂和苍
蝇、蚂蚁被释放的时候,不知会不会这样喊。
来到书架前,往玻璃盒里看。吓一跳:大哪!怎么一只变两只了?只见两只螳螂紧紧抱
在一起,贴着盒底睡着,一动也不动。难道是我那八十九岁的老母,又抓来一只螳螂,偷偷
放了进去?我猜,家里就她这个老顽童,有可能。
小心翼翼地抬玻璃盒端到亮处,见到“一尸一鬼”。原来那两只螳螂,一只是死的
“它”,一只是“它的鬼魂”。
可不是吗?那鬼魂是半透明的,一模一样地伸着脚、翘着屁股,只是头不太清楚,像脱
下的面具,被卷在一起。再摇摇,“它”还动,没死!突然灵光一闪:
“天哪!敢情它脱皮了。”
跟着是悔恨:我怎么那样糊涂呢?它不吃不喝、不打不斗,原来是等着脱皮。还有,它
不断爬来爬去,又把头紧紧靠在盒底,原来是为寻找个脱皮的好地方。书上不是写了吗?因
为身体要长大,外面的皮却长不大,螳螂一生要脱五次皮。每次都先不吃东西、懒洋洋好几
天,再找个树枝,好好抓紧,头朝下地从“旧衣服里”钻出来。
提到“旧衣服”,使我想起“蝉衣”,也就是“蝉蜕”,那张牙舞爪挂在树上的空壳,
明明主子早不要它了,还紧抓着树皮不放。这不放是有道理的,只有“死壳”不放,才能让
“新身”得以脱离,好整以暇地从旧衣服里慢慢钻出来,连每次个脚趾头都完好无缺地
“脱”出来。再站在旧壳上休息,把翅膀晾干。
现在订了。我赶快把玻璃盒子打开,将它拿出来,旧皮轻如无物地飘落,手上“四肢无
力”的是新生的螳螂。我真想知道,在无物可抓的情况下,它是怎么脱身的?
这就如同摘手套,你总得一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套尖,才脱得下来。而今这螳螂的旧皮
既然不能先站稳在树枝上,难道是用不断甩动的方式,把旧皮摔掉的吗?
我注意检查它的六只脚,除了前面两只大钳子,还有一小部分没脱干净,其余四只脚确
实有三只半已经脱出来了。稍稍拉了拉那没脱干净的半只脚,一层薄皮便掉下来。只是它必
定经过了一翻挣扎,脚虽然全出来,后面两条腿,和中间的大腿,却都折伤了。
更麻烦的是翅膀,书上说螳螂在“脱身”之后,都会改为“头朝上,屁股朝下”的方式
站着,使原先团在一起的翅膀能像花瓣一样舒展开,又说这是最神奇的一刻,可是现在它没
能挂在枝梢,让体液流入翅膀,更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清风把那潮湿的翅膀吹干,而是委在
地面,趴在盒子的一角。怪不得那翅膀看来像几片脏脏的抹布,抒成一团。
照心理学,童年过的无助与恐惧,可以再用游戏的方式表演一遍,且在表演当中把原来
无助的情势逆转,就能克服心底潜藏的恐惧。
我现在也要为它作这样的治疗。
首行旬折断的三肢,得趁着外骨胳还没定型,先为它矫治。这小东西当然不能绑绷带、
打石膏,我找来了胶条,把那折成九十度角的细腿拉直,并固定在胶条里。我常为不小心弄
断的花做这种事,而今“园艺家”改行当“兽医”,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接着找来一根细线,把它由胸部绑起来,再挂到昙花树枝上。这样做也有道理,想想,
它的六肢折伤了三肢,前面两只大钳子,又刚用小镊子,一点一点把旧壳剥下来,当然不可
能站立,更甭提攀爬了。而它的翅膀若不挂起来“利用地心啄力”,就无法伸展;刚矫正的
腿若强迫站立,更不可能复健。
当然只好用挂的。
接着是使时光倒流,为了怕它着凉,我用毛笔蘸水,把“那团”翅膀弄湿,再抚平,希
望像是回到刚裉出旧壳的时间,站在枝头伸展双翼。
哦!其实不能称为双翼,如同晴蜒,它是四支翅膀的。两支绿褐色的在身体第二截的背
上,另两支褐红色的在第三截,也就是所谓“腹”的背面,当它敛翅的时候,绿的应该盖在
红的上面。所以整只螳螂就看来是绿褐色的了。
我也作了退一步打算,如果翅膀能展得开,固然好。若果还是没办法,与其让它拖着这
么一大团,不如动手术切掉。螳螂本来就不需要飞,飞多半是为逃跑,既然已经成为我的盒
中物,未来半生自可以在盒子里称王,每天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又何需翅膀?
至于那些折伤的脚,如果胶条有效,大概不致残障。要是已经伤筋断骨,无法复健,恐
怕我只好狠心地把它处死。
这也不是狠心,而是仁心。与其让它饿死,或放到外面,让它的仇家蚂蚁们咬死,不如
来个痛快的。如同马,伤了脚,既然是只马,却不能跑,不如射杀。请不要觉得我残酷,螳
螂毕竟不是人,残障的人还能思考,哈佛的那位写《时间简史》,还休掉他老婆,另结新欢
的史蒂芬·霍金(Stephen W。Hawking),不就是严重的残障吗?据说还被认为是爱因斯坦
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呢!
但这螳螂能思想吗?不能思想、又不能猎杀的螳螂,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突然想起
项羽,很能杀,却不能思想。其实他也非不能思想,而是思想时多了几分仁慈。猎杀的人有
了仁慈,就如同妓女在做生意时有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