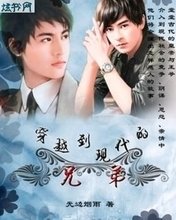极端的年代-第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崭新的世界带到他们眼前——对那些不识字的小民来说,传入耳中的广播电波,有时甚至还是以他们没有文字的方言出现。虽然收听广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可是除此之外,本人若不曾在城里打过工,几乎也都有个三亲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儿讨生活打天下。因为乡间人口以百万计地拥向都市,甚至在以农村为主的非洲,动辄三四十万人口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见——如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加纳、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贝宁、赞比亚、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等。于是村镇与城市密不可分,紧紧相结。甚至连最偏远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乐瓶、廉价电子表、合成纤维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历史逆向反转之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然也开始在第一世界里推销它们本土的技能。于是欧洲城市的街头,可以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脉来的印第安游民,吹弄着他们的感伤的笛乐。纽约、巴黎、罗马的人行道上,则有西非的黑人小贩,售卖各色小玩艺给西方大城里的居民;正如这些大城市民的先祖,曾前往黑色大陆经商一般。
凡是大城,自然便成了变化汇集的中心点,别的姑且不论,大城市照定义天生便代表着现代。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移民,便经常指教子女道:“利马进步多,刺激也多。”(julca,1992)也许进城之后,乡下人还是用老家带来的工具为自己建立起遮风蔽雨之地,盖起一片片跟种田的家乡无异的破屋茅舍。可是城里毕竟太新奇了,充满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务,眼前的一切,都与过去如此地不同与矛盾。在年轻女人身上,这种变化的感受尤其显著。于是从非洲到秘鲁,都对女人进城之后,行为就变了样的现象发出同声悲叹。一位由乡下进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马一种老歌(huayno)唱出了抱怨之声:
当年你由家乡来,是个乡下小姑娘;
如今你住在利马,秀发梳得像个城里妞;
你甚至还说:“请”等等,我要去跳个扭扭舞;
别再装模作样,别再自以为神气,
你我眉梢发际,其实半斤八两。
(mangin,1970 pp.31-32)
其实就连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的波及(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行销、新组织席卷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开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新旧两面的冲激,在哥伦比亚亚马孙河边区一带最为激烈。70年代,该地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大麻的中继站,在此炼制成可卡因。这一新天地的出现不过几年工夫;是由不堪国家及地主控制而迁移至此的拓荒者所开辟的。他们的保护神,则是一向以小农生活捍卫者自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游击队。这个无情残酷的新市场,自然与从来以一枪、一狗、一网,即可自给自足谋生的农耕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试想一小片丝兰(yucca)地、香蕉田,怎能与那虽不稳定但一本万利的新作物相抗衡?这股巨利的诱惑怎能抗拒?旧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挡那毒贩保镖横行酒吧歌厅充斥的新兴城市?
于是乡间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其转变却完全依赖城市文明及城市工业的动向。乡间的经济状况,更常视本乡人在城里所能挣得的收入而定。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谓“黑人家园”的经济,即建立在这种“外汇”之上。当地10%~15%的经济来源,来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余则完全依靠出外人在白人地域工作的所得供应(ripken and wellmer,1978,pp.196)。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往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在外出户与留居户复杂的作业整合之下,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移转向非农业性质(smith 1989,chapter 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为出色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工,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低中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不为官方数字所记录的非正式经济活动。
因此,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究竟如何成形,以及转变的自我意识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可供效力。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级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寂沉,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除此之外,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
不管50年代百般纷乱,到60和70年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已经明显,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情势确凿,在南亚及东南亚几处主要国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渺。其实世人往往不知,共产党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转动变化,倾覆动摇其半分。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能,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一般以为,居住在苏联与阿富汗边境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两族,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显然要比他们居于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许多。其实不然,居于南部的族人并不比居于北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那里。同样道理,1930年以来,民族之间的流血斗争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从来就不曾需要共产党统治当局烦恼操心(不过在这数十年的集体社会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难免:苏联法律年鉴中,就曾记载过一起因集体农庄上打谷机意外绞死人而引发的仇杀事件)。但是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初期,往日旧观再现,使得观察家必须提出警告,认为“车臣地区(chechen)大有自我灭族之虞,因为绝大多数的车臣家庭,都卷入了某种家族仇杀复仇的纠纷之中。”(trofimov/diagava,1993)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学者发现:“加纳以及非洲各地固有的家族关系,在巨大的负荷之下勉力支撑运作。就好像一道旧桥,多年来在高速往来的交通重压之下,年深日久,桥基已经崩裂……农村的老一代,与都市中的年轻人,相隔着数百英里破旧难行的道路,以及数百年来的新发展,彼此深深地隔离着。”(harden,1990,p.67)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拥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造成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方化精英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再多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级。后者来往的对象,是外来的殖民者,或自己留洋归来的同类。多数时候——尤以在南亚为最——前者对后者极为忌恨。总而言之,贫苦大众对西方19世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生观不表同感,在西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原有的非宗教领袖与穆斯林民众的新兴力量之间,冲突日显,而且爆炸性愈为严重。从阿尔及利亚到土耳其,凡是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有关宪政法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其捍卫者多属领导该国由殖民政权解放出来的世俗政权,或其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因此,政府以军事力量,与民意相抗衡着。
这类冲突发生的地区,并非仅限伊斯兰教国家;与进步观念相作对的人士,也不只是贫苦大众。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徒的强烈排他性,即获得新兴的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80年代,一股意外的种族宗教国家主义潮流,更将原本平静繁荣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一转而成杀戮战场,其激烈野蛮,只有萨尔瓦多可以相比。争端植因于两项社会转变的因素: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以及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提高的年轻群众(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而分裂;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知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口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事象——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兴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增添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iama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