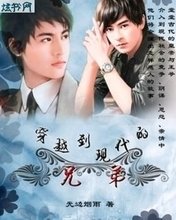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7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Ӵ�Ҳ��������֮·������ī�����Կ�����������֮�ȵĹ��ң���1910��������������߸�Ϊ��ȷһ�㣬��30���������ī�����������������Ѿ������Ĵ����ؾ��֣�agrarismo���������������ϵĺ�����Ȼ�ܶ࣬ѧ���ϵ�ͳ���о����ܲ��ϣ��������ĸ��������Ͼ����㣬��ֳ֮������ңԶ��ս�ܾ���ϡ�٣����������ظĸ��վ���������һֱҪ����˹�����ڹŰͷ���������Ϊ�Űʹ��������ģ���ʹ���ظĸ�����������������ν��̣�����ŸĹ��ˡ�
���������ִ������˶��ԣ����ĵĺô���ֹһ�����棺�����ϵ������Բ����ԣ������Ǹ�����Ȩ���������෴�ķ�������Ȩ��˫�����ɽ��Ӯ��ũ��֧�֣�����˼���ϸ�Ϊ�������硰���ػ����Ͷ����ȿںţ�����ʱ���������ԴﵽijЩ�����ľ���Ŀ�ġ�����Ȼ��������ĸ�����ʿ��ĸ�ң����ڽ������������·�������˵��ֶξ�������ɼ��ָ��ƣ���δ����̫����������ʵ���ڲ���ά�Ǻ������������ֱ���1952���1958��ʵ���������·���֮��ũҵ�ܲ������������½�������Ϊ��ƽ���������Ҳ��ָ����������ũҵ������������ԭ�����Ѽ��ߵĵط�����ǰ�����ij��Ⱨ����̬�ȵ�ũ��һ������Լ�����أ��ܿ�㷢�Ӹ߶ȵ�����DZ�ܡ��������ձ���̨�������õ����ӣ���������̨��ijɾ���Ϊ���ˣ�land��reform��1968��pp��570��575����ά��һ�����ũ��Ⱥ��Ĵ��ڣ��䶯����ʵ�뾭���أ���ȥ��ˣ�������Ȼ����Ϊ�ִ������ݱ����ʷ֤����ũҵ�����Ĵ�����ߣ�ǡ����ũҵ�˿ڵļ��ٳɷ��ȣ��Զ�ս��������������������������Ϊ���ء��������ĵ����壬�������Ĩɷ����Ϊ���Ͼ�Ҳ֤�������Ը�ũ�ƶ��£����������ִ����ֶξ�Ӫũ����Ľϴ���ũ�ң���Ч�ʾ��Կ����봫ͳ������軧�ƶȣ���۹�����Ĵ��ģũׯ�������������Ҿ��и���ĵ��Կռ䡣��������ijЩ�빤ҵ�����о�Ӫ�İ취����1945�����ά��ʽ���͵Ĺ�Ӫũ�����Լ�Ӣ����̹���ῦ��tanganyika��������̹ɣ���ǡ��������������ַ������й�֮���������ڹ�ȥ������֮���ũ����������������ڣ�һ����Ϊֻ���Դ��ģũׯ�ķ�ʽ��ֲ��Ӫ�������ֶΣ���˵������ijЩȱ��������Сũ����Ȼռ�м�Ϊ���Ե����ƣ�ȴ�Ѿ��DZ�Ҫ�ľ�Ӫ��ʽ�ˡ����������ף��Դ�ս��������������������ũҵ�ϻ�����ش��չ����ν�Կ�ѧѡ�ֵġ���ɫ���������Ͼ������ɾ�����ҵ��Ӫͷ�Ե�ũ�ҿ�ʼ�ģ�ӡ�ͱ߾��������ռ�Ϊһ����
������ˣ����ظĸ�ľ��ö���ȴ���dz�������������ߣ�����������ƽ�ȵĿ��ǡ��ͳ��ڲ�����Ĺ۵���ԣ�һ��ʼ�����óɱ�����������������÷��䲻����״�����������ձؽ��������ľ��롣�ƽ�ʱ��ĩ�ˣ������������������ھ��������ϴﵽ��ƽ�ȳ̶ȣ����ڵ������磬���ɼ�����ʵ�Ե�һ�ߡ����������������ھ���˥�ˣ��Լ�һЩ��ʿ�������г����Ž����ڽ���ѧ�����ţ����ò������������ٶ���ijЩ�������֡���������ƶ��������Ϊ���أ����ӴΣ�������һЩ���������棬ƶ���IJ��ȴ�൱�ӽ����⼸������������������ռ�����Э����ֱ�Ӿ�Ӫ֮�£�������һ����Ϊ���ҵ����ظĸ�����ձ���������̨�壨������������ƽ�ȳ̶ȣ���Ȼ�Ȳ���ʵ���������Ķ�ŷ���ң���ʱҲ�����Ĵ����ǣ���kakwani��1980����ƶ�������������٣�����������Լ������Եĺô����������۲������Ϊ��Щ���ҹ�ҵ���ɹ���һ�������۲����Ҳͬʱ��Ϊ���������õķ�չ�����ȼ�Ъ������ǰ��ȴ�ֵ�������������ϰ��������ᡱ�ľ��ñ��������á����������ƶ�����ز���������ӦΪ���������õĴ�ܵ����������Ρ���ƶ�����������ݹ��ڹ�ҵ�������г�������ޣ��Բ����⡣����������ƽ�ȵ�����������أ�������ȱ�����ģ��֯�Ե����ظĸ����֮�䣬ʵ�ں���˵û���κι�����
���ظĸ��ȻΪ���������Сũ����ӭ�������������ֶλ�δ���γ�Ϊ��������ũ������ʽ֮ǰ����ˡ������ֱ��Σ��ǹ��������ҵij�����Ȼ������ӭ���ܻ�ӭ���ڸ���Сũ�볫���ִ����ij��иĸ��֮�䣬˫�������ĵ��ڴ�ȴ��ԯ���ޡ�ǰ�߶������Ծ�����Ե����������Ȥ���ڹ������εĹ۵㲻ͬ�������ص�����Ҳ�ǽ�����һ���ԵĴ�ԭ��֮�ϣ�������������ض������š���³�ĸ��ɽ�����ɵ���������1969���ƶ��������ģ���ͼһ�ٴݻٸù������������ƶȣ�haciendas��������˶�ʧ�ܡ�ԭ����³ӡ�ڰ��ߵص�����һ��Ϊ����˹ɽ����ũ���ṩ������˫������Ĺ�ϵ��Ȼ�����ȶ������Ǹĸ����Щ��������壬ȴ������ζ���ط��洫�ġ����������ص���һֱ������������ԭ�����������ٸ���������������ʼ���μ������ȴ������ļ����磬�����ʧ��������ԶҲ����������hobsbawm��1974�����ĸ�ǰ���е�����������ʽ����������ά��������ʵ�����ڶ��������������unidades����ԭ��Ա��������Ȩ���ˣ����ڸĸ�����ʽ��Ӫ��ʵ�飬�������κ������ũҵ�ƶȣ�Ҳ��������Ȥ�����Ǽ��ڱ��ֵĶ��������ǹ�ȥ��ͳ����Ȧ���䲻ƽ�ȣ��У������еĴ�ͳ�����ֶΡ�����ڸĸ����֮������ȴ��ͷ�����֡��������µĹ����������ʵ�������Ƕ����й�ͬ��Ӫ�ߵ����ݣ����·��ڴ���ׯ������������֮�䣨�Լ���������֮�䣩�����صij�ͻ�����̴棬һ�ж�δ�ı䣨gomez��rodriguez��p��242��255��������Щ������������ԣ��ĸ������ʵû���κ���ı䡣��ϸ̽��������������ӽ�Сũ��������ظĸ����Ҫ��30���ī����ij��ԣ��ⳡ�ĸォ�������ص�Ȩ�����������䣬��ȫ����ũ�����Լ�����Ը��֯���ع��У�ejidos�����������⣬�Ǽٶ�Сũ���������Ը��Ե�������������һ��ʩ������Ч���ϻ�ü���ɹ��������ھ�������ī�����պ��ũҵ��չȴû���κι�����
������
��ʮ���¡��������硡4
/С��˵��
4
��ս֮����ǰֳ����ɱ���ɵ���ʮ���¹��ң��ټ���һ��Ҳ�������ɵ۹����幤ҵ�������������������������ң��ܿ췢���Լ����ۼ���ͳ�ơ��������硱������֮�£�����ԭ�����桪��������Ϊ����ƺ�����1952�굮����harris��1987��p��18���������������Ա��ߣ����з��﹤ҵ������ɵġ���һ���硱���ɹ�������Ϊ��Ա�ġ��ڶ����硱����˵���ֽ���������gabon����ӡ����Ͳ����¼����ǣ�papuanew��guinea����һ���Զ�����ͬ�����ķ�ʽ��Ϊ��Ц��������������Ҳ����ȫ��ͨ����Ϊ��Щ���Ҷ�һ����ף��롰���������ȣ�����������������������������������λ�����ǵ�����Ҳ��һ��һ����Ҫ����չ����ͬʱȴҲ����������ͷ�ʱ�����������г���������ѧ�������ŵġ�������桱�ṹ�������ڹ�������˽����ҵ���з�չ�����ߣ��ܹ��������Ǵﵽ��չ��Ŀ�ꡣ�ҿ���սǰ�dz����ô���������ս��������ʷ��ѵ����ֵ�����Ǿ��裬��Ϊ�����֮ʦ��������ս�������������ȫ��ֻҪ�����κ����ɿ������ձ����ж������Ĺ��ң���Ȼ��С����������������������˵��κ�һ�����ܶ���֮��Ҳ���Ǽ����ܿ�������֮ɫ��ĵ����������ս��
Ȼ��������һ�ߵ�ȥ��������ζ�š������ˡ����ұ����ս˫��������ȫ��ͬ�ķ������������������˶����ij����ߡ���1955����ӡ����¡��bandung���״ι��ʴ��֮����ʼ���ô���������������ǰֳ��ʱ���ļ����������ӣ���ӡ�ȵ����³��ӡ����ռ�ŵ�����������������Լ����빲������Ӫ����˹������ͳ���еȡ��⼸λ��ʿ�����������ڶ���ǰֳ������������Ȩ����һ�㣬�����Լ���λΪ����������ɫ����������ߣ���������ʽ��������壩����������կ�Ļʼҷ��������壨royal��buddhist��socialism�����ڡ�������Ƕ�����������ijЩͬ���Ͽɣ�����Ը������շ��ṩ�ľ��������Ԯ������ԭ����Ϊ�棬��Ϊ��ս��ʼ���ڶ�������������ָ���һ�̣������㼱æ������ȥ�ķ�ֳ�����崫ͳ����ʼ�ڵ�������Ѱ��������Ϊ������Ȩ��֧�֣�������Ϊ���ԡ�������Ķ�������1958�����ǰ�ģ������ˡ������䡢�ͻ�˹̹���Լ����ʹ������µ����ʡ������Ĺ���ɡ�������Լ��֯����central��treaty��organization��cento���������ϡ���������Լ��֯����south��east��asia��treaty��organization��seato���еķ��ɱ���̩�����ͻ�˹̹������������֯������Ŀ�ģ�����Ϊ������ԡ���������Լ��֯��Ϊ�Ǹ��Է������������ľ�����ϵ������ǰ����֯ȴδ��������Ҫ���ã���1959��Ű���֮��ԭ�Է�������Ϊ���IJ�����Ȧ�������γ�����ͬ���������������ij�Ա����Ȼ��������������жԱ������ϴ���ʹ��ļ�����������¡ϵ�еķǹ��������ң���ʵ�ʼ�������������Ӫ�ĵ���������������һ�㣬��û���κ�ʵ�����յ��ж������Dz�����ۏ�볬�������ȫ����ŵĻ�ˮ����Ϊ�糯��ս����Խ��ս�������Ű͵���Σ��������ʾ�����г�ͻ���������ǽ���Զ��ս���ϵ�ù�ĵ�һ�ߡ�������Ӫ֮��Ľ��磨����ŷ�Ľ��ߣ�Խ�ȶ���һ��ǹ�����䣬��ͷ��Խ�п�����������ij����ɽͷ�������ij�صĴ����
Ȼ����������Ķ��ţ���Ȼ������������ع�����Ĺ�ϵ����ʱ�����������ȶ��������ƣ�ȴʼ������ȫ����ȫ�֡����������м����������������ع��еĽ��Ź�ϵ������������ս����������ɣ�������ѹ�������ݱ�ɳ��ڵij�ͻ�������¸õؼ�Ъ�Ե�ս���������������ж���ӡ�ȴδ�½�ı��������س�ͻ����żȻ������Դ�ڵ۹�������ȥǰ���⽫�����ָ�İ��ţ���ӡ�ȱ����ij�ͻ���棬���Ƚ���������ȫ�����ս֮�⣬��Ȼ�ͻ�˹̹һ��һ�����������������������һֱ��80�����������ս���������ͻ�˹̹����ͼʼ��δ�ܵóѣ��μ��ڰ˼���ʮ���£�����ˣ��õ����Ⱥ�������������ս����������֪����������٣�1962����ӡ����Ϊδ���߽������ս���з���ʤ����1965��ӡ��֮ս��ӡ�����ɴ�ʤ�����Լ�1971��ӡ�������ٴεij�ͻ���������Ƕ��ͻ�˹̹�����ϼ�������ӡ��֧���¶��������⼸��ս���У�����˫�������������Ե�������ͣ��ɫ�������ж�����ȴ����˸��룬��Ϊ����ֱ�ӹ�ϵ�źܶ������˰��ɫ�С������䣬���������µ����ʡ������ؽ������ϵĸ�������1952��İ�����50��60����������˺������ǡ�60��70������ϲ����������Լ�1979�����ʹ�������ά��Ȩ�ı��Ʒ����������Ǿ��»��������䣬��֤���õ������״���IJ��ȡ�
������ˣ���Щ�����Եij�ͻ���ڻ�����ȴ����սû�б�Ȼ�Ĺ�ϵ����һ��������ɫ������¹��ҵĹ����б����������������ɫ���պ�ȴ��λ��Ϊ��������Ҫ�����ѡ�������������������ŷ���˹���̵Ĺ��ң������·�߲������ң�������һ�����ϴ������������ɸõ������ѵ�ԭ������ɫ�е���̫���������ィ����һ����Ӣ����ͼ���Ϊ�����̫�˹��ң��Է��˾٣�ʹ��70��������̫��İ���˹̹����������ʧ����������������±�1948�����̫�˿�Ϊ�ࣩ��calvocoressi��1989��p��215������ɫ��Ϊ�ﵽ����������Ŀ�ģ�ÿ10����ս����1948�ꡢ1956�ꡢ1967�ꡢ1973�ꡢ1982�꣩����ʷ������ɫ��ǿ�н����������ж���ӽ���ǰ��������18������³ʿ�Ĺ��������Ҷ�����frederick���������ҴӰµ������ж�ȡ���������ǣ�silesia�����Ӵ�������ս������ȡ�ø����������Ըõص�����Ȩ������ս����������ɫ�н��Լ�������ж�������ǿ���һ֧����������ͬʱҲȡ���˺˹��ҵĵ�λ��������ȴ���ڹ���Զ���������������ȶ����ھӹ�ϵ����ס������������ڻ��������ж����صİ���˹̹�ˣ��������м��ߣ����������á��������壬��ʹ�ж������Ӵ˲��ٳ�Ϊ��սǰ�ڣ������䱬ը�Եľ���ȴһ���ǰ��
���������μ��ij�ͻ���ģ�Ҳʹ�ж�һ�صij�ͻ�������ϣ��������к�����˹�壬�Լ������䡢�������������Ĺ��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