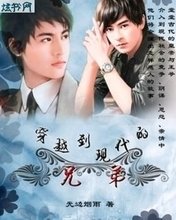极端的年代-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手可得——如果忽然想去尼泊尔充电一阵子——更是随时可弃之物。这种代沟现象,并不只限于工业国家,因为农民人口的大量减少,也在农工两代与人力机器之间,裂下一道断层深痕。法国老一辈的历史教授,都生长于每个法国孩童均来自农村或至少在乡间度过假期的时代,如今却发现自己得大费周章地向1979年的学生解释,挤奶女工的活儿是怎么回事,堆着粪堆肥料的农舍庭院又是什么模样。这道巨大代沟,甚至波及一向居于本世纪惊涛骇浪边缘的众多人口——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一向以来,政治上的各项骚动只是远远扫过他们。其中种种热闹纷扰,除了对个人生活造成很少影响的部分,他们都兴趣索然不予置评。可是如今,这份安静清闲却不再有了。
诚然,不论新事物的裙角是否再度掠扫他们而去,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比以往年轻了。在大多数出生率始终居高不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于20世纪下半期任何一个时期当中,都有五分之二到半数国民的年龄在14岁以下。不论他们家族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生活中传统网络的制约有多强大,新一代人口如此众多,两代之间在人生的经验期望上,无法不存在一道巨大的深沟。90年代初期,海外流放多年的南非政治人士重回祖国,虽然飘舞着同样的旗帜,同为南非国民大会党而效命,可是他们的心情,与南非各地城镇新起的年轻“同志”,却有着极大的不同。相反地,索韦托(soweto)的多数群众,这些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入狱后多年才出生的一代,除了把他当作一个象征或圣像之外,实在难有相通之处。就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国家的代沟其实比西方更大——因为后者的老少之间,至少还有永久性的制度,以及政治上的延续性为之相连。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3
。^生。网
3
青少年文化就广义而言,更成为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其内涵包括了风俗活动的规则,休闲方式的安排,以及日愈形成都市男女呼吸主要空间的商业艺术。因此这项文化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是通俗的、平民化的;一方面它却又是主张废弃道德的。这两点在个人行为上尤为显著,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外界的限制规范处于最低点。但在实际上,人人却又摆脱不了同辈及时尚的压力,众人的一致性反而不比以往为低——这一点,至少在同辈之间或次文化群体中是如此。
上流社会从“庶民百姓”中撷取灵感获得启发的事例,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当年法国有玛丽皇后(queenmarie antoinette)突发奇想,以假扮农家女挤奶为乐。这且不论,浪漫人士也对农村的民俗文化、民歌、民舞大为欣赏,崇拜不已。在他们时髦善感的同好之中,则有一批知识分子——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贫民生活突发幽情(nostalgiede la booue)。此外,尚有维多利亚的上流人物,特别喜欢跟社会阶级比自己低下的人发生关系,他们觉得此中趣味无穷——至于其对象的性别为何,则视个人喜好而定(这种心态直至20世纪末期的今日仍未绝灭)。在帝国时代,经由平民艺术的兴起,及大众市场性的娱乐精华——电影——这两项新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冲击之下,文化影响首次有系统地自下而上发动(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不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大众与商业娱乐的风向主流,主要仍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先导,或至少也以其名行之。古典的好莱坞电影界,毕竟是“受人尊敬”的行业;它颂扬的社会理想,遵循着美国强调“家庭价值”的路线;它揭橥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爱国情操的高尚口吻。诸如《安迪·哈代》(andy hardy,1937-1947)等“促进美国生活方式”的“好电影”成为好莱坞制片的道德标准模式(该片连出15集,曾因以上优良主题赢得一座金像奖)(halliwell 1988,p。321)。凡是与这个道德世界相违的作品一如早期的匪盗电影,即有将宵小之徒理想化的危险——好莱坞在追求票房之余,便得赶紧恢复这个小世界中的道德秩序。其实它的自我设限已经很严格了,好莱坞制作道德规范里规定(1934-1966年),银幕上的亲吻镜头(双唇紧闭式的亲吻),最多不得超过30秒。好莱坞最红最轰动的作品——比如《飘》(gone with the wind)——都是根据中产阶级一般人读物的通俗小说摄制。这些电影里描绘的文化世界,完全吻合萨克雷(thackeray)笔下的《名利场》(vanityfair),或罗斯丹(edmond rostand)《西哈诺》(cyrano debergerac)一剧中的众生相。只有那轻松歌舞剧或马戏团杂耍小丑出身的喜剧电影,才能坚持其凌乱无秩序的平民风格,不被这一股中产阶级之风所同化。可是到了30年代,连它也站不住脚了,在明灿亮丽百老汇大街型喜剧风格的压力之下溃退,也就是所谓的好莱坞“疯狂喜剧”(crazy edy)。
于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百老汇“音乐剧”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这种花团锦簇的音乐喜剧,以及点缀其间的舞曲歌谣,事实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的趣味——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爵士音乐的影响,此风是否还能成其气候。这些作品的写作对象,是纽约中产阶级的成年观众;其中的词情曲意,也都是为这一群自以为是都会新秀的男女而发。我们若将百老汇大家波特(cole porter)所作的词曲,与滚石乐团随便比较一下,即可发现两者之间大异其趣。好莱坞的黄金年代,与百老汇的黄金年代相互辉映,都建立在一种市井平民与体面人物共生的混合趣味之上。
50年代与众不同的新奇之处,在于上层与中层阶级的年轻男女——至少在对世界风气日起领导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青年中间——开始大量模仿并吸收都市低层社会的人,或被他们以为属于这一阶级者的行为事物,诸如音乐、衣着,甚至语言皆是,摇滚音乐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50年代中期,摇滚乐突然破空而出,从原本被美国唱片公司列入专以贫穷黑人为对象的“种族类”(race),或“蓝调类”(rhythm andblues)音乐当中,一跃脱颖而成全球年轻族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人青少年的世界语言。劳工阶层中的时髦小伙子,过去模仿上流社会的高级时尚,或向中产阶级次文化,如波希米亚式艺术家,暗自效仿——劳工阶级里的姑娘更擅此道。可是现在形势逆转,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凡夫俗子的年轻男女,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且反过来,开始领导贵族的时尚风骚。随着牛仔裤的锋头大健(男女皆然),巴黎的高级流行时装(haute couture)若不是暂时偃旗息鼓,就是干脆接受失败事实,挟带着自己的响亮名号,或直接或授权,下海做起大众市场的生意——附带一句,1965年,是法国女装业裤装产量超过裙装的第一年(veillon,p.6)。英国年轻的上流男女,纷纷脱去原本一出口即可证明自己高级正确无误的口音,改用一种接近伦敦一带工人阶级的腔调。体面的上等男子——上等女子也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也开始模仿劳动工人、士兵等职业的粗犷口吻,喜欢偶尔在说话当中带起脏字眼。这种说粗话代表男性气概的作风,原本绝对是受人鄙夷的下流行为。文艺界也绝不居于人后:某位颇有才气的剧评家,即在广播中用起“干”这个脏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童话世界的历史上,灰姑娘化身的美女,从此不再需要凭华服丽饰于舞会中夺魁了。
西方世界中上等阶层青年男女的品味,忽然一下子大转弯,改向平民风格涌去——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这种趋势,巴西的知识分子即颌一时风骚,大力推动原源自平民的“桑巴舞”——数年之后,则有中产阶级的学生,涌向革命理念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两者之间,若有似无,也许有,也许没有连带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时尚流行却常常有预言作用。自由主义气息重新点燃之下,同性恋次文化慢慢抬头,对时装流行及艺术风尚起了重大的带头作用,影响所及,在年轻男性中间尤为显著。然而不论是性别取向的改变,或喜好品味的日趋平民化,两者都可看作是年轻一代向父母辈价值观反抗的手段;更精确一点说,这是他们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为自己摸索方向的新语言方式。
新青少年文化中带有的强烈废弃道德意识,一旦化为理性语言,其精神面表达尤为清晰,如1968年5月巴黎的口号:“严禁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以及作风激烈的美国流行歌手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没在牢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wiener,1984,p.204)照传统的想法看来,乍听之下,这些好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宣言,其实不然,他们想要废弃的压制对象,其实跟法律也没有半点关系。政治法律,都不是他们反抗的目标。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正如同1968年5月的另一句口号:“我把我的欲望当真,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真实性。”(katsiaficas,1987,p.101)。他们的欲望,也许出之以示威、群体、运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有时也许甚至造成群众暴动的效果。可是这一切表象的核心,却是强烈的主观感受。“我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成为新一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口号,其效果可能也是多年激进化中持续最久的一环。其中意义,不只限于政治行为是以个人动机成就为满足,更指出政治面的成功标准,系于其对个人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所谓政治的定义很简单:“凡是让我烦心的事,都可以算作政治。”70年代一本书的书名,便将此中奥秘一语道破:《胖——也是女权主义的论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orbach,1978)。
1968年5月还有一句口号:“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这句话要是落在革命前辈列宁耳朵里,甚至连当年因主张混交而被列宁痛斥的维也纳共产党人菲舍尔听了必定也会大惑不解(zetkin,1986,pp.28ff)。反之,60和70年代的新一代,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激进青年,也一定不能了解布莱希特笔下,早年献身共产国际之士的心情与作为——即奔走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连做爱时脑子里也想着心事。”(brecht,1976,ii p.722)。到了60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之际的感受。做爱与搞革命纠缠不清,难分难解。
因此,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相辅相成,是为一体的两面了。而其中最能够打破国家、父母、邻里加诸我们身上的限制、法律、习惯的,莫过于性与毒品。不过性这件事,源远流长,其五花八门多样之处,由来已久,其实用不着年轻人费心发掘。尽管保守派诗人忧心忡忡地吟道:“性交,始于1963。”(larkin,1988,p.167),可是这句话并不表示,在60年代以前性交是什么稀奇大事。诗人的真意,在于性交一事的公众性质与意义从此开始发生改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为佐证,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一书的解禁;一是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问世。然而,对于以前一向遭到严禁的事物,反抗的姿态其实不难表明;凡是在过去受到容忍的事物,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容忍——如女子的同性恋关系——就特别需要点明出来,如今正有一种反抗的姿态产生。因此同性恋者公开现身,表明态度,便变得特别重要。可是吸毒一事却正相反,除了烟酒是广为社会接受的癖好而外,麻醉药物一向仅限于小团体与次文化中(虽然这次文化的分布,三教九流都有),并没有包容性的法令。毒品的风行,当然不只是一种反抗姿态,因为吸食本身带来的感官刺激便有莫大的吸引力。可是正因为吸毒是一件非法行为(通常也属于一种社交行为),吸毒,便不但具有高度挑衅叛逆的痛快意味,更使人有高高在上,不把那些严令禁止者看在眼里的满足心理。西方年轻人最盛行吸食的毒品是大麻(marihuana)——其实大麻对人体的伤害恐怕还不及烟酒为害之烈——此事更证明其中所涉心理的微妙。60年代,在摇滚歌迷和激进学生汇集的美国疯狂两岸,吸食毒品与示威抗议往往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事物。
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