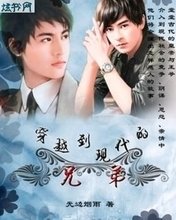极端的年代-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8年间,纳粹德国之所以令人咋舌地顺利兴起,几乎未曾受到任何抵制,极可能便肇因于此。
尤有甚者,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情节,加上经济力量的种种缘由,各种政府的世界观也很有差异。比如以美日两国为例,它们的重心分别在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的局势与其实在没有什么重大相干。对于英国而言,欧洲大陆的风云也同样无足轻重,因为它一心仍然看重于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并以维持全球海上霸权的战略为主——虽然在事实上,英国国势已经大衰,其两重目的一重也难以维持。至于东欧各国身处德俄两强之间,情势使然,国策自然受其地理位置左右——尤其在后来的事实发展之下,西方各国显然不能保护它们时更是如此。其中更有一些国家,已于1917年后自俄国取得部分土地;因此它们虽然反德,却也不愿见到任何抗德的联盟行动把俄国势力再度带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内。但是最后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给法西斯有效打击的联合行动,却少不了苏联这一份力量。再从经济角度观之,英国等国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经发动过一场远超自己财力物力所及的大战,如今再度面对重整军备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却步。简而言之,各国虽然都认识到轴心势力的存在确属一大威胁,但是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却有一段极大的距离。
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扩大了这道“知易行难”的鸿沟(依照自由民主观念的定义,天生便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止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当局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如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外交方针。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二战之外。因此除此二事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把美国投入这场战争。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上下众人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二战的牺牲为大(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可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二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主张“拒绝作战”权利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反战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如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头目。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党魁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必要的军事手段,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可以讨论。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颤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劳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解决,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说,若想空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造成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的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不但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实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我们如何策划种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身为法西斯的反对者,我们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或不决)——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政客们对选举的计较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失血地步,国力之弱小,可能比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共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止住德军的攻击(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到1933年,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战略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在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理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
英法两国都深知本身的国力太弱,实不足维持于1919年建立的国际政治现状,以期配合自己的需要。它们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局势极其不稳,继续维持实在难上加难。再战一场,非但无益,徒招更大损失。因此眼前现实的上上之策,便是与再度兴起的德国磋商,以求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欧洲秩序。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便意味着向日渐强大的德国让步。不幸的是,新复兴的德意志帝国,却掌握在黩武独夫希特勒的手中。
所谓“绥靖”政策,自1939年以来即被报界口诛笔伐,可以说声名狼藉。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许多西方政客眼中看来极有道理。这些人心里并不十分反对德国,在原则上也没有强烈反对法西斯的热情。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大陆的版图更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极不熟悉的遥远国度”(张伯伦语,1938年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发生的变换,可不是什么令英国人血压升高的大事。(法国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于德国的举动,都使得法国人神经紧张。德国人迟早会跟法国作对,可是法国弱得很,哪里禁得起。)但是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定会使英国经济倾家荡产,大英帝国必也解散大半。后来事实证明,果如所料。虽然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主义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可言。
然而事实发展显示,希特勒德国的国家主义根本不讲道理,其政策目标既无理性又无止境,与之妥协谈判,无异与虎谋皮。扩张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这套系统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除此一途,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纳粹德国的意图是由意识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能;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主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时,那群姑息主义者仍不死心,抱着他们莫名的和平幻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发生1939年3月到9月间那场黑色荒谬的悲喜剧。可笑的一幕,终于以一场大战宣告结束——这却是一场其时其地,没有一个人想打的战争(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英法两国,则被莫名其妙地投入这场战事,一直到1940年德人发动闪击战将它们摧枯拉朽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延后,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一张废纸。伦敦、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当此时刻,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并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张伯伦会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结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国向德宣战。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各国政治人物想要一战,却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的东进政策太过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原本对反抗法西斯一事无所谓的广大群众,现在一举动员,起而相抗,这种形势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根本上来说,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语气,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虽不情愿,也只有被迫从之。英国政府的政策既转了方向,法国政府别无他计,也只有立即跟进,追随自己这个唯一还算有点办法的盟友。于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英国国民同仇敌忾,决意与希特勒作殊死战,不再分歧不合——可是为时已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铁蹄迅速无情,踏进波兰,并与斯大林瓜分该国。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后患已定。一场德国大唱独脚戏,英法只能虚张声势的“假战”(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后到来。
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管哪一种现实政治的言词,都无法再解释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开战之势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形势?——唯一可做的事,应该只有加紧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