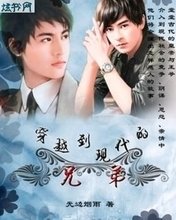极端的年代-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意志,东有混乱的俄罗斯,终于遏止不住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流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货币单位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其他的例子虽然没有这么极端,后果却同样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欢向小辈讲一个故事:话说奥国通货大膨胀期间,他的保险单刚好到期。于是将之兑现了好大一笔款子,可是这批一文不值的通货,只够他在最爱光顾的餐馆喝杯饮料而已。
长话短说,总之,在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一扫而空,企业资本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覆没。不过在波兰、匈牙利及奥地利诸国,原有的通货总算还保留了一丁点少得可怜的价值。这段经历,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中欧地区因此造就了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如何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二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年),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及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指出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滑落(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金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金输出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金开始撤退,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如此相信或假装如此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回合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环经济指数出现下落的现象,都使其他指数的跌落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落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推往天文数字。)
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工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掌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于是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大英帝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震撼。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至于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但是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补贴之道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只为自给自用而生产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小农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挽救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本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当年的大萧条,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经济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小农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下田吃米饭),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率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任何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年),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率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性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需要保障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的危险,也要应付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口,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
大量失业的结果,对工业国家政局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最直接最显著的意义就是大量失业。虽然经济史家指出(逻辑也同样证明),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战之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劳工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成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weber,i,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二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难迷乱的感觉,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是什么方向——或左或右——总有个政治手段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欲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解决的手段,技穷之下,经济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短期内为了立即解决国内的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年),同时间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定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i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者,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snyder,1940)。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出头的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一页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派经济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如此。象征意味更重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