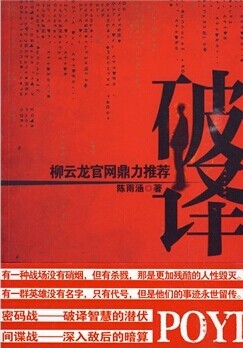破译圣经-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这并不是说诺查丹玛斯在大写预言诗的当时,就毫不存在教会进行宗教迫害的危险,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借助了王权的庇护来避免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诺查丹玛斯立于现实的预言总是与王室有关的主要原因;同时,诺查丹玛斯所作出的那些出于假想的最大预言,总是在挑战距离当时足足有400年之遥20世纪!显然,以预言的方式来挑战遥远的未来世界,对任何一位预言家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最为安全的一种举动。Ⅷ。40 寿终正寝的千年预言
当对于人的命运进行的预言,由神如斯说转变为人如斯说时,进行预言的预言家的身份,也就从代神传言者,摇身一变而成为言为心声者,因而对于神与人分离的宗教预言家来说,由于其始终保持着与神的界限,反而容易保留着人的形象;然而对于以人的面目出现的世俗预言家来说,则因其容易流于神化,最后将可能出现人与神之间难以分辨的结局,并走向新的造神运动,从而导致人的命运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样的伊甸园游戏的长存,在使智慧之树夭亡的同时,也使生命之树枯萎。
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集《请世纪》流入法兰西宫廷之后,引起强烈反应的是卡特琳娜王后,因为在这些预言中再次出现了关于国王之死的预言,而王后关心自己7个儿子的命运,于是在王宫召见诺查丹玛斯,由于没有留下记录,据说诺查丹玛斯对王后说过“您的儿子都能成为国王”,可是后来的事实是王后只有4个儿子成为国王,即使真有此预言,看来也是真假参半。在所有关于国王命运的预言之中,精确到死亡时间与死亡形式都丝毫不差的,是死于1559年7月10日那天的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他因为与绰号叫做狮子的臣下比试枪法,被对方的枪尖从黄金头盔的缝隙穿过刺中眼睛而死。
不过,如果从《诸世纪》的出版情况来看,最初是分成两部分的,分别在1555年和1568年印刷发行,而据说在1555年出版的那一部分,上面连印刷日期都没有,再加上1566年诺查丹玛斯去世,因而很可能《诸世纪》一书曾在他的弟子杰维尼整理出版的过程经过了合乎史实的某种修改,从而使立于现实的预言转换成基于历史的预言。这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提高了《诸世纪》预言的准确性,但是却开启了对于《诸世纪》之中的预言进行历史附会的恶劣之风。
从此以后,这一风气愈演愈烈,据说甚至用一首预言诗——“欧罗巴西部最深处。”贫穷家里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他靠三寸不烂之舌让许多人如坠迷雾。”他的名声扬遍东方国度“——便可以一箭双雕地射中所谓历史造就的两个如此相似的人物:拿破仑与希特勒。但是,只需稍微细心一点就不难发现,这一附会至少有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拿破仑出生在科西嘉岛上,而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两个地方都不是欧罗巴西部的最深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预言像语言一样,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内重复地使用,还能够是预言吗?然而,像这样可以进行一箭双雕式解说的预言诗,在《诸世纪》中还有很多。
事实上,对《诸世纪》进行解说的专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那些小预言家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不少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或者是由于“背景材料不足,难以将它同某个史实相联系”,或者仅仅是“一首十分普通的四行诗,大概是预测了一个阴谋,我们从诗中难以推测”,或者是因为“不明晰的地方太多,这给破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等等。其中,关于一位国王之死的预言诗,即“他的逝世。”来源于雄狮十字架雏鹫的王冠“。据说”此诗是《诸世纪》中令专家倍感头痛的预言诗之一,历史上持有这样王冠的国王,多如恒河沙粒,大多数都符合本诗的描述,要将他们一一区分排除,找出真正的'主角',是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不过,这种情形的出现,正好表明如果是将历史往预言上硬贴,只能是白费力气,因为预言除了预示未来发生的事件之外,还可以预告对于未来的希望,比如说新教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崛起,而诺查丹玛斯却希望通过武力,来使“世界因为宗教分离而乱七八糟”的现状得到制止。这就在于诺查丹玛斯是倾向于王权政治的,因而他预言“当世界基督教国家没落之时”,应该出现一位罗马皇帝一样的国王,“月亮之王给亚平宁带来和平”,重建统一的新罗马帝国。对于这个预言的落空,连专家也认为“然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又是诺查丹玛斯的一厢情愿而已”。不过,如果硬是要用历史来证明这一预言的话,“欧盟”及“欧元”的出现,不是已经实现了诺查丹玛斯的梦想了吗?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后来者的专家们,往往是将其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和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解说的。
根据解说,不仅法国大革命与之有关:“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监狱发生暴动,革命志士们就是从《诸世纪》中得到感悟的。”根据是“在狱中的桌子上有一部分供阅读用的《诸世纪》影印件,被关押的囚犯们在十天中相互传阅,以此坚定了行动成功的信心”;而且第三帝国的兴起也与之有关:“1939年秋,德国向欧洲宣战后不久,戈培尔博士夫人读着一位名叫诺查丹玛斯的人所写的若干预言,兴奋不已,以致于不得不叫醒丈夫,共同仔细研读,戈培尔亦为之震惊,随即命令宣传部雇来一位名叫恩斯特·克拉夫特的瑞士籍占星术师,命其利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资料,对所占领的欧洲战区展开心理扰乱战”。
在这些有关的预言诗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伟大的希勒恩”将“成为世界主宰”的那首预言诗,预言他将“被人喜爱。”畏惧恐怖烟消云散。“对他的赞誉高过云天。”他很满意圣者的称号“。戈培尔夫妇的兴奋,也就在于这一关于”伟大的希勒恩“的预言,无疑将实现在他们所效忠的元首希特勒身上,从而导致了在德国宣传部门与英国情报机关之间的一场创纪录的心理大战:1940年,德军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撒下英语和法语版本的《诸世纪》选集,预言希特勒的一定胜利;而1943年,英军飞机在欧洲大陆撒下德语版本的《诸世纪》选辑,预言希特勒的必然失败。
其实,如何对这首预言“伟大的希勒恩”降临的四行诗进行解说,专家们的意见倒是比较一致的:“在预言诗中,'希勒恩'受到的'赞誉高过云天',且被封为'圣者',简直可与耶稣基督媲美。这暗示他也许是影响力与基督教旗鼓相当的新兴宗教的领袖。因此,研究专家们将他比喻为'伪基督'”。事实上,尽管诺查丹玛斯对于基督教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没有多少好感,但是,他不可能杜绝基督教教义对于自己的影响,这是因为诺查丹玛斯毕竟是在基督教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文化环境之中生长与生活的。
因此,这一宗教的影响,不仅仅是出现在他对于救世主的圣者“伟大的希勒恩”的一次预言上,更是发生在对于世界末日到来的诸多预言上,具有代表性的预言是这样的:“1999年7月为使安哥鲁莫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尽管专家们对于该诗除了”1999年7月“之外的诗句众说纷坛,难以破译,但是,据说”这首诗所涉及到的时间的重要性,诺查丹玛斯早就充分认识到了。他的其他预言诗,以半开玩笑的调侃式的语气随便说来,似乎是故意要让后人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去猜测不休。但这首诗却是例外,其中预测事件发生的日期说得相当明确,使人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预言诗呢?是不是“可以认为,诺查丹玛斯在这首诗里,再也没有使用他那惯用的闪烁其词故意作弄人的手法,出于一位预言家的责任感,他这是在对我们这一代人作出极其慎重的警告”呢?只要对于诺查丹玛斯在世时期的整个文化背景进行考察,也许就会给出另外一种答案来。
其实,问题的答案还得从诺查丹玛斯自己的预言诗里面去寻找:在那首据说是预言了“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的诗中他曾这样写到“两座城市邻近海港。”前所未有的灾难从天而降。“饥饿横行瘟疫猖獗魔剑追赶。”他们向天神求救,哭喊之声震天响“。显然,诺查丹玛斯并没有故弄玄虚,他只不过描写了自己当年在里昂等地行医时所看到的大瘟疫流行的惨状,借以警告众人不要放弃对于神的信仰,以免遭到惩罚。如果说立于现实的预言并没有作弄人,那么,出于假想的预言,特别是面对”1999年7月“这样明确无误的诗句,诺查丹玛斯究竟要表达些什么东西,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里,“1999年7月”不仅包含着与《圣经》阐释之中的神圣数字“l”、“3”、“7”直接相关的数字,体现出上帝的意志及创造;而且还包容着与基督教神学之中的“千禧年”之说直接相关的年份——公元1999年7月,将是基督耶稣与基督耶稣及其圣徒拯救世界各1000年,总共2000年即将结束的日子,它意味着在两千年期满之后,魔鬼将被释放,恶人复活,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由上帝进行最后的审判。因此,1999年7月,既是预示着善人即将进入天国的日子,上帝的创造物会“获得幸福生活”,又是预告着恶人即将进入地狱的日子,复活的恶人,甚至从天而降的魔鬼“恐怖大王”都将难逃此厄运。
所有这一切都在显示出来自《圣经》的'启示文学“传统对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集《诸世纪》发生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但丁的《神曲》里面则更为鲜明、更为突出。这首先与但丁和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家身份有关,一个是从世俗生活出发的宗教预言家,一个是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世俗预言家;这其次与但丁和诺查丹玛斯的生活年代有关,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盛极将衰的日子里,一个生活在中世纪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中”启示文学“的传统对于不同时期中的不同个人,已经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并且还将继续影响到后来者,因而应该对《圣经》中”启示文学“的传统进行追寻。
“启示文学”并非是文学的一种,而是在《圣经》的有关文本之中,主要通过种种异象的出现,来着重传达上帝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特别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以促使信徒坚守信仰,等待上帝的拯救与审判。所以,启示文学是借助文学性的象征或隐喻手段来显示上帝旨意的,具有宗教启示性的未来预言,要言之,启示文学就是特指宗教预言。虽然《圣经》里的启示文学因素散见于众多典籍的文本之中,但是,集中体现启示文学特征,并具有代表性的典籍,分别是《圣经·旧约》中的《但以理书》,与《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
从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但以理书》,到公元1世纪据说由约翰写成的《启示录》,在将近3个世纪之中,逐渐形成了《圣经》中特有的启示文学传统,出现了众多的各种文本,并且以异象来作为其特有的标记,为进行对于这一传统的追寻提供了路标。如果这一追寻从对《诸世纪》与《神曲》的文本溯源来逆向展开,就可以看到陆续出现了不少的异象,而且越是时间推前,文本之中的种种异象就越来越多,在《圣经·新约》的《启示录》里面达到了颠峰。
《启示录》之中的异象空前绝后而又集大成式地出现,是与《圣经·旧约》,主要是与《但以理书》的影响分不开的,特别是与以怪兽形象出现的异象直接联系着:“但以理说:'我夜里看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又有一兽如熊,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有大铁牙,头上有十角'”,然后,又明白了“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征兆。同时,“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又被告知“有一个像人子的”将拥有永远的权柄与国度,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并把“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这实际上是关于千禧年预言的雏形。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因而《但以理书》之中的异象在《启录》里面由约翰改写:
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