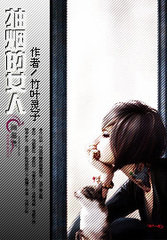大校的女儿-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决定给彭澄写信,不再徒劳地等。提起笔来心下茫然:写什么?不能再说彭湛,真的假的都不想、不能再说。关于她的那首诗我也无话可说:我已付印了十几份寄往了十几处,有熟人的地方,还写了信,信中恳请他们帮我把这诗发了,并且厚着脸皮,在信尾处做出暧昧的暗示:“友情后补。”但他们无一不是铁面无私,铁面无情,好歹回了信——没有熟人的编辑部绝无信来,发去的诗如同泥牛入海——那信还不如不回,“思想肤浅,情感做作,语言缺乏意境”。我很清楚那诗的稚嫩,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但总想还不至于一无是处吧,首先,它不乏真诚。只可惜这真诚又很难为外人——我是说没有身临其境的人——理解。不得不承认,还是功夫不到家,还是不能够将一些看似纯个人的感受有效传递,直至能引起受众的共鸣。人人的感受,本应相通,做不到这点,是写作者的失败。可是,话说回来,他们发过的那些诗,就一定都比彭澄的高明吗?比起其中某些矫情的、故作晦涩深沉的莫名其妙的文字垃圾,彭澄的《 墓地里只有一个她 》至少明快,健康,好懂。怎么就不能腾出一点地儿来给她发了,给她一个鼓励,给她一点希望?人需要被鼓励被肯定,彭澄就此长足进步也未可知,文坛的一颗新星就此冉冉升起也未可知。而且,在信中我也不是没跟那些熟人编辑们介绍彭澄的情况,二十三岁,女兵,在青藏高原上。现在想,我的这些介绍同彭澄的诗一样,是失败的,我没有能够将我感受到的彭澄的处境心境传递给那些不熟悉她的人们,也许,还给了他们一种相反的错觉:浪漫,神秘,奇异,得天独厚?要这样,更是害了彭澄,使她的那诗不仅是肤浅、做作、缺乏意境了,而且是无病呻吟,是小女子的顾影自怜,自恋,是吃饱了没事干之后的一种消遣。
我能跟彭澄说的,似乎只有海辰了。
窗前的杨树树冠如盖,叶片墨绿、硕大,阵风吹过,沙沙沙沙,蝉儿在其间声嘶力竭此起彼伏;身后的大床上,小梅正在和海辰说话。海辰还没有学会成人的语言,只好由小梅倒退回去,说婴儿话。两个人正聊得起劲,咿咿呀呀,有问有答,嘻嘻哈哈。
这时候的海辰很有一些人的样子了,所谓人的样子,是指他不再是整天吃了睡、睡了吃了,他已开始有着人的追求人的特点了。比如,在刚开始给他添加辅食时,我是将分别有着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的数种食品一块捣碎,搅拌,烧煮,煮出一团说不清颜色的糊糊,喂他,小梅对此颇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多说什么,毕竟孩子不是她的。但当有一次看到我居然能将蛋黄、馒头、葡萄、青椒这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弄碎了,再和上牛奶一起煮时,还是忍不住了,替海辰打抱不平道:“啧啧啧!这还叫饭吗?纯粹是饲料。”“配方饲料。”我为她做着补充,得意洋洋,自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实际、科学,值得大加推广。小梅道:“你以为是喂牲口喂动物哪!”我道:“你以为是喂什么?”小梅说不过我,便不跟我说,跟海辰说,举着碗高声地道:“海辰,来,咱们吃猪食了!”惜乎海辰真的就吃,像一头真正的小猪,只要饿了,给甚吃甚,全不管小梅作何想法。只是好光景维持了不过月余,他便开始转变立场,拒食“猪食”,到后来,怎么哄怎么喂都不行,小嘴紧闭,左右摆头躲着已碰到了嘴唇的勺子——我敢肯定这就是人类将“摇头”定为“拒绝”之意的起源——如果遇上我和小梅也在吃饭,他就会伸出小手去抓我们的饭菜。每到这时,小梅会意味深长地瞥我一眼,什么都不说,起身去厨房,为海辰做“饭”,花出数倍于我做“猪食”的时间力气,把同样一堆东西做得黄是黄、白是白、红是红、绿是绿,花里胡哨令海辰大悦,也令我讪讪,也感慨:这就开始懂得追求饮食的色香味了吗?说长,就长得这样大了吗?
也开始有了精神追求的倾向。
睡足了一大觉醒来,哼哼唧唧地要求人陪,我顺手将一只橡皮鸭塞给他,他不要,小胳膊一挥打到了地上。小梅拾起鸭子,放在了大床的另一头,他两眼便突然放光,骨碌一下,仰卧改为俯卧,直向鸭子而去。其时他刚刚会爬,严格说,是半会:两腿一动不动拖在后面,只凭小胳膊撑着身体一下一下往前面蹭,那姿势有点像士兵的匍匐前进,却因了腿的不会动,要更艰苦些。他却不以为苦兴致勃勃,头使劲高抬,眼紧盯目标,一步一步,相当执著。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努力——确是千辛万苦,小胳膊肘都因此被凉席磨得通红——终于,他拿到了早先给都不要的那只鸭子,并因此而眉开眼笑。追求过程胜似追求结果,典型的人的精神特征。
还有了审美意识。
小梅出去买菜,心血来潮烫了一个当时流行的“爆炸头”回来,难看至极。我说她,她不服,把正在床上玩的海辰抱了过来,让其裁判:“海辰,看,梅姨的头是不是好看?”乍开始,海辰被眼前这颗陌生而难看的头吓得愣住,待认出了是小梅,神情立刻严肃,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就伸出两只小手掌推她,这意思已非常明确,小梅却不甘心,死抱着人家不肯撒手,直惹得海辰要哭。一俟摆脱了纠缠回到床上,小家伙立刻背转身去,决不肯再看那头一眼;小梅却不知趣,一绕,又绕到了海辰脸前,逼得孩子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一头扎在了被窝垛上,把自己的小脸严严实实藏将起来,以让那客观世界在主观视野里消失。当时我在,目睹了整个过程。就是从那以后,在海辰面前我开始注意检点自己的服饰。以前从来不。就像人们从来不会在乎在一个小动物眼里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就跟彭澄说海辰,说他的上述表现,详详细细不厌其烦,写了满满的七大张纸,直到自觉也算交代得过去了,至少在长度上,才住了笔。这封信为保险我贴了三张八分邮票。
……
彭澄的诗终于得以发表,数家报刊同时刊出,全文,一字没动,包括题目:《 墓地里只有一个她 》。他们——那些苛刻的资深的编辑们——为什么不给动一动,是想彻彻底底保持住它的原汁原味吗?
我看着报纸上印成了铅字的那诗,不知为什么,印成了铅字后就觉着好了许多似的。同时,数家报刊不约而同将作者彭澄的名字用一个黑框框起,不约而同在诗前、在框了黑框的作者名字后,加了一段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这样写道:
该诗作者是驻守西藏高原的一名女兵,一个月前,在执行任务中车祸牺牲以身殉职,时年二十三岁。现将这首作者生前寄给我编辑部的诗作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编者按语的内容是我提供的。
彭澄乘车下部队巡诊,一车六人,翻了车。彭澄曾多次跟我描述过汽车在冰雪盘山路上行驶的惊险,描述过彼时她心中的恐惧,她将那恐惧化作了一首美丽的诗,这诗却因过于美丽了而不被认可。六个人除彭澄外包括司机都还活着,伤势最重的,是手腕腕骨骨折。彭澄也是骨折,却折在了颈椎,当场就停止了心跳呼吸,没有给她同车的战友们留下一丝丝抢救的余地。但战友们还是按照所有抢救程序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的她实施了全力抢救,气管插管,胸外按摩,口对口呼吸……
我知道这些情况时,彭澄早已化作一缕轻云融入了西藏高原那无尽的苍穹。是彭湛告诉我的,在电话里。我给他打的电话。那是一个下午,当发现仍无彭澄的信时,我再也沉不住气了,向小梅交代了一下海辰的事,骑上车便去了邮局,打长途电话。
彭湛在家,声音很远,我大声地道:“彭湛吗?我韩琳!”那边一下子便没有了动静,我更紧地握住话筒,更大声地:“喂!彭湛!”
“干吗?”
态度非常生硬,生硬到令人不解,令人不能不问:“你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
“最近彭澄……”我想说的是,“最近彭澄给你写信了没有”,彭湛没容我说完。我刚说出了彭澄的名字,他便开始说了,就是那些有关彭澄出事的话,说得很快,一口气,语调平板。他去过西藏一趟,部队给他发了电报,他是彭澄当然的唯一的亲人——意识到这点,处在极度震惊痛楚中的我仍是感到了一种新的创痛。
“……什么时候的事?”他说完后,我轻声问。
“四月二十九号。”
“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大叫。
嘟、嘟、嘟,电话断了。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个意外,马上重拨,通了,有人接了,我刚“喂”了一声,即刻又被挂断。再拨,再就没有人接了。我不甘心,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重重地拨着那组电话号码,疯子一般,直到引起了邮局工作人员的注意,走过来干涉制止了我。
后来,见面时,我就此事质问彭湛,他一下子转过了身去,背对了我,一言不发。片刻后,肩背部开始剧烈颤动。我意识到,他哭了——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在我面前哭过,之后也没有——同时意识到,这会儿假如不是面对面,是通电话,他一定又会把电话挂了。于是,我走过去,在他身后站住,伸出两手轻轻抱住了他的肩,非此我无法传递我的歉意,我的理解,我的与他相同的情感。感到他没有想到,屏息静气了几秒,猛地回转身来紧紧抱住了我——仿佛无助中的儿子抱住他的母亲,仿佛一个落难者抱住另一个落难者——他抱住了我,而后,说了,泪水阻塞着他的鼻腔、喉管,使他的诉说时断时续。
“……她躺在那里,像是睡了,还是梳的短头发,可能是才剪了不久,也就刚、刚……刚齐耳垂儿……”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偶像啊,
永远明亮的眼睛永远飞扬的短发。
盯着终于印成了铅字的彭澄的诗,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读下去,读完了这份报纸上的,再换另一份报上的读,仍然是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阳光从窗外进来,倾泻在印有彭澄的诗的报纸上,把报纸晒得烫手。已是夏季了,冬季却好像就在昨天,她给海辰上户口回来,带着一团寒气,一脸伤心……
那天在邮局与彭湛通完话,我没有马上回家,就在邮局里给各编辑部写信通报彭澄的情况,以便写完后能马上发走。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为那个女孩儿做一点什么;也不知道我正干着的这件事,对她还有什么意义。但是假如让我什么都不干,就这样无所作为两手空空地离开,回家,我怕我会憋死。彭湛的电话打不通,除了彭湛,我还有什么渠道能把淤积堵塞在胸口的那团沉闷疏散出去?在遭到邮局工作人员的严厉制止后,有好一会儿,我怔怔地站在邮局的地当中,无依无靠没着没落呆若木鸡。是在突然之间想起了那些也算与彭澄有过某种关系的编辑部的,在想起他们的那一瞬间,心里头竟涌上了一丝恶狠狠的快意:你们不是说她的诗思想肤浅情感做作吗?好,现在她用生命为它做注释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还想要什么?!……一度凝滞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心激跳,脸发烫,情绪激昂大脑清楚,就地买了纸,借了笔,写信。一笔一画,一封一封,我站在邮局的柜台前头都不抬,一口气写了十几封内容相同的信,分别折好,放进信封,贴上邮票,再看着它们由邮筒扁扁宽宽的嘴里滑落进去,郁闷的呼吸才好像通畅了一点,独自承受着的沉重才好像被转嫁了一些出去。……我离开邮局,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家里走,慢慢地想到,我所做的这件事对彭澄毫无意义,她不需要,她已经超脱了人世间的这一切高高在上,自由,空灵,飘逸。我做的这事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活着的人自己……
“哎,我说,别看了,该给海辰洗洗睡了。”
是小梅,抱着海辰站在我的身后。也许是她感到了某种异样,一手抱海辰一手在我看的东西里扒拉了扒拉,却没发现什么。我没有告诉她彭澄的事,她不熟悉彭澄,要说就得从头说起,那过程我无法忍受。我起身,对小梅笑笑,接过海辰去了卫生间。小梅去厨房收拾我们俩的午饭。我们通常在海辰睡了后吃午饭,以能吃得安静、踏实一点。
我给海辰洗澡。海辰坐在澡盆里——真正的澡盆,一个比他身体长许多的红色椭圆形澡盆,再不是彭澄给他用的我那个脚盆了——小脖子小脊背硬朗朗地挺着,在这样大的澡盆里都不必再担心他会被淹死。他极喜欢洗澡,喜欢用两只小手用力拍打水面制造出高高的水花,倘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