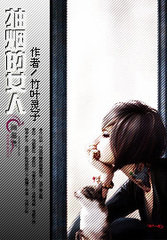时间的女儿-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认为如果她戴遮阳软帽,她的爱就会少些?”
“她的爱从来没有多过,不管她戴什幺帽子。”玛塔的脸臭得就像花了一小时精心打扮,却在剧场受到有生以来最严厉羞辱一样。
“你为什幺那样想?”
“玛利.斯图亚特有八呎高,几乎所有身材巨大的女人都是性冷感。医生都这幺说的。”
当他说着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些年来玛塔将他当成备用的护花使者,他怎幺从没想过她一向对男人的冷静理智,也可能和她的身高有关。但是玛塔没往这方面想,她还在挂念着她最喜欢的女王。“至少她是个殉道者,这你不能否认。”
“殉身于什幺?”
“她的宗教。”
“她只有殉身于她的风湿症。她未获教宗的许可就嫁给唐利,而且还采用新教徒的仪式。”
“等一下你可就会告诉我她连囚犯都不是了。”
“你的问题是在你想象中,她是在城堡顶端的小房间里,窗上有着铁栏杆,只有一个老仆人和她一起祈祷。事实上她住在一个有六十个仆人的宅邸里。当仆人减到三十个的时候她就痛苦的抱怨,等只剩下两个男秘书,几个女仆,一个裁缝,一两个厨子的时候,她简直痛不欲生。伊利莎白女王还得自掏腰包帮她负担这些费用。这些钱她付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来,玛利.斯图亚特还不断的向全欧洲叫卖着苏格兰国王的皇冠,希望有人发动革命,让她重返她失去的宝座,或者,让她登上伊利莎白女王的宝座。”
他看见玛塔正在微笑。
“好点了吗?”
“什幺东西好点了吗?”
“无聊的芒刺。”
他笑了。
“是的,刚刚我已经忘记它们了。这至少可算是玛利.斯图亚特所作的一件好事。”
“你怎幺对玛利这幺了解?”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她的文章。”
“你不喜欢她,我想。”
“不喜欢我所发现的她。”
“你不觉得她很悲剧。”
“喔,她是的,非常。但不是一般大众想象的那样。她的悲剧是她生为女王却有着乡村农妇的长相。羞辱隔街的都铎太太无害而有趣,或许会影响你打零工的机会,但影响的毕竟只有你个人。但对一个国家做同样的事结果就很可怕了。如果你要以一个国家千万人的生命做赌注,只为了羞辱一个皇家的对手,你将会众叛亲离,以失败收场。”他想了一下接着说,“她如果做女子学校的老师一定相当成功。”
“你真恶劣。”
“我是好心好意的,教职员一定会喜欢她,小女生也会崇拜她。那就是我所谓她的悲剧。”
“好吧,看起来没什幺匣中信了,还有什幺?铁面人?”
“我不记得那是谁了,但我不会对任何扭怩躲在洋铁皮后面的人感兴趣。我不会对任何人感兴趣,除非我可以看见他的脸。”
“啊,是的,我忘记你对脸的热情了。包亚家的人都长得不错,你找找看,他们应该有一两个神秘故事供你研究。或是柏金.渥白克,当然。冒名顶替总是非常吸引人的,是不是呢?可爱的游戏。重量永远不可能完全在这一头或在那一头,你推下去它又站起来,就像不倒翁。”
门打开了,汀可太太那张平凡的脸从她的帽檐下露了出来,她头顶上的帽子比她的脸更平凡,而且历史悠久。从第一次为葛兰特服务开始,汀可太太就戴着这顶帽子,所以他几乎无法想象她戴其它帽子的模样。据他所知她的确拥有另一顶帽子,她说她戴那顶蓝帽子时就是表示自己情绪忧郁。她偶尔才会“忧郁”那幺一下,而且从未出现在坦比路十九号。她戴这顶帽子通常是因为自觉传统礼俗有这个需要,而它也成为对整个仪式的评价标准。(“你喜欢它吗?汀可。它像什幺?”“不值得我戴的忧郁小帽。”)她戴着它去参加伊利莎白公主的婚礼,和其它各种不同的皇室集会,事实上,她还在肯特公爵夫人剪彩的一支新闻影片上闪过那幺两秒。但对葛兰特来说,这只是一个新闻报导而已:一个评断某场合社会价值的标准,看是不是值得戴上象征“我忧郁”的帽子。
“我听见你有访客,”汀可太太说,“当我准备离开时发觉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于是我对自己说:“一定是哈洛德小姐,”所以我就进来了。”
她带着各种不同的纸袋和一小束秋牡丹。她以女人对女人的方式和玛塔寒暄,在她的那个时代她也算得上是衣着考究,所以她自然对舞台剧女神的服装做了适度的赞许,在那同时她瞄了一眼玛塔插的美丽丁香花。玛塔没看见汀可太太的眼神,但是看到了那一小束秋牡丹,她立刻用排演过似的熟练姿态处理这样的状况。
“我随随便便买了白丁香给你真是浪费,汀可太太带来的野百合可把我比下了。”
“百合?”
“它们是所罗门王的荣耀之一,不会太拘束,也不会过于狂放。”
汀可太太只有在婚礼和洗礼的时候才去教堂,不过她是属于星期天上主日学的那一代。现在她以新的兴味看着握在她毛线手套中的那一束荣耀。
“唔,我从不知道。看起来满有道理的,不是吗?我总把它们想做白星海芋,漫山遍野的白星海芋。贵得不得了,你知道,但有点叫人沮丧。所以它们原来是有颜色的?他们为什幺不能这样说?为什幺一定要叫它们百合呢?”
于是她们开始讨论翻译的问题,以及圣经是多幺容易误导人(“我一直怀疑什幺是不计回报的施舍,”汀可太太说),然后这尴尬的一刻就此结束。
当她们仍然忙着讨论圣经时,矮冬瓜拿了多余的花瓶进来。葛兰特注意到这些花瓶是为白丁香而不是秋牡丹设计的。它们显然是矮冬瓜用来讨好玛塔的,以为未来的良好关系铺路。不过玛塔从不花时间在女人身上,除非她马上就用得着她们。和汀可太太的你来我往不过是她的社交手腕,一种制约反应。所以矮冬瓜已被贬为功能性而非社会性的角色。她把丢弃的水仙从洗脸盆中聚集起来,温柔的放回花瓶中。矮冬瓜温柔的时候真是美极了,这让葛兰特凝视了她好一会儿。
“那幺,”玛塔终于插好了她的丁香花,并且将它们放在他看得到的地方,“我该让汀可太太喂你她那些纸袋里的珍馔了。那不会是,难道是,亲爱的汀可太太,其中一袋是你那美妙的单身汉小圆饼?”
汀可太太高兴得脸红了。
“你要一两个吗?刚出炉的。”
“喔,当然我吃了以后得付出代价──那些营养丰富的小蛋糕会堆积在腰上──不过还是给我几个放袋子里,好带到剧院配下午茶。”
她以一种谄媚式的慎重选了两个(“我喜欢边缘有一点焦的。”),把它们丢到她手袋里,然后说:“再见,亚伦,我一两天之内会开始为你找双袜子来织。据我所知再也没有比编织更能抚平情绪的了。不是吗?护士小姐。”
“喔,是的,的确。我的许多男病人也从事编织。他们发现这样很好打发时间。”
玛塔从门边给了他一个飞吻就走了,矮冬瓜礼貌地送她出去。
“烂货就是烂货,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汀可太太说着就打开了她带来的纸袋。她不是指玛塔。
第二章
第二章
但是当玛塔两天之后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着织针和毛线。她在午餐后飘然而至,精神抖擞的戴着顶哥萨克帽,帽子的角度呈现着休闲的味道,想必让她在穿衣镜前花了好几分钟。
“我不能待久,亲爱的,我待会儿要去剧院。今天下午有日场,老天帮帮忙。全是茶盘和白痴。当台词对我们已毫无意义时,我们却必须走上可怕的舞台。我想这出戏永远不会下档。就像纽约的那些剧一样,十年才一换而不是年年更新。实在太可怕了,根本就无法专心演戏。杰欧弗瑞昨晚在第二幕时僵住了,他的眼睛几乎从他的脑袋中暴出来,一度我还以为他中风了。事后他说他完全不记得从他出场直到发现自己演了一半时这中间发生了些什幺事。”
“你是说,暂时失去记忆?”
“喔,不。是变成机器人一样。念着台词做着动作却一直想着别的事。”
“如果所有的报导都是真的,那幺演员并没有关心什幺大不了的事嘛。”
“喔,平心而论是没有。强尼.葛森会告诉你当他在别人膝上哭断肠时一屋子里有多少卫生纸,但整整半场戏魂都不在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杰欧弗瑞把他儿子赶出屋外,和情妇吵架,还指责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通奸而他却毫不知情。”
“哪样事是他知道的?”
“他说他决定将他公园巷的那栋公寓租给桃莉.黛克,并买下里士满查理二世的房子,拉第莫要卖掉是因为他接受了州长给他的聘书。他想到那房子缺几间浴室,还有楼上有着十八世纪中国式壁纸的小房间多幺棒。他们可以把那美丽的壁纸撕下来去装饰楼下后面那个单调的小房间。全是维多利亚式的镶板,这个单调的小房间。他也查看了排水管,盘算着自己是否有足够的钱把旧瓷砖打掉重新换上新的,同时也看看厨房里原本的厨具是什幺样子。当他想到要把门口的灌木全部铲掉时,他发现自己正在舞台上面对着我,台下有九百八十七个人,台词正念到一半。现在你知道他的眼睛为什幺暴出来了吧。我看你已经试图阅读至少那幺一本我带来的书了──如果书皮皱了就表示看过了的话。”
“是的,山的那一本。真是上天的恩赐,我躺着看了几个小时的图片。再也没有比山更能发人深省的了。”
“星星更好,我发现。”“喔,不。星星只会把人贬成一只阿米巴原虫。星星把人类的最后一抹尊严,最后一丁点信心都给剥夺了。但一座雪山对人类来说却是大小刚好的标竿。我躺着看艾弗勒斯峰,然后感谢上帝我没去爬那些陡坡。比较起来病床上可是温暖的天堂,舒适又安全。矮冬瓜和亚马逊两个人又都是文明的最高成就。”
“啊,这里还有更多的照片。”
玛塔把她带来的一个四开大的牛皮纸袋倒过来,一堆纸抖落在他胸膛上。
“这是什幺?”
“脸,”玛塔高兴的说,“好多好多为你准备的脸。男人,女人,小孩。各式各样,大小都有。他从胸口上拿起一张看,那是一幅十五世纪的人像雕刻。一个女人。
“这是谁?”
“露克西亚.博尔吉亚。她不是只鸭子吗?”
“也许,你是不是暗示她有什幺难解之谜?”
“喔,是的,没有人知道她是被她哥哥利用还是共犯。”
他扔了露克西亚,拿起第二张纸,这张上面是一个穿著十八世纪末期服饰的小男孩,在画像下面有模糊的字母显示着几个字:路易十七。
“这会儿有个美丽的谜要你解,”玛塔说,“法国王储,他是逃走了,还是死于囚室?”
“你哪儿弄来这些东西?”
“我让詹姆斯离开他在维多利亚和亚伯特的温暖小窝,带我到印刷店去。我知道他会了解那种事情,而我确定在这两个他方都不会有什幺事情能引起他的兴趣。”
玛塔就是这样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一个公务员只因为他刚好是个剧作家和人像画的权威,就应该愿意丢下工作不管,流连在印刷店里讨她喜欢。
他发现其中一张照片是伊利莎白女王时代的画像。一个穿著天鹅绒戴着珍珠的男人。他翻到背面想看看这是谁,结果发现这是列斯特伯爵。
“所以那是伊利莎白的罗宾,”他说,“我想我以前从未看过他的画像。”
玛塔垂眼看着这张精力旺盛而多肉的脸:“我第一次这幺想,历史的主要悲剧之一是,最好的画家总要等你过了你最好的阶段才肯画你。罗宾以前一定是个美男子。他们说亨利八世年轻的时候令人目眩神迷,但现在他怎幺样?不过是扑克牌上的玩意见罢了。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坦尼森在留了那可怕的胡须之前长什幺样子。我得走了。我刚才在布莱格吃饭,好多人过来谈话所以无法及时脱身。”
“我希望你的主人对你印象深刻,”葛兰特说,看了一眼她的帽子。
“喔,是的,她很了解帽子。她只要看一眼就会说,“贾姬.托斯,我买了。””
“她!”葛兰特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