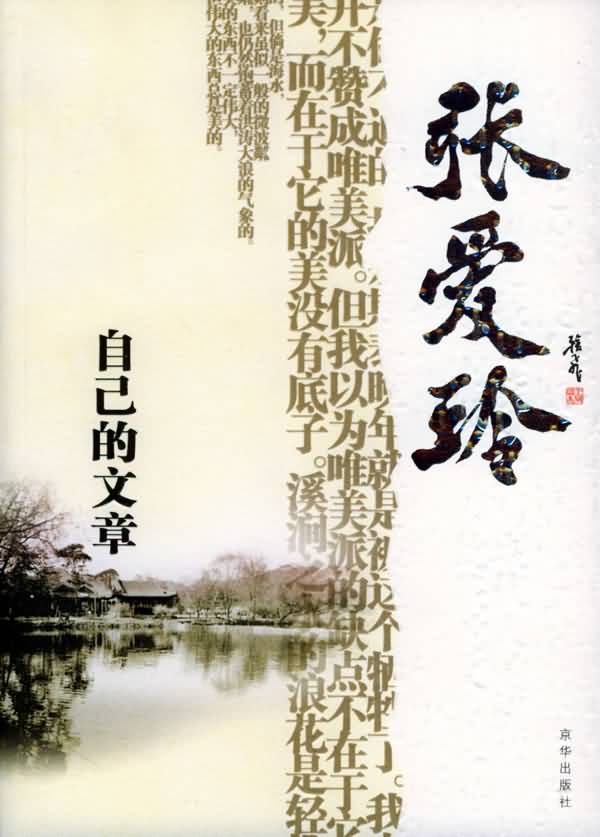路遥文集-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于是在这个方圆几十里唯一的集镇上瞎转起来。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村子。除过公社几个机关和一个小商店、一个邮电所、一个汽车站外,也没有多少人家和建筑。
我突然发现,一个破败的大门口挂着这公社中学的校牌。我马上想起小芳动员我到这个中学教书的事。
现在让我去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学校放学了,不见一个学生。教师们此刻大概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午睡了。我一个人手里提着空孱,开始视察这个学校。
学校看起来就像一个废弃了的大院路。院子里堆满沙子。风棵老柳树大部分的皮都牲口啃光了。到处都是马粪和驴粪蛋——看来老百姓赶集时,可以随意把牲畜拴在学校的院子里。没人管吗?两排砖砌的教室,门窗都没油漆,日经月久,木头都沤成了黑的。院子的墙角里长满杂草——这倒看起来很惹人喜欢。如果在大城市的学校,这些杂草恐怕早被铲除了,但在这里,杂草是一种很好的风景。
整个学校是用一道粘土墙围起来的。从墙里望出去,就是无边的大沙漠。现在,那沙丘已经一直涌到墙头上来了。想那二三月大风季节,恐怕这学校一夜之间就被埋在沙梁之下了……亲爱的小芳,你就让我到这里来创造那两项纪录吗?
“真不堪设想!”我自言自语说着,便离开了这个学校。
我来到商店门口,又等了二十多分钟,才终于买到了一斤酱油。返回农场时的十里路上,我仍然没有碰见一个行人。
唉,沙漠里的道路也是寂寞的……
不论怎样,小芳是为我准备了一顿味鲜美的饺子。她把一碗粉汤饺子调好后,自己先尝一尝味道怎样,才双手递到我手里——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只有自己的爱人才尝自己男人碗里的饭。她这种亲切的感情,使我忍不住鼻根发酸……
晚上,小芳细心地帮助我收拾好东西,让我早点休息,自己就过客房那边去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拿出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我眼睛模糊得连一个字也辨不清。
大大小小的蚊子、飞蛾和一些不知名的虫子,雨点般散落在书上和身体的裸露部分。窗户纸和屋顶的天花板也沾满了蚊虫,像下雨似的沙沙作响。
我不时发出一连串的叹息……
有人敲门。我穿上外衣去开门。是小芳。“蚊子太多,让我给你想想办法。”她说。
她让我到屋外去,然后拉灭了屋里的灯。她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门外面,又在煤油灯旁放了一脸盆水。
蚊子和飞蛾都纷纷从屋里的黑暗中飞出来,向煤油灯罩上扑去,然后又落在了脸盆的水里。
我们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都没有一点睡意。
我们努力搜寻着拉一些家常话。更多的时间都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深夜。偶尔有农场的工人穿着短裤出来上厕所,惊异而迷惑地看一会儿我们。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亮……
吃完早点,小芳送我到公社的汽车站。
……当汽车开动以后,我看见她撵着车跑了几步,然后便绝望地站住,把头扭到了一边。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含着泪水向她拼命招手。别了,我亲爱的人!我爱你,但我还是要离开你。我将深切地盼望着你有一天会来到我的身边。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也盼望我来到你的身边生活,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多么困难……别了,我亲爱的人!
别了!别了!别了……
。。
你怎么也想不到20…(郑小芳)
生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汽车站回到农场的……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还是走了。
他也许再不会来这里了。他爱我,但并不爱我所坚持的生活道路。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再在一块生活呢?当他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似乎心花怒放地以为,他终于又和我并肩走在了一条路上。我甚至想对他大声朗育诵我们曾共同喜欢过的伟大的惠特曼的诗句:请和我同行吧,和我同行,你将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但是我错了。他只是来看看我。他在我和大城市之间依然选择了后者。可是,薛峰,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呢?你把艰苦和伤心留给我,然后你走了……一种痛苦的情绪不时地涌上我的心间。是的,像任何别的女人一样,我希望按自己的思想去进行崇高的劳动和创造,但也希望在爱情上能得到幸福和满足。可是,生活往往不能如人心愿——你得到一些东西,也许就会失去另外一些东西。
可是想来想去,不管多么痛苦,该失去的也只能失去。人总不能为了得到某种感情上的满足就背叛生活的原则。
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是一无所有。我有我热爱的事业,这足以使我的精神感到充实。无论如何,我不能可再离开这里了。这里有我的花棒,我的桑树苗,我的蚕……
几天以后,我突然在一天之内同时接到薛峰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我最后一次央求你,到我身边来吧!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了!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里。”第二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刚把信塞进邮筒,我就又后悔了!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我的呼唤。那么,我央求你,给我一点时间吧,让我好好想想。我说不定会很快回到你身边来的。你应该相信我,我要是再回到你那里,就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了。我现在的脑子像火烧一般疼!亲人,你答应我吧!等着我!,等着我吧!!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我把两封信放在桌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会。
此刻,我似乎看见远方那个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怎样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一样,转圈圈走着,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拼命吸烟……我理解他的痛苦,我也知道他那矛盾的灵魂,在进行怎样一种严酷的搏斗!也许他能战胜自己,重新勇敢而高尚地直面人生。也许他仍然不能悔悟,继续在原的生活轨迹上走着……但不论怎样,我亲爱的人,我还是要对你说:我答应你,我等着你,我盼望你回到我的身边来。要知道,我虽然离你,但我一直爱着你,想念你,并且在梦中常常和你相会……回来吧!我亲爱的人!我等着你……
。。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我听对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因此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的。
一般说来,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一堆烂柴烂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1)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