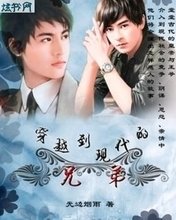革命的年代-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它的商业。(英…法冲突和罗马…迦太基冲突的类比,大量存在于法国人的思想中,他们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时,法国资产阶级会指望靠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抵消掉英国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为自己建立一个广大而受控制的市场,把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与其他冲突不同,这两种考虑都会使英法冲突变得持久而又难以解决。任何一方实际上除获得全面胜利外,都不准备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今天虽然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罕有的事)。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和平(1802-1803年),便因双方都不愿意维持下去而告终结。这种冲突的难以解决,因双方在纯军事领域中的对峙局势,而变得更明显:从18世纪90年代末期,情况就很清楚,英国人无法在大陆上有效赢得战争,而法国人也不能成功突破海峡。
另一些反法强国,则忙于不那么残酷的争斗。它们都希望推翻法国大革命,虽然都不想以它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为代价,但到了1792-1795年后,这样的愿望显然已难以实现。奥地利是最坚定的反法大国,因为法国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和对德国的主宰地位。因而奥地利加强了与波旁王朝的联系,并参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国参加反法战争则时断时续,它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参战。普鲁士的态度则有点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奥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兰和德国,却需要法国的主动支持。于是,它只是偶尔参战,并且是以半独立的方式:如在 1792-1795年、1806-1807年(当时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时不时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政策摇摆。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政治归政治,它们还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非要它们坚定不移地敌视法国,特别是一个决心定期重划欧洲领土的常胜法国。
欧洲国家这种长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为法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盟友。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处于紧张关系的每一个永久性国家体系中,与甲方的不和,就意味着对反甲那方的同情。这些潜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较低的德国王公们,他们有的是长期以来便将自身的利益建筑在(与法国结盟)削弱皇帝(即奥地利)对各诸侯国的权力上,有的则是饱受普鲁士势力增长之苦。德国西南部诸邦,如构成拿破仑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老对手以及受害者萨克森,是这类国家的代表。实际上萨克森是拿破仑最后一个最忠实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经济利益来说明,因为萨克森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心,可以从拿破仑的“大陆系统” (continental system)中获得好处。
即使把反法一方的分裂和法国人可资利用的盟友潜力考虑在内,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反法联盟还是要比法国强大得多,至少开始阶段是如此。然而,战争的军事记载却是法国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胜利。在外国军队和国内反革命的最初联合被打退之后(1793-1794年),在战争结束前只有一个短暂时期,法国军队的防御是处于危急状态,即1799年,第二次反法联盟动员了苏沃洛夫(suvorov)统率的俄国军队,这支强大而可怕的队伍首次出现在西欧战场上。就一切实际成果而言,1794-1812年间的战役和地面战斗一览表,实际上便是法国不断取得胜利的记载。而其原因就在于法国的革命本身。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在国外的政治宣传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它防止了反动国家的居民起而抵抗为他们带来自由的法国人,但事实上,18世纪正统国家的战略战术,并不指望也不欢迎平民参战。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曾斩钉截铁地告诉那些支持他对抗俄国的柏林人,要他们远离战争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人的作战方式,并使其比旧制度的军队优越许多。从技术上来说,旧制度的军队有较好的训练、较严密的军纪,在这些素质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地方,如海战,法国军队便处于明显弱势。他们是出色的私掠船和打了就跑的武装快船船员,但这不足以弥补训练有素的海员,尤其是称职海军军官的缺乏。这部分人被革命杀死了一大批,因为他们大多是保王派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乡绅,而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又无法很快拼凑起来。在英、法之间的六次大海战和八次小海战中,法国的人员损失大概是英国的10倍。但在临时编队、机动性、灵活性,特别是十足的进攻勇气、士气和计算等方面,法国人是没有对手的。这些优势靠的并不是任何人的军事天才,因为在拿破仑接管军权前,法国人的军事纪录已相当令人注目,虽然法国将帅的一般素质并不突出。但这些长处多少得益于国内外核心官兵的活力恢复,而这正是任何革命的主要成效之一。1806年,在普鲁士强大陆军的142位将军中,有79人超过60岁,而所有的团指挥官中,这种年龄的军官也占了四分之一。但同年,拿破仑(24岁时任将军)、缪拉(murat,26岁时指挥一个旅)、赖伊(27岁时也指挥一个旅)和达福(davout),却只有26…37岁不等。
??
第一篇 发展 第四章 战争 2
;
2
由于胜利一面倒向法国,因而在此无需详细讨论陆上战争的军事行动。1793-1794年,法国人保住了大革命。1794-1795年,他们占领了低地国家、莱茵地区、部分西班牙、瑞士、萨伏伊(和利古里亚)。1796年,拿破仑著名的意大利战役使法国人赢得整个意大利,并破坏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对马尔他、埃及和叙利亚的远征(1797-1799年),被英国的海军力量割断了他与其基地的联系,而他不在法国的这段时期,第二次反法同盟把法国人赶出了意大利,并使他们退回德国。盟军在瑞士(苏黎士战役,1799年)的大败,使法国得以免遭入侵,而在拿破仑回国和夺取政权不久,法国人又再度处于强势。至 1801年,他们把和平强加于欧洲大陆盟国,到1802年,甚至强迫英国人接受和平。此后,在1794-1798年被征服或被控制的地区中,法国的主宰地位一直是不成问题的。1805-1807年,一轮重新发动的抗法企图,更把法国的影响推进到俄国边境。1805年,奥地利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会战中被打败,并被迫议和。独自而且较晚参战的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edt)会战中遭击垮和肢解。俄国虽然在奥斯特里茨战败,在艾劳(eylau,1807年)受挫,并在弗里德兰德(friedland, 1807年)再度战败,但仍保持军事强国的完整性。《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1807年)以无可非议的礼遇对待俄国,尽管该和约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除斯堪的纳维亚和土属巴尔干外。1809年,奥地利企图摆脱法国控制,但在阿斯本…埃斯林(aspern-essling)和华格南(wagram)会战中被打败。然而,1808年西班牙人起义反对拿破仑兄长约瑟夫成为他们的国王,从而为英国人开辟了一个新战场,经常性的军事行动在伊比利亚半岛持续进行,但因英国人周期性的失败和撤退(如1809-1810 年),而未取得重大效果。
可是在海上,法国人此时已被彻底打败。特拉法尔加(trafalgar,1805年)战役以后,别说越过海峡入侵英国,就连在海上保持接触的机会都消失了。除施加经济压力外,打败英国的办法似已不存在,因而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系统”有效地实施经济封锁。实行封锁的种种困难,相当大程度地破坏了《提尔西特和约》的稳定性,并导致与俄国的决裂,这成为拿破仑命运的转折点。俄国遭到入侵,莫斯科被占领。如果沙皇像拿破仑的多数敌人那样,会在类似的情况下进行议和,那么这次冒险就大功告成了。但沙皇没有这样做,因而拿破仑面临的问题是进行一场胜利无望、休止无期的战争,或是撤退。两者都同样是灾难性的。如前所述,法国军队的致胜办法是在足够富庶和人口众多、可靠该国生存的地区进行速决战。但是,在最先产生这种战法的伦巴底或莱茵地区行之有效,在中欧仍然行得通,到了波兰和俄国的广大不毛之地,却彻底失败了。与其说是俄国的严冬使拿破仑招致失败,毋宁说是他无法使他庞大的军队保持足够给养所致。莫斯科撤退摧毁了这支军队。曾几何时,首次穿越俄国国境、人数曾高达61万的大军队,当再度越过国境时,却只剩下几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次反法同盟不仅包括法国的宿敌和受害国,更联合了那些急于站到此刻明显将取得胜利那方的国家,只有萨克森国王过迟地离开其原先追随的人。一支新的、大多未经训练的法国军队,在莱比锡(leipzig,1813年)惨遭大败,尽管拿破仑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调动,盟国军队还是无情地向法国本土推进,而英国人则从伊比利亚半岛攻入法国。巴黎被占领,而皇帝则于1814年4月6日退位。他企图于1815年恢复其政权,但因滑铁卢会战(waterloo,1815年)失败而告终。
。。
第一篇 发展 第四章 战争 3
小说
3
在战争进行的这几十年里,欧洲的政治疆界被重新划过几次。在此只需考虑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使其持续时间超过拿破仑失败的变动时间。
这些变动中最重要的是欧洲政治地图的普遍合理化,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在政治地理方面,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结束。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典型的现代国家是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领土是连成一体并有明确边界的完整区域。(法国大革命以来,也设定国家应代表一个单一“民族”或语言集团,但在这个阶段,有主权的领土国家尚不包含这层意思。)尽管典型的欧洲封建国家有时看起来也像是这样,如中世纪的英国,但当时并未设定这些必要条件。它们多半是模仿“庄园”而来。好比“贝德福公爵庄园”既不意味它必须在单一的区段,也不意味它们全体必须直接受其所有者管理,或按同样的租佃关系持有土地,或在同样的条件下租佃,也不一定排除转租,也就是说西欧的封建国家并不排除今天显得完全不能容忍的复杂情况。然而到了1789年,大多数国家已感受到这些复杂情况是一种累赘。一些外国的领地深处在另一个国家的腹地之中,如在法国的罗马教皇城阿维尼翁(avignon)。一国之内的领土发现自己因历史上的某些原因也要依附于另一个领主,而后者现在恰好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因此,用现代词汇来说,它们处于双重主权之下。(这类国家在欧洲的惟一幸存者是安道尔'andorra'共和国,它处于西班牙乌盖尔〔urgel]主教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双重主权之下。)以关税壁垒形式存在的“边界”,存在于同一国家的各个省分之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他自己几个世纪积攒下来的公国,但它们从未充分实行同一制度或实现统一。(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直至 1804年前,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称号可以涵括他对自己全部领土的统治[他只是奥地利公爵、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蒂罗尔伯爵等等〕。)此外,他还可对形形色色的领土行使皇帝权力,从独立存在的大国(如普鲁士),到大大小小的公国,到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以及“自由帝国骑士”,后者的领地常常不超过几英亩,只是恰好没有位居其上的领主。每个这类公侯国本身,如果足够大的话,通常也呈现出同样缺乏的统一领土和划一管理,它们依据的是家族遗产的逐块占有、分割和再统一。结合了经济、行政、意识形态和实力考虑的现代政府概念,在当时尚未被大量采用,于是再小的领土人口,都可组成一个政府单位,只要其实力允许。因此,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小国和迷你国仍大量存在。
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大量清除了这类残余,这部分是由于对领土统一和简单划一的革命热情,部分是因为这些小国和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期暴露于较大邻国的贪婪面前。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大多数城市国家和城市帝国之类的早期国家,都告消失。神圣罗马帝国亡于1806年,古老的热内亚和威尼斯共和国亡于 1799年,而到战争末期,德国自由市已减少到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