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夜幕的掩护下,苏维埃巨型战舰于子夜时分通过博斯普鲁斯。
我一时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全城都在睡梦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苏维埃巨舰不知将开往何处,从事何种活动。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提醒伊斯坦布尔,提醒全世界。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勇敢的小英雄做这样的事——把城民从睡梦中唤醒,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水患、火灾和入侵的军队袭击。
我忧心如焚的同时,想出一个十万火急的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日后成了习惯:我集中因背诵而更为敏锐的脑筋,专心于苏维埃战舰,用心记住,数着它。此话怎讲?我的做法就像传说中的美国间谍——传闻他们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把通过的每艘共产党船只拍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事实根据的伊斯坦布尔传说,至少在冷战期间)——将这艘问题船的显著特征罗列出来。我在脑海里将新资料和有关其他船舶、博斯普鲁斯海流甚至地球转速的现存资料详细比较。我数着它,这使巨船变成一件普通事物。不仅苏维埃战舰,数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图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这么说,学校教我们的是真的:博斯普鲁斯是关键,是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心,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及其军队,特别是苏联人想占据我们美丽的博斯普鲁斯的原因。
我这一生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尽管只是从远处观看,而且是从公寓、清真寺的圆顶和山峦之间观看。能看见博斯普鲁斯,即使是远远观望,这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有其神圣意涵,或可说明临海的窗户为何像清真寺的壁龛、基督教堂的祭坛以及犹太教堂的圣坛,我们面朝博斯普鲁斯的客厅为何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我们对博斯普鲁斯海景的热爱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如果搭船从马尔马拉海进来,你会看见伊斯坦布尔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为了仔细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过的海面。
数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或许是个怪癖,但从我同他人开始讨论这件事以来,我发现这在伊斯坦布尔的老老少少当中很常见:在通常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人经常到窗前和阳台作记录,这么做让我们对灾难、死亡和浩劫有些许领略,它们说不定正沿着海峡过来,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搬到贝希克塔斯,在塞伦塞贝区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有栋房子里住着我们的远亲,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过的船只记录下来,让人以为这是他的工作。我有个中学同学相信,每一艘形迹可疑的船(老旧、生锈、失修或来历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苏联武器走私给某国的叛军,就是把石油运往某个国家,以扰乱全球市场。
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数船癖好,我与许多人共有的这项癖好,基本上是由于恐惧使然,这种恐惧也吞噬着城里的许多人。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民族主义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洋气的东西(尽管我们亦对之垂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
城里居民记得最清楚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灾难的类型,自然与博斯普鲁斯的船舶事故有关。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连在一起,使整个城市像个大村落。由于这些灾难终止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且最后总是饶过“我们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尽管心怀内疚)喜欢这些灾难。
当时我才八岁,那天晚上我推断——根据划破星夜的声响与火焰——两艘载运石油的油轮在博斯普鲁斯中间相撞,发生大爆炸后起火燃烧。但我的兴奋更甚于惊恐。很晚我们才从电话得知燃烧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库发生爆炸,火势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险。正像那个时代每一场壮观的火灾一样,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顺序:首先我们看见火焰和黑烟,接着谣言散布开来,多半是不实之谣,而后,尽管母亲姑妈们哀哀恳求,我们却有一股确切的欲望,想亲自去看大火。
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们,把我们塞进车里,取道博斯普鲁斯后方的山丘,载我们去塔拉布亚。就在大饭店(尚在建造中)前方,道路被封锁,这跟大火本身一样,使我既难过又兴奋。后来听我一个狂妄自大的同学说他父亲亮出证件高喊“记者!”之后,使他们得以通过警戒线,令我欣羡不已。就这样,1960年某个秋夜天将破晓之时,我最后还是跟着一群好奇甚至欢乐的人群,他们身穿睡衣和匆匆套上的裤子和拖鞋,把宝宝抱在腿上,手上拎着袋子,一同观看博斯普鲁斯起火燃烧。后来的几年中我常看见,在壮观的大火摧残“雅骊”、船舶甚或海面之际,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摊贩,在人群中兜售纸包芝麻蜜饼、“芝米”、瓶装水、瓜子、肉丸和冰镇果汁。
据报纸报道,载运十吨燃油的“彼得佐拉尼赫”油轮从苏联港口陶普斯开往南斯拉夫,因走错航道而与航道正确、开往苏联添加燃料的希腊油轮“世界和平号”相撞,相撞后一两分钟,南斯拉夫油轮漏出的燃料爆炸,威力凶猛,伊斯坦布尔全城都听得见。不知是因为船长和船员立即弃船还是在爆炸中身亡,两艘船上都没有人,于是失去了控制,开始在猛烈而神秘的海流与漩涡中打转。它们左右摇晃,变成火球,对坎勒札、欸米甘与叶尼廓伊的“雅骊”、楚布库鲁的油气储库以及贝廓兹沿岸的木头房屋造成威胁。曾被梅林描述为人间天堂、希萨尔称之为“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海岸陷入一片火海,黑烟呛鼻。
只要船距离岸边太近,大家便逃出他们的“雅骊”和木头房屋,一手夹着棉被,另一手夹着孩子,尽快地逃离海岸。南斯拉夫油轮从亚洲漂往欧洲岸时,撞上停泊在伊斯亭耶的土耳其客轮“塔色斯”,过不久,这艘船也燃烧起来。燃烧的船漂过贝廓兹,成群的人拎着棉被、穿着匆匆套在睡衣外面的雨衣,朝山丘上奔去。大海被灿烂的黄色火焰点亮。船成了堆高的红色熔铁,熔化的桅杆、烟筒、船桥歪向一边。天空染上一片红光,好似由内散发而出。不时会有一阵爆炸,燃烧着的大铁片飘入海中。从岸边和山丘传来呼喊声、尖叫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多么令人心碎,却又发人深省,审视这片柏树与松林、庭院桑树成荫、忍冬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
后来想想,我要是数船,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由于对城里遭受的灾难感到负有责任,我并不想逃离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尽我所能靠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后来,像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我几乎是期望灾难,这种期望在下次灾难发生时使我更觉得罪过。
就连坦皮纳(其著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国内快速西化的奥斯曼文化废墟中之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到头来,人民本身由于无知与绝望,终于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也承认,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在《五城记》的伊斯坦布尔章节中,他和戈蒂耶一样,拿自己与暴君尼禄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几页之前,坦皮纳还苦闷地写道:“一栋接着一栋,眼前的杰作有如浇了水的岩盐快速熔化,直到仅剩下一堆堆灰烬与泥土。”
坦皮纳在1950年代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居住在“鸡不飞胡同”——我数苏维埃战舰时就住在同一条街。他从这里看着大火烧毁萨比哈公主的滨海宫殿,以及曾经是奥斯曼议会、后成为他曾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木造建筑。大火熊熊燃烧一个小时,随着每一次爆炸抛射出阵雨般的碎火花;“从喷发的火焰和缕缕烟柱,可知道审判日已然来临”。或许觉得需要调和奇观所提供的快乐,以及眼见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美丽建筑与其宝贵收藏(包括建筑师艾尔登 'sedad hakk eldem' 的奥斯曼古迹档案与详细规划,据说是当时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绝望,他继续说明奥斯曼帕夏们也从观赏世纪大火中享受过类似的乐趣。坦皮纳带着怪异的内疚感如此告诉我们,听见某人高喊“失火!”,他们便跳上自己的马车,赶往现场;而后他继续列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万一大火将持续一段时间——用来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和锅子。
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习俗。
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
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
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
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
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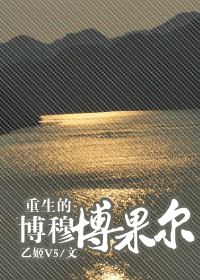
![[基尔·布雷切夫_孙维梓] 必](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