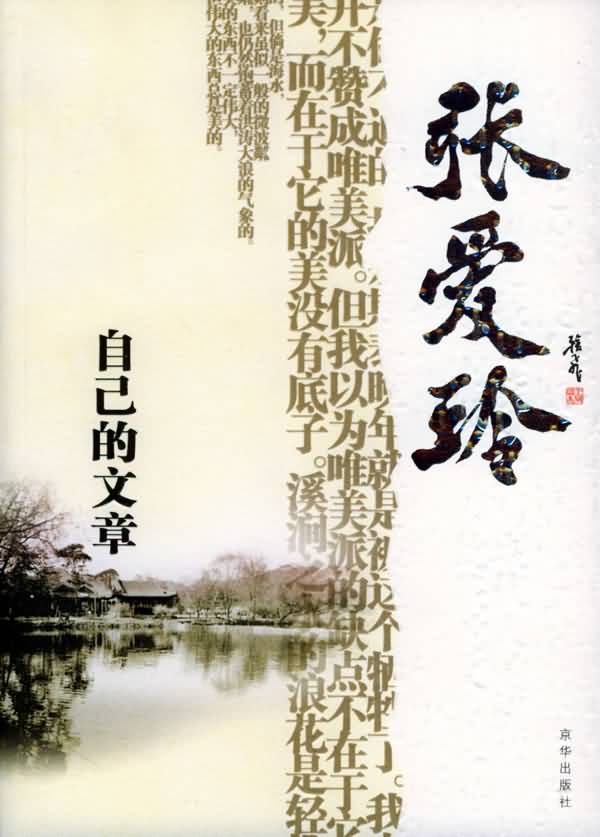博尔赫斯文集-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缘以及我们的想像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他似乎没有听我说。突然问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称也是博尔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我毫无把握地回答:
〃我也许会说事情太奇怪了,我试图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个问题:
〃您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明白,在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眼里,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死人相差无几。我回说:
〃看来容易忘事,不过该记住的还能记住。我在学盎格罗一撒克逊文,成绩不是全班级最后一名。〃
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不像是梦境。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我马上可以向你证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梦,〃我对他说。〃仔细听这句诗,你从未见过,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条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诗: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觉察到他惊讶得几乎在颤抖。我低声重复了一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亮的字。
〃确实如此,〃他嗫嚅说。〃我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诗句。〃
诗的作者雨果把我们联结起来。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此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突然又记起柯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
我想出一个类似的办法。
〃喂,你身边有没有钱?〃我问他。
〃有,〃他回答说。〃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请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鳄鱼咖啡馆聚聚。〃
〃你对西蒙说,让他在卡卢其行医,救死扶伤……现在把你的钱币给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银币和几个小钱币。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给了我一枚银币。
我递给他一张美国纸币,那些纸币大小一律,面值却有很大差别。他仔细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钞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这简直是个奇迹,〃他终于说。〃奇迹使人恐惧。亲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人也会吓呆的。〃
我们一点没有变,我想道。总是引用书上的典故。
他撕碎钞票,收起了那枚银币。
我决定把银币扔到河里。银币扔进银白色的河里,画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不见,本可以给我的故事增添一个鲜明的形象,但是命运不希望如此。
我回说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出现两次就不吓人了。我提出第二天再见面,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碰头。
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有看表,却说他已经耽误了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真话,每人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找我。
〃找你?〃他问道。
〃不错。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也会几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见黄颜色和明暗。你不必担心。逐渐失明并不是悲惨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第二天,我没有去。另一个人也不会去。
我对这次邂逅相遇思考了许多,谁也没有告诉。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
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得不真切。现在我明白他梦见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现的年份。
乌尔里卡
。
他把出鞘的格拉姆剑放在床上两人中问。
《沃尔松萨伽》,27
我的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于我个人记忆所及的事实,两者相去无几。事情是前不久发生的,但是我知道舞文弄墨的人喜欢添枝加叶、烘托渲染。我想谈的是我在约克市和乌尔里卡(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也许再也不会知道了)邂逅相遇的经过。时间只包括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
我原可以无伤大雅地说,我是在约克市的五修女院初次见到她的(那里的彩色玻璃拼镶的长窗气象万千,连克伦威尔时代反对圣像崇拜的人都妥为保护),但事实是我们是在城外的北方旅店的小厅里相识的。当时人不多,她背朝着我。有人端一杯酒给她,她谢绝了。
〃我拥护女权运动,〃她说。〃我不想模仿男人。男人的烟酒叫我讨厌。〃
她想用这句话表现自己的机敏,我猜决不是第一次这么说。后来我明白她并不是那样的人,不过我们并不是永远言如其人的。
她说她去参观博物馆时已过了开馆时间,但馆里的人听说她是挪威人,还是放她进去了。
在座有一个人说:
〃约克市并不是第一次有挪威人。〃
〃一点不错,〃她说。〃英格兰本来是我们的,后来丧失了,如果说人们能有什么而又能丧失的话。〃
那时候,我才注意打量她。威廉·布莱克有一句诗谈到婉顺如银、火炽如金的少女,但是乌尔里卡身上却有婉顺的金。她身材高挑轻盈,冰肌玉骨,眼睛浅灰色。除了容貌之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那种恬静而神秘的气质。她动辄嫣然一笑,但笑容却使她更显得冷漠。她一身着黑,这在北部地区比较罕见,因为那里的人总喜欢用鲜艳的颜色给灰暗的环境增添一些欢快。她说的英语清晰准确,稍稍加重了卷舌音。我不善于观察;这些细节是逐渐发现的。
有人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告诉她,我是波哥大安第斯大学的教授。还说我是哥伦比亚人。
她沉思地问我:
〃作为哥伦比亚人是什么含义?〃
〃我不知道,〃我说。〃那是证明文件的问题。〃
〃正如我是挪威人一样,〃她同意说。
那晚还说什么,我记不清了。第二天,我很早就下楼去餐厅。夜里下过雪,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荒山野岭全给盖没。餐厅里没有别人。乌尔里卡招呼我和她同桌坐。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
我记起叔本华一句开玩笑的话,搭腔说:
〃我也是这样。我们不妨一起出去走走。〃
我们踩着新雪,离开了旅店。外面阒无一人。我提出到河下游的雷神门去,有几英里路。我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乌尔里卡;除了她,我不希望同任何人在一起。
我突然听到远处有狼嗥叫。我生平没有听过狼嚎,但是我知道那是狼。乌尔里卡却若无其事。
过一会儿,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我昨天在约克礼拜堂看到的几把破剑,比奥斯陆博物馆里的大船更使我激动。〃
我们的路线是错开的。乌尔里卡当天下午去伦敦;我去爱丁堡。
〃德·昆西在伦敦的茫茫人海寻找他的安娜,〃乌尔里卡对我说。〃我将在牛津街重循他的脚步。〃
〃德·昆西停止了寻找,〃我回说。〃我却无休无止,寻找到如今。〃
〃也许你已经找到她了,〃她低声说。
我福至心灵,知道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对我来说并不受到禁止,我便吻了她的嘴和眼睛。她温柔而坚定地推开我,然后痛快地说:
〃到了雷神门的客栈我就随你摆布。现在我请求你别碰我。还是这样好。〃
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身男人,应许的情爱是已经不存奢望的礼物。这一奇迹当然有权利提出条件。我想起自己在波帕扬的青年时期和得克萨斯一个姑娘,她像乌尔里卡一样白皙苗条,不过拒绝了我的爱情。
我没有自讨没趣问她是不是爱我。我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次艳遇对我也许是最后一次,对那个光彩照人的、易卜生的坚定信徒却是许多次中间的一次罢了。
我们手挽手继续走去。
〃这一切像是梦,〃我说。〃而我从不梦想。〃
〃就像神话里的那个国王,〃乌尔里卡说。〃他在巫师使他睡在猪圈里之前也不做梦。〃
过一会儿,她又说:
〃仔细听。一只鸟快叫了。〃
不久我们果然听到了鸟叫。
〃这一带的人,〃我说,〃认为快死的人能未卜先知。〃
〃那我就是快死的人,〃她回说。
我吃惊地瞅着她。
〃我们穿树林抄近路吧,〃我催促她。〃可以快一点到雷神门。〃
〃树林里太危险,〃她说。
我们还是在荒原上行走。
〃我希望这一时刻能永远持续下去,〃我喃喃地说。
〃永远这个词是不准男人们说的,〃乌尔里卡十分肯定地说。为了冲淡强调的语气,她请我把名字再说一遍,因为第一次没有听清楚。
〃哈维尔·奥塔罗拉,〃我告诉她。她试着说一遍,可是不成。我念乌尔里卡这个名字也念不好。
〃我还是管你叫西古尔德吧,〃她微微一笑说。
〃行,我就是西古尔德,〃我答道。〃那你是布伦希尔特。〃
她放慢了脚步。
〃你知道那个萨伽的故事吗?〃我问道。
〃当然啦,〃她说。〃一个悲惨的故事,后来被德国人用他们的尼贝龙根人的传说搞糟了。〃
我不想争辩,回说:
〃布伦希尔特,你走路的样子像是在床上放一把剑挡开西古尔德。〃
我们突然发现客栈已在面前。它同另一家旅店一样也叫北方旅店,并不使我感到意外。
乌尔里卡在楼梯高处朝我嚷道:
〃你不是听到了狼嚎吗?英国早已没有狼了。快点上来。〃
我到了楼上,发现墙上按威廉·莫理斯风格糊了深红色的壁纸,有水果和禽鸟交织的图案。乌尔里卡先进了房间。房间幽暗低矮,屋顶是人字形的,向两边倾斜。期待中的床铺反映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抛光的桃花心本使我想起《圣经》里的镜子。乌尔里卡已经脱掉衣服。她呼唤我的真名字,哈维尔。我觉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家具和镜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
代表大会
。
他们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墙上有这么几行文字:〃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属于全世界。你们进来时经过这里,出去时还要经过这里。〃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名叫亚历山大·费里。我有幸结识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说,我的姓名既带光荣的金属,又有伟大的马其顿人的遗风。但是这个掷地有声的威武的名字同写这篇东西的灰溜溜的人并不相似。我现在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街的一家旅馆楼上,这里虽说是南城,但已没有南城的特色了。我已经七十多岁;还在教英语,学生为数不多。由于优柔寡断、漫不经心,或者别的原因,我没有结婚,如今还是单身。我并不为孤独感到苦恼;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发现自己垂垂老矣;确凿无疑的症状是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不觉惊异,也许是因为我注意到新鲜事物也不特别新鲜,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而已。年轻时,我感怀的是傍晚、郊区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我不再以哈姆雷特自拟。我加入了保守党和一个象棋俱乐部,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国立图书馆某个幽暗的书架上找到我写的《约翰·威尔金斯简析》,这部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订其中的许多疏漏错误。据说图书馆的新馆长是个文人,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仿佛现代文字还不够简单似的,他还致力于颂扬一个想像的江湖气十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来到这个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个江湖哥们或者据说是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