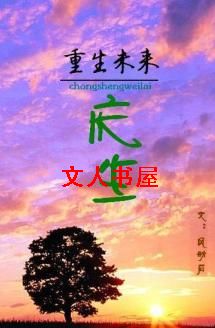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o)、阿尼姆(arnim)、艾亨多夫(eichendorff)、波托茨基(potocki)、果戈理(gogol)、奈瓦尔(nerval)、戈蒂埃(gautier)、霍桑(hawthorne)、爱伦·坡(poe)、狄更斯(dickens)、屠格涅夫(turgenev)、列斯科夫(leskov),一直到斯蒂芬逊 (stevenson)、吉普林(kipling)和威尔斯(wells)。与此同时,我还遵循了有时候是在同一作家作品中跳动的另外一个脉博;这一脉搏使幻想中的情节从日常的——一种内在的、心智的、不可见的幻景中跳跃出来,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登峰造极。
在二十一世纪预制形象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描述幻景的文学依然是可能存在的吗?现在看来似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我们可以回收利用已经用过的形象,在新语境中改变其意义。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倾向,讽喻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库存形象,或者把对于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奇异因素的趣味注入强调其疏离化的叙事技巧之中。二、我们可以把石版擦拭干净,白手起家。撒姆尔·贝克特通过把视觉因素和语言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办法取得了最为超凡绝伦的成果,好像是身处世界终结之后的另一个世界。
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出现的第一篇作品大概是巴尔扎克的《无名的杰作》(le chef doeuvre inconnu)。我们所说的先知洞察力源于巴尔扎克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虽然他处在文学史的一个交点上,有一种时而是幻景的、时而是现实的、时而两者共存的刺激或经验,但他显然经常受到各种自然力量的牵引,同时十分明了他所作的一切。
他是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三七年写作《无名的杰作》的,最初的副标题是“幻想故事”(conte fantastique),而最后的定稿则化为“哲学研究”(etude philosophique)。在这几年之内发生的事, 正如巴尔扎克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所说的,是文学扼杀了幻想。在这篇作品第一版(于一八三一年发表在杂志上)中,年迈画家弗伦费尔(frenhofer)的完美画作中只有一只女人的脚从混乱的色彩中、从昏迷的雾霭中浮现出来,得到画家的两个同事:普尔毕·普桑(pourbus poussin)和尼古拉·普桑(nicholas poussin)的理解和称赞。“这么一小块画布包含着多少让人愉快的因素啊!”虽然那模特儿不大理解,却也得到了某种愉快的印象。
在一八三一年单行本的第二版中又增添的几段对话,显示出弗伦霍费尔的同事缺乏理解,他依然是一个为理想而生活的、有灵感的神秘人物,然而注定要忍受孤寂。最后的定稿(一八三七年)增加了几页绘画技巧评论和一个结尾:弗伦霍费尔是一个狂人,连同他被信以为真的杰作一起被关起来,后来他把画烧毁,然后自杀了。
《无名的杰作》常常被评论为关于现代艺术的寓言。我在阅读这些研究著作中最新的一篇(胡贝尔特·达米什(hubert damisch:《闪闪的黄窗》【fenêtre jaune cadmium】,1984)的时候意识到,这篇短篇小说也可以当作关于文学的寓言来研读,其所指是语言表达与感性经验、与视觉想象力的飘忽不定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巴尔扎克这篇小说第一版本中包含了幻想不可思议这一定义:“对于全部这些奇妙的事物来说,现代语言只有一个词语来形容:真是不可思议(it was indefinable)……一个恰到好处的词语。它总结了描写幻景的文学;它说出了我们精神中有限的感受力无法把握的一切;只要把这个词语摆在读者眼前,他就被弹射到想象空间中去了。”
在以后的年代中,巴尔扎克放弃了对他而言原来曾是关于万物神秘知识的艺术的幻景文学,而转向对于世界本来面目的详细描写;但他依然确信他是在表现生活的秘密。正像巴尔扎克本人长时间不能确定是把弗伦霍费尔造就成一个预言家或者一个狂人那样,他这篇小说也一直包含有一种歧义,而其最深刻的真实也就寓于其中。艺术家的想象力是一个包容种种潜能的世界,这是任何艺术创作也不可能成功地阐发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适应着其他形式的秩序和混乱。在纸页上层层积累起来的词语,正像画布上的层层颜料一样,是另外一个世界,虽然也是不限定的,但是比较容易控制,规划起来较少费力。这三个世界的联系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不可思议(indecidable);或者,我想称之为无法判定(undecidable)。这是包含着其他无限的整体的无限的整体的相谬之处。
一个作家——我所指的是像巴尔扎克那样具有无限雄心的作家——所进行的创作活动,涉及他的想象力的无限性或者可能企望的偶然性的无限性,或者二者兼具,其手段就是写作中语言表述的无限性。有人可能提出反驳,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从生到死,只能获取数量有限的信息。一个个人储存的形象和个人的经验如何能够超越这个界限呢?不过,我深信,这类逃避繁复性漩涡的尝试是无济于事的。乔达诺·布鲁诺向我们解释说,作家想象力从中汲取到形体与人物的幻想精神(spiritus phantasticus)是一个无底的深井;至于外在的现实,那么,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édie humaine)时的出发点,就是设定文字的世界和不仅是今天的,而且还有昨天的,或者明天的生活世界,都是类似的。
作为一名描写幻象的作家,巴尔扎克力求用在无限数量的想象中的一个单一的象征来把握世界的灵魂;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被迫让文字载负内容过量,结果文字所指已经不是它本身之外的世界,正如弗伦霍费尔的色彩和线条那样。巴尔扎克在到达这个境地的时候,便止步而改变成整个的计划:由密集描写转向广泛的描写。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要通过写作来拥抱充溢着人群、生活和故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和时间。
然而,艾舍尔图画中的情况会不会在这里再现呢?——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评论那些画是戈德尔怪圈的图示。在一个画廊里,一个人正在凝望一座城市的风景,而这片风景又扩展开来,包容了含有画廊和观望风景的人。在说不完、道不尽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必定也包括了他现在或者过去充当过的幻象作家及其无穷尽的幻象;而他必定也包含了他现在或者过去充当过的那位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企望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捕获无限的现实世界(尽管也许正是幻象作家巴尔扎克的无限的内心世界包含了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内心世界,因为前者的无限幻象是和《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无限性不谋而合的……)。
然而,全部“现实”和“幻象”只有凭藉写作才能体现出来;在写作过程中,外在性与内在性、世界和我、经验和幻景,显然都是由同一种文字材料讲成的。视觉的多形态景观和精神都被收入到由小写和大写字母、句号、逗号、括号组成的、整齐划一的行行文字之中,充满了像紧紧贴在一起的沙粒一样的符号的书页,在一个表面上再现着多姿多彩的世界景象,而这个表面是永远不变,却又变幻无穷的,正像沙漠旱风不断推移的沙丘一样。
.。
第五讲:繁复
5。繁复 (multiplicity)
首先,让我们来引用卡尔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的小说《极度杂乱的美鲁拉纳大街》(that awful mess on via merulana)中的一段:
英格拉瓦罗军官(officer ingravallo)聪明过人,却很贫穷,看样子靠沉默生活,在那黑漆漆的像阴暗丛林似的卷曲的拖把布条下睡觉。他聪明过人,有时候打破这种沉默和睡眠,发表演说,提出他对男人当然还有女人的种种事务的某种理论性观念(也就是说,一般性观念)。初看上去,或者不如说,刚一听见的时候,那些观念像是陈词滥调,而其实不是,所以,这些在他嘴里像硫磺火柴突然点燃噼啪作响的急切宣言发表之后,经过几小时,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好像经过一段神秘的孵化期那样,便又在人们的耳朵里复活。“说得对!”有关人士承认道,“英格拉瓦罗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这位军官认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动机,一个特殊原因的后果或者效果;这些大灾难更像是一个大漩涡,世界意识压抑中的飓风眼,是由种种原因交集造成的。他也使用像乱麻、缠结、混杂这类的字眼儿。但是,法律术语“动机,诸动机”他是避而不用的,虽然有失于违心。从亚里斯多德到伊曼努埃尔·康德等哲学家相继留传下来的见解——我们必须“在我们中间改变因果论的含义”,而且用多种原因取代一种原因——这一见解对他来说是一种中枢性的、持久的见解,几乎是一种偏激。这种偏激言辞从他肥厚、却相当白的嘴唇里软软他说出,而挂在他嘴角的纸烟头儿摇摇晃晃地好像是要陪伴他的惺松睡眼和那又苦又痴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在这种笑容中他通过“老”习惯来振兴睡意浓重的脑门子和眼皮以及漆黑拖布下面的下半张脸面。他就是这样,毫厘不爽地这样地来限定“他的”罪过的,“他们一找我……对的。他们一找我,就准是出了麻烦:有乱子,有结子要解。”他常常这么说,因为夹杂了那不勒斯和奠里土活,他的意大利语被弄得含混不清。
明显的动机、主要的动机,当然是一个。但是,罪恶是一系列狂风般地倾泄在这个动机上的动机造成的后果,这一系列的动机最后把已经脆弱的“世界理性”卷进恶的旋风(正象风的一览表中所列的十六种风拧成一个飓风,形成一个强风低压那样)。就像拧转一只鸡的脖子一样。他还常常带有几分倦意地说:“你不去找花裙子的时候,偏偏就能找到。”这是老掉牙的法国语“寻花问柳”的姗姗来迟的意大利文翻版。后来看样子他后悔了,好像他诽谤了夫人小姐们一样,于是决心改弦易辙。可是这又可能让他陷入困境。所以他只好闭口沉思,生怕话多失言。他的意思是,某种温情的动机,或者照如今的时髦说法,一定数量或者某一配额的情爱、“情欲”,也要牵扯到“兴趣之事”,牵扯到显然和爱情风暴风马牛不相及的罪恶之事。有些稍微有那么一点嫉妒他的直觉能力的同事,有几名更为谙熟我们时代众多邪恶之事的教士,有些僚属、小官,还有他的顶头上司,都一口咬定他看了奇书,所以从中摘取这些没有意思,或者几乎毫没有意思的奇谈怪论,可是这些胡话却比别的话更能迷惑天真汉和愚昧无知的人。他那些饶舌的术语是给疯人院里的大夫听的。但是,实际行动却大不相同!概念啦,思维推理啦什么的,应该留给耍笔杆的人,因为警察局的人小分队的实际经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需要大大的耐心、慈善和消化极好的胃。还有,如果意大利的全武行射击比赛还不见退烧的话,那就需要一种责任感,当机立断精神,和平的中庸态度,对啦,对啦,还需要雷厉风行之士,这些反对意见虽然合情合理,但是对他,对齐齐奥先生毫无作用:他依然自顾自地睡觉,空肚子高谈阔论,装模作样地吸那老是早早熄灭的半截子香烟。(英译本,1965,第4…6页。)
我一开讲就引用加达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今天的讲演主题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引子。这主题是: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
我本来也能够选择其他小说家来示范本世纪如此典型的这一“职业”。而我选择了加达,因为他是用我们的意大利语写作的,又因为他在美国少为人知(部分原因是他风格特别繁复,连意大利语原文中也颇显艰难),还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十分适合我的讲题:他把世界看成是“诸系统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每一个系统都制约其他系统,也受其他系统的制约。
加达一生都致力于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结子、一团乱麻;表现这个世界,同时毫不降低它无法摆脱的复杂性,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儿,毫不省略汇集起来决定每一事件的、同时存在的最为不同的因素。把他引向这种世界观的原因是他的精神修养、他的作家气质,还有他的精神病症。作为一名工程师,加达受过科学文化教育,学会了技术知识,并且倾心爱好哲学。这最后一项——爱好哲学——他是一直秘而不宣的:直到他于一九七三年逝世之后,在他的文稿中才发现他的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基础的哲学系统初稿。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