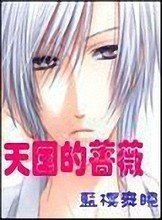金蔷薇-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幽静夜晚的
透明的夜色,五月夜的闪光,
这时候,我坐在房里,
写作或读书,不用点灯,
寥无人迹的街道上:
在沉睡的高楼大厦清楚可见,
而海军都大厦的尖塔如此明亮,
不待金色的天空上
降下夜雾,
朝霞早已一线接着一线,
让黑夜只停留半个时辰。
这些诗行不只是诗的峰顶。其中不仅有准确性、心灵的明朗和宁静,而且还包涵着俄罗斯语言的全部魅力。
即使我们想象俄罗斯诗歌消失了,俄罗斯语言也绝迹了,而只剩下了这几行诗,那么什么人都仍然能够看出我们的语言的丰富性和音调和谐的力量。因为在普希金的这首诗中,好象在魔幻的结晶里,凝聚了我国语言的一切罕有的特质。
赋有这种语言的人民,诚然是伟大的、幸福的人民。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吗?假如我们不保护我们的语言,而任不学无术的人随意败坏,使之成为贫乏而支离破碎的东西,那么我们便在文化面前,在我们的祖国和人类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愆。
..
第十一章 花花草草
,
不仅是一个守林人寻找词的解释。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种解释。而且在没找到之前,不能安静。
我记得有一次,在谢尔盖·叶赛宁的诗中,“潋纹”这个词使我感到多么惊奇:
在风吹成的潋纹之上,
或者在那沙原上
绳索套着项颈
把我领向忧愁之乡……
我不知道什么叫潋纹,但我感觉到在这个词里有着一种诗的内容。这个词本身就好象透露出这种诗意。
我很久没弄明白这个词的意义,而种种猜测都得不出一个定论来。为什么叶赛宁说。风吹的潋纹?显然,这个概念和风有点关系。可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词的意义从地方志作家尤林那里弄明白了。
所有跟俄罗斯中部的自然、生活方式、历史即使只有一点点关系的东西,尤林都孜孜地钴研过。
这一点他极象那些乡土专家和乡土爱好者,这些人专心研究,一点一滴地收集那些俄罗斯小城中还保存着的一切地方性的以及区域性的地理、动植物和历史的有趣的特征。
尤林到乡下来看我,我们一起到河对岸牧场上去。我们在干净的沙洲上往小桥那边走去。前一天刮过风,和往常一样,在刮风之后,沙上留下了波纹。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尤林指着波纹问我。
“不知道。”
“潋纹,”尤林回答说。“风把沙子吹散成这种波纹。所以叫这么个名字。”
我非常高兴,显然,和守林人给一个词找到解释时一样。
这就是叶赛宁写“风吹的潋纹”,并提到沙子(“或者在那沙原上”)的原因。我最高兴的是,象我所预料的一样,这个词表现了大自然的普通的诗的现象。
叶赛宁的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今名叶赛宁诺)在奥卡河对岸不远。高耸的河岸的突出部分,遮住了这个村子。
太阳总是从这边落山,我从那个时候起,就觉得叶赛宁的诗,出色地表现了奥卡河彼岸的广漠的落日和潮湿的草原上的黄昏,每逢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雾,还是林中蓝色的焦烟,弥漫在原野上。
在这仿佛寥无人迹的草原上,我有过多次不同的事故和突然的会遇。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湖上钓鱼,湖岸高耸陡峭,长满攀缠的黑莓。湖的四周围绕着古老的垂柳和黑杨,所以在湖上甚至在晴朗的日子里,也是无风昏暗的。
我坐在水边长得密密层层的树丛中,以致从岸上完全看不见我。菖蒲沿湖边开着黄花,再往前,在湖水深处,时时从水底冒出气泡——大概是鲫鱼在钻淤泥寻找食物。
在上边,在我头顶上,开着有半人高的花,乡下的孩子们正在那里采酸模。听声昔,那儿有三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子。
两个小姑娘在学着孩子多的乡下女人的模样说话。她们大概都在摹仿自己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玩意儿。第三个小姑娘总没说话,只是尖声尖气地唱着:
在空袭请报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往下的歌词她不知道了,在沉默片刻之后,又重复起关于空袭警报的歌儿来。
“请报,请报!”一个哑嗓子的小姑娘生气地说,“整天价,吃苦受累,就为了能把他们,这一群崽子,送去上学,可他们在学堂里能学个什么?连话都不会说!是‘警报’,不是‘请报’!等我告诉你爸爸,叫他教训教训你。”
“我那彼契卡前两天,”另外一个小姑娘说,“算术吃了个两分。让我把他这顿捶呀,把手都打木了。”
“全是编的吧,妞儿卡!”小男孩子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是彼契卡的妈妈打的他。就打了两下。”
“瞧啊,鼻涕鬼!”妞儿卡喝道。“你再讲讲看!”
“小姑娘们,你们听着!”哑嗓子的姑娘高兴地喊道。“咳!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就在这儿,雀滩附近,有一棵灌木。天一黑,就开始从下到上冒蓝火苗!冒的可凶着哪!一直冒到天亮。连走到它跟前去都不敢。”
“它干吗冒火苗呢,克拉娃?”妞儿卡吃惊地问。
“就是说有宝,”克拉娃回答说。“下边埋着宝。有金铅笔。谁若是拿那支铅笔写上自己非常希望的东西,——要啥就有啥。”
“给我!”小男孩子要着说。
“给你什么?”
“铅笔!”
“你别跟我胡缠!”
“给我!”小男孩子喊道,而且忽然粗着嗓子哭了起来,又讨厌,又刺耳。“给我铅笔,臭丫头!”
“啊,你这样吗?”妞儿卡喊道,立刻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倒霉蛋!干吗我把你生下来了!”
小男孩不知道为什么立刻不哭了。
“可是你呀,亲爱的,”克拉娃用一种假装的温柔的口吻说,“别打自个儿的孩子。容易打晕过去。你跟我学——教他们懂事。若不然长大了也是一群呆子,对自个儿,对别人都没有一点儿好处。”
“能教他什么?”妞儿卡气愤地回答说。“你教教他看!他会给你个样儿瞧瞧!”
“不教怎行呢!”克拉娃反驳说。“什么都得教给他们。他这会儿跟着我们,哼哼唧唧地,你看,这一左一右全是花,一个跟一个不一样。有几百样儿。可他懂得什么呢?屁也不懂。比方说,这朵花,连叫个什么他都不晓得。”
“夜盲草,”男孩子说。
“这才不是夜盲草,这是肺草。你才是夜盲草哪!”
“飞草!”男孩子甚至有点高兴地重复说。
“不是‘飞草’,是‘肺草’。字眼儿咬清楚。”
“肺草,”男孩子急忙回答一遍,立刻问道:“这是什么花,这个粉红色的?”
“这是薄荷。你跟着我说:薄荷!”
“薄荷不就得了,”男孩子应着说。
“你别跟我得了不得了的,你就光跟我学着说。这个是绣线菊。可香着哪!可娇着哪!你要不要,我给你掐一朵?”
小孩子,看来很喜欢这个游戏。他一面哼哧着,一面极认真地跟克拉娃重复着花名。她飞快地说了一大堆名字:
“你看这是猪殃殃。这个是睡莲。就是那个带白铃铛的。这个是剪秋罗。”
我听着,只是惊讶。小姑娘认识许多花。她叫了许多名字,有车叶草,甜香花草,石竹,荠菜,马兜铃,皂根,唐菖蒲,缬草,百里香,金丝桃,白屈菜和很多别的花草的名字。
但是,这一堂出色的植物课,突然给破坏了。
“我扎了刺了啊!”男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们把我领到哪儿来了,臭丫头?!哪儿都是刺!我回不去家了!”
“喂,小丫头们!”在远处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喊道。“你们干吗欺负小孩子?”
“帕霍姆老大爷,他自个儿扎了刺!”准确发音的捍卫者克拉娃喊道,同时低声添上了一句说:“欧,欧,欧,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自个儿不管谁都要欺负!”
听得见老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的声音。他往下,往湖上看了一眼,看见了我的钓竿,说道:“这儿有人钓鱼,你们嚷到半天云上去了。这么大的牧场还不够你们跑的!”
“在哪儿钓鱼呢?”男孩子急忙问道。“让他给我钓一会儿!”
“往哪钻!”妞儿卡喊道。“就欠掉进水里去了,不听话的孬种!”
孩子们很快就走了,我就这样没看见他们。老头儿在岸上站了一会,思索一下,小心地咳了两声,然后用一种犹豫不决的声音问道:“先生,您身上带着烟没有?”
我告诉他有,于是老头儿从斜坡上滑下来,因为挂到了黑莓的蔓藤上,口里不断地骂着,发出可怕的声音,到下边来跟我要烟抽。
原来是一个矮矮的糟老头子,不过手里却拿了一把大刀。有一个皮套。老头子一看出我对这把刀怕是有点担心事,他便急忙说:“我来砍柳条。编筐子和篓子。每天编点儿。”
我跟老头儿说,方才在这儿有一个小姑娘,非常有意思,什么花草都认得。
“您说的是克拉娃吗?”他问道。“那是集体农庄的饲马员卡尔纳乌霍夫的丫头。她怎能不知道呢,她奶奶是全省数一数二的草药医!您和她奶奶谈谈。保您听个够。不错,”他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说。“每一种花都有自个儿的名称……也就是说,这全登记下来啦。”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老头儿又要了一支烟就走了。不久,我也走了。
当我从树丛钴出来到牧场大路上的时候,在前方,远远地看见了三个女孩子。她们抱着一大把花。其中有一个拉着一个赤足的小男孩子,他戴着一顶很大的便帽。
小姑娘们走得很快,象一溜烟似的。然后传来一声尖声尖气的声音:
在空袭请报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太阳已经在奥卡河对岸,叶赛宁诺村背后落下去了,浅红色的斜辉,照耀在绵亘在东方的茂密的森林上。
。。
第十二章 辞典
~
有时候,在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出现。譬如这样的想法:若能编几部新的俄语辞典倒不错(当然现有的一般辞典除外)。
一种辞典,譬如说,可以收集与自然有关的词汇,另一种收集好的准确的方言,第三种收集各行各业的用语,第四种收集乱七八糟的废字,一切官样文字,洋字和败坏俄罗斯语言的鄙俗的字。
最后的这部辞典用来教人们抛弃那些内容贫乏,支离破碎的言语。
收集跟自然有关的词汇的想法,是那一天我在草原的小湖上,听到那个哑嗓子的小姑娘说出各种花草名字的时候想到的。
这当然应该是一部详解辞典。每个字在解释之后,应该从作家、诗人、学者们的著作中引用一些和这个字有科学的和诗学的关系的断片。
譬如在“冰柱”一词的后面,可以引用普利希文作品中的一个片段:“垂在陡岸下的稠密的长树根,现在在河岸下黑暗的凹陷处变成了冰柱,越来越大,已经触到了水面。而当微风,即使是最柔和的春风,吹皱水面,涟漪在峭壁下够到冰柱的尖端的时候,也漂动了冰柱,冰柱摆动着,彼此相碰,发出声音,这种声音是春天的最初的声音,是风神之琴。”
而在“九月”一词的后面,最好附上巴拉廷斯基诗作的一个断片:
九月了!太阳迟迟才出山,
发出闪闪的寒光,
阳光在摇荡的水面上
漾着朦胧的金光。
想着这些辞典,特别是想着“自然界的”词汇的辞典时,我把词汇分为“森林的”,“田野的”,“草原的”,关于季节的,气象的,水和河川湖泊的,以及动植物的。
我认为这种辞典应该编得可以当作一本书来读。这样才既能给人关于我们的大自然的概念,又能给人关于俄罗斯语言的丰富多采的概念。
当然,这项工作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终生工作也是不够的。
每次当我想到这种辞典的时候,便想少算二十年岁数,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来编这部辞典———我没有这种知识——不过即或参加编纂工作也好。
我甚至动手为这种辞典作了一些札记,但照例都丢了。要单凭记忆想起来,差不多已是不可能的了。
有一次几乎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搜集花草的名字。我从一本旧的植物手册上知道了它们的名称和特性,同时记到我的笔记本里去。这是一件极有趣的工作。
在这以前,我从没想过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其目的,从没想到过每一片小树叶,每一朵小花,每条根须和种籽都是那样复杂而完整的。
人们有时纯粹从外表,甚至是过份地感到这个目的性。
有一次在秋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荒凉的奥卡河旧河床上捕了几天鱼。这个河床在几百午前就与奥卡河没有关系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深而长的湖。四周蔓草纵横,很难走到湖边去,而有的地方根本不能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