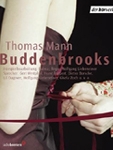布登勃洛克一家-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直到下午四点吃午饭时才会见到自己的妻子。
由于商业活动的存在,老屋的一楼还一直保持着活跃和生气,但是楼上现在却空荡荡的,说不出的寂寞冷清。小伊瑞卡已经由卫希布洛特小姐收纳下作了寄宿生,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带着自己的四五件家当在一个寡妇中学教员,一位克罗色敏茨女博士那里找到了便宜的寄宿处。甚至连老仆人安东也因为少主人更需要他,已经搬到那边新居去了。有时克利斯蒂安一上俱乐部,下午四点钟圆桌旁边就只孤零零地剩下老参议夫人和永格曼小姐两个人。圆桌四周的加板自然是用不着了,在悬着一幅又一幅的神像的空旷的大餐厅里,这张圆桌显得异常渺小。
在老参议员去世以后的日子里,孟街的社交生活也消沉下去,除了偶尔有些神父牧师之流的人物来拜访以外,老参议夫人只有在星期四能看到一些亲友,此外,几乎没有什么来访的客人。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儿子和新媳妇却已经举办过一次宴会了。这次宴会办得很排场:餐厅和起居间都摆满宴席,特别请了厨师和临时工人;还特意准备了吉斯登麦克厂造的酒,宴会从五点钟开始,直到深夜十一点还听得到人们的喧哗笑语。朗哈尔斯·哈根施特罗姆、吉斯登麦克、胡诺斯、鄂威尔狄克、摩仑多尔夫几家人,商人和学者,结了婚的夫妇和单身汉,都得到了满意的招待。饭后大家又玩惠斯特牌戏,欣赏了几段美妙的音乐演奏。这次宴会在证券交易所一直被谈论了一星期之久,倍受赞赏。这一次宴会证明,参议的新婚妻子不愧是交际场中的老手……当天晚上,屋子里还燃着烧残的蜡烛,桌椅凌乱,空气里残留着美酒佳肴、香水、雪茄、咖啡、女人身上和餐桌上摆着的香花交织成的浓厚香气,当只剩下夫妇两人的时候,托马斯握住他妻子的手对她说:“太好了,盖尔达!
我们没有什么要红脸的。这种事很重要……我不喜欢办舞会,把这里弄得乱糟糟的,再说地方也不够。但是成家立业的人在我们这儿会感到乐趣的。这样的宴会固然花钱多一点……可是物有所值。
”
“你说得对,”她回答道,一边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花边,她的洁白胸脯隐约从花边底下透出,如同洁白的大理石。“我也喜欢宴会,不喜欢舞会。宴会特别能给人一种舒坦的感觉……我今天下午玩了一会乐器,真是特殊的享受……现在我的脑子好像已经死了,即使洪水涌进来,我觉得我也不会改变面色。”
第二天十一点半参议在母亲身边坐下吃早餐的时候,他给她念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妈妈:
首先我要请求您的原谅,我已经到这里八天了,一直还没有写信,实在太不像话了。这里要看的东西太多,忙得我一点工夫也没有……这些事我下边再谈。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这些亲人,您、汤姆、伊瑞卡、盖尔达、克利斯蒂安、克罗蒂尔德和伊达身体都好吗?你们是我的生命。啊,这些天我看了多少东西啊!雕塑品陈列馆啊、绘画展览馆啊、皇家酿酒厂啊、皇家剧院啊、教堂啊,以及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一切留待我以后口头告诉你们吧,否则我就得给你们写本小说了。我们还乘马车到伊萨尔峡谷去了一次,明天打算到屋尔姆湖远足。日程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安排下去。伊娃对我很好,尼德包尔先生,那位酿酒厂经理,对我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们住在城内一个非常美丽的广场旁边,广场正中有一口井,就像咱们家市场上的井一样,我们住的房子离议会大楼非常近。我简直无法形容这所房子的美丽!这所建筑物从上到下绘着五彩缤纷的图画,什么屠龙的圣乔治啊,穿着盛装、佩着纹章的巴伐利亚的老诸侯啊,你们想一想吧!
是的,我一下车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慕尼黑。这里的空气很富于强健神经的作用,我的胃病现在一点也不犯了。我很喜欢喝啤酒,喝的很多,尤其是因为这里的水不很清洁。但是对这里的膳食我还不很习惯。这里蔬菜吃得太少,面粉则太多,譬如说在汤汁里吧,真叫人头痛。这里的人不会享受真正的烤小牛肉,因为肉铺的人总是把肉切得乱七八糟。此外我在这里也吃不到鱼。整天喝啤酒就黄瓜和马铃薯凉拌菜,想起来真是荒谬,我的胃已经咕噜噜地提出抗议了。
我想,你们也会理解,人们初到一个新环境总要使自己习惯一大堆新事物的,我就像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使用的是不同的铜币,跟普通人,跟佣人说话彼此了解也有困难,我的话对他们来说有些快,对我说来他们的话吉利咕噜一点也听不清……此外这里还有天主教。你们知道,我恨他们,我看不起这种教……念到这里参议笑了起来,他手里还拿着一块涂着香草奶酪的面包,仰靠到沙发上。
“看你,汤姆,有什么好笑的?!”他的母亲说,用中指在桌布上敲了两下。“她能如此坚持她父亲的信仰,鄙视基督新教以外的那些花言巧语,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知道,你在法国和意大利日子久了,不由自主地就会同情起天主教来。然而这不是你的宗教感,汤姆,这是另外一种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我们虽然讲究宽恕,但你也不能以嬉戏的态度来面对这种事情。我一定要祈求上帝,让他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使你们在这方面也懂得严肃起来。使你和盖尔达,因为我了解她也是属于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之列的。我出于责任心而对你说的这些话,不会使你生气吧?”
他接着念下去:
井泉上边立着一个圣母像,我从房间里就可以看到。常常有人来给她献花圈,一些普通老百姓带着玫瑰花的花环跪着祈祷,真令人感动。虽然书里面写的是:回到你的小屋去。街上常常有僧侣走过,他们总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这座城市里居然会发生如此的事情!昨天有一个地位很高的教会中的人坐着马车经过戏院街,也许是一位大主教,一位年高有德的人……不管是什么人吧,这辆马车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他居然从窗户里向我狠狠地盯了两眼,和一个禁卫军少尉的眼神没什么两样!您知道,母亲,我一向就不把您那些传教师、神父之类的朋友看在眼里,但和这座城市中的教会人物相比,那位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真不啻小巫见大巫了。
“这是什么话!”老参议夫人不由得喊起来。
“真是咱们的冬妮!”参议说。
“什么,汤姆?”
“喏,她多半是先逗弄了他一下……看他会不会有邪念。我是知道冬妮的!反正这两眼是非常使她开心的……也许这就是那位老先生的初衷。”
老参议夫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仔细追究,他接着念下去:
前天尼德包尔先生举行了一次晚宴,有意思极了。虽然人家的谈话我有时跟不上去,我觉得他们的语调有时模棱两可,他们甚至请了一个宫廷的歌剧演员来表演助兴,还有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求我,他要给我画一张画像,被我宛拒了,我觉得不太合适。我最感觉兴趣的是跟一个姓佩尔曼内德的先生的谈话……这个姓你们听说过吗?……他是一个经营啤酒原料忽布的商人,一个讨人喜欢的有趣的人,已经过了中年,却还是独身。吃饭的时候他和我同席,饭后的时间我也大半跟他在一起,因为在所有这些来客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新教徒,而且他虽说是慕尼黑人,老家却是纽伦堡。他一再向我表示,我们的公司他久已闻名,他说这话时语气极为恭敬。汤姆,你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么高兴。对咱们家的情形他打听得也很仔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甚至连伊瑞卡和格仑利希的事他也问到了。他常常到尼德包尔家来,他也可能和我一同参加明天的远足。
下次再谈吧,亲爱的妈妈,我无法再写下去了。如果生活得健康愉快,像您常常说的那样,我还要在这里待三四个星期,以后你们就可以听我亲口讲慕尼黑的事了,在信里我真不知道从哪下笔。但是我可以说,我非常喜欢这里,只是需要训练一个会做像样的汤汁的女厨子。您知道,我的年岁也不小了,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我足够的兴趣了。但是如果,譬如说伊瑞卡以后能够健康幸福地在这里结了婚,我绝对不反对。
念到这里参议禁不住又把早餐搁下,笑着靠到沙发上。
“她可太有意思了,母亲!要是她想做假,简直找不出第二份儿来!我最佩服她这一点。她简直不会装假,她的装假的技术还差得远呢……”
“是的,汤姆,”老参议夫人说,“她是个好孩子,幸福对她而言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接着她把信读完了:
……………慕尼黑,一八五七年四月二日玛丽安广场五号
d
第二章
!
冬妮在四月底回到娘家来了,虽然她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生活,现在一切又变成了老样子,她又要参加祈祷,又要在“耶路撒冷晚会”上听丽亚·盖尔哈特朗诵,她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变化,快乐并充满希望。
她是从布痕回来的,她那作参议的哥哥亲自到车站接她,跟她一起乘马车回来。马车一走进霍尔斯登城门,参议就禁不住恭维她说,家里的人除了克罗蒂尔德以外,她实在是最美丽的一个。“噢,天啊,我恨你,汤姆,”她回答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挖苦一个老婆子呢……”
但这恭维话确实是发自参议的肺腹:格仑利希太太的确出色地保持住她的风韵。她的金灰色的头发非常茂密,她在头边梳起两个蓬,然后从两只娇小的耳朵上面盘到后面去,用一只贝母的梳子在头顶高高挽起一个髻子;她的灰蓝色的眼睛仍然闪露着温柔的目光;此外,她的美丽的双唇,她的美丽的鸭蛋脸和柔嫩的肤色,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她还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少女,谁也不会猜出她已经年满三十了。她戴着一副非常精致的金的吊耳环,这种耳环在祖母一代就非常时兴,只不过式样略有不同罢了。缎子翻领和平绦子肩饰,暗色的薄绸衣服,松松的腰身,使她的胸部望去丰满而柔和,使人浮想连翩。
她的心情确实不错,逢到星期四,当布登勃洛克参议,布来登街的几个本家,克罗格参议,克罗蒂尔德,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带着伊瑞卡来用餐的时候,她就有声有色地谈起慕尼黑来,谈那里的啤酒,谈通心粉,谈留给她印象最深的宫廷马车,当然还有要给她画像的那位画家。她有时也顺便提到佩尔曼内德先生,而如果遇到菲菲·布登勃洛克说出下面这样的话,像什么这样的旅行惬意固然惬意,但对实际的结果来说,却不起什么作用,这时格仑利希太太就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不理睬她,向后仰着头,却又尽力把下巴贴到胸脯上。
此外她又新添了一种习惯,只要门铃在过道里响起来,她就急急忙忙跑到楼梯口去看来的人是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件事大概只有伊达·永格曼……冬妮小时的保姆和多年的挚友……一个人知道。永格曼常常对她说:“小冬妮,我的孩子,他早晚会来的。他是一个精明的人……”
家里的人也都感谢冬妮给家里带来了欢快的气氛,说实话,这里的空气令人沉闷的要死。原因就是,随着时日的推延,公司主人和他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改好,反而可悲地日渐恶化下去。
两兄弟的母亲,老参议夫人忧虑地看着事态的发展,为了居中调停,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她虽然一再规劝克利斯蒂安应该更规矩地上班,克利斯蒂安却只是心不在焉地以沉默代替回答。有时他的哥哥也这样指责他,这时他的态度就变得严肃不安,显出一副忧心忡忡、羞愧难当的样子。他并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接连几天,在工作中投入极大的热情。但是在哥哥身上却越来越发展一种对兄弟的恼怒和鄙视,虽然克利斯蒂安对哥哥的指责并不辩解,只是深沉地、目光惶惑不安地表示接受,哥哥的恼怒和鄙视却仍旧不能为之稍减。
参议的繁忙的业务和他的神经状态不允许他同情地或至少平心静气地倾听克利斯蒂安对自己无法治愈的病症作详细的描述,在他母亲和妹妹面前他甚至厌恶地称这些病症为“愚不可及又讨厌无比的观察自身的必然结果。”
克利斯蒂安的腿疼病,那种难以捉摸的酸疼,因为采用了种种外部治疗,已经有一个时期不出现了。但是在饭桌上吞咽不下食物的现象却依然常常发生,而且最近又加上了呼吸困难,染上哮喘病。好几个星期克利斯蒂安一直觉得这是肺病,总是皱着鼻子极其详细地把病况和病历叙述给家里人听。格拉包夫医生被请来问计。他肯定地说,他身体中的主要器官十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