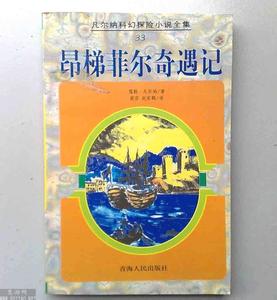曼斯菲尔德传-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义。她过去一直采用模拟手法,现在则发现了在整个作品中从头至尾使用模拟的方法。另一更为明显的影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笔调中,在肮脏邋遢的叙述者的自我表白中,都能找到不少《地下室手记》①的痕迹。《我不会说法语》是凯瑟琳称为自己“反对腐败堕落的呼喊”的短篇小说,表明自己艺术目标的最具说服力的叙述之一,下面的一段话常被引用:在写作这场游戏中我有两个“开球”,其一是快乐——真正的快乐——在波琳促使我写作,此种写作我只有处于极乐的平静状态下才能进行,此时某种绝妙可爱的东西似乎在我眼前展开,像一朵从未意识到冰霜寒冷的鲜花——知道周围的一切温暖,柔和,静静以待。我一直竭力想将其表达出来。
另一个“开球”是我旧有的,如果没有体验过爱情,那会是我唯一的:①陀斯妥耶夫斯基著名作品之一。——译注并非仇恨或毁灭意识(两者都是采取蔑视态度的真正动机),而是一种极端的绝望情绪,感到一切都像杏花和圣诞糖果一样注定要愚蠢任性地走向毁灭。对了,当我掏出一张香烟纸时,正好找到了准确的词来形容它——反对堕落的呼喊——这的确是一矢中的,不是抗议——而是呼喊。当然堕落也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
目前我已处于这第二种状况,全力以赴驶进了深深的海洋。。《我不会说法语》首次问世时由私人出版社印刷的小版本非常珍贵,当时未经删改,尚未磨去锐力,后来则再也没有重印,因而故事的原来形式就鲜为人知了。
故事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卢尔?都克的愤世嫉俗的年轻波斯人,“像一个洒了香水的狐狸似的法国人”,他坐在咖啡馆内沉思,而整个故事则经过他的思绪。
他为两份报纸撰稿,但爱好严肃文学,他还喜欢具有英国风味的东两:身穿英式大衣,寓所内有一张英式书桌;他喜欢那个关于“一个鱼丸”的滑稽歌曲;他对英国年轻作家迪克?哈蒙有一种同性恋似的喜爱,他们曾在巴黎见过面,后者更喜欢他自己的母亲。
在咖啡馆,都克拿起一本记事簿,发现有人在那儿写下了“那句愚蠢的套话‘我不会说法语’”,而正是这句话突然使他回想起关于迪克和那个孤独无援的漂亮英国女孩的悲惨故事,迪克把她带到巴黎后不久就抛弃了她。
迪克称她“老鼠”(无疑是“老虎”的余音),她也没有其他名字。他们请都克在一个“体面”的旅馆预订两个房间,他去车站接他们。老鼠优雅柔弱,身披黑毛镶边的黑色长斗篷,双手藏在小小的皮手笼内——“老鼠第二”。
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说法语”,她在巴黎不认识别人。
他把他们领到房里去,休息了一会儿,老鼠请求“立即送茶来!”他不久就察觉到他们之间一切都不对头;然后迪克跑到另一个房间去“写一封信”:“是给我母亲的”。他再也没有回来;尴尬不安地等了很久以后,老鼠走到对面房间,发现留给她的那封信:老鼠,我的小老鼠:这没有用,这不可能,我不能坚持下去,噢,我的确爱你,我的确爱你,老鼠,但是我不能伤害她。。都克(当他坐在咖啡馆回忆这个小小悲剧时,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个男妓)不能安慰老鼠,她避开他温柔的帮助,对他所说的“请把我看作你的朋友”的话感到怀疑,但是接受了明天给他打电话的建议,因为“一切都太困难了”——因为“我不会说法他就这样离开了,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故事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卡尔科的《纯真》的反驳,默里在前一年7月曾为《文学副刊》评论过那篇作品,她现在告诉他“题材,即‘说法语’,当然是取自于卡尔科,格特勒以及天知道谁,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你当然明白),我并没有故意伤人,的确没有。”
实际上故事原稿是紧接着一段话后开始的。
那段话开头说“但是,天哪,天哪,我多么痛恨法国人,他们总处于发情期,看看他们怎么跳舞,嗅着一个女人的裙子吧。。”将前半部分寄给默里时,凯瑟琳说自己刚才重读了一遍,想不出她“究竟从何处得来的故事——取自于现实生活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个我讨厌的非洲洗衣妇——但仅仅是讨厌而已——而迪克?哈蒙,当然是,有些是——”。
她在此处中断了,不难看出迪克?哈蒙“有些像默里”,而戴着皮手笼的老鼠则部分是他1912年带到巴黎去的凯瑟琳,是6个星期前离开伦敦滑铁卢车站的凯瑟琳,当然肯定也是他1911年在巴黎抛弃的玛格丽特,借口该责备母亲。而都克则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①的尼克?卡罗威②一样,是凯瑟琳以自己的眼光观看自己,这个角色蕴含着对她聪明的自我的自我谴责一对《纯真》中四处剽窃的维尼的自我谴责。
两年以后,当康斯特布尔准备出版包括《我不会说法语》在内的选集时,迈克尔?萨德勒③坚持要删去某些片断,这些片断都与性的滥用有关,其本身目的在于使都克的自我描绘更清晰、邪恶,正是其刻薄的讽刺意味才使故事的意图一览无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凯瑟琳的《荒原》。
1920年,听说康斯特布尔要求某些删改,凯瑟琳说她对迈克尔?萨德勒感到极端愤怒,绝不会同意:“难道要我为了40个英镑摘掉故事的眼睛吗?。。轮廓将变得模糊不清,那些清晰的线条不能删掉。。。”第二天,她作了让步,认为自己过于任性,然而后来又再次改变想法,后悔不该删去一个字:“我错了——大错特错。”
经过那次《日与月》的梦境体验后,凯瑟琳又着手某个“了不起的故事”;但这不过是《幸福》。这个故事一直受到称赞,享有盛名,实际上极其冷酷无情,其中的女人是人,男人却不过是些类型,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疏远隔离,伯莎④自己的描写则汲取了痛苦的现实:。。在她心中仍有着那块光明灿烂的地方——那一阵小小的火花出自那个地方,这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她几乎不敢呼吸,唯恐将火焰煽得更旺。然而她深深地、深深地呼吸着。
——但是她的丈夫哈里是一个庸俗的证券商人,而愚蠢的埃迪似乎来自《笨拙》描绘的一场网球聚会。附庸风雅的伦敦客厅式的嘲讽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嘲讽一样聪明肤浅,他自己就是埃迪的原型。
t。s。艾略特在他的《崇拜异神》中虽称赞故事“处理微小素材的完美手法”,也公正地评论其“道德寓意则微乎其微”。
3月悄悄地过去,没有再写什么。现在凯瑟琳一心想的只是回家与默里团聚,摆脱埃达——她威胁说要坐着她的出租车去雷德克利夫街默里的住处帮凯打开行李,尽管有默里在那儿:“旅行后一定得有人好好照看你”。凯瑟琳说,“如果你看见她说这话时眼睛怎样牢牢盯着我,就会明白我为什么①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1),美国小说家,其主要作品之一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泽注②《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故事讲述者。——译注③负责出版凯瑟琳小说选集的编辑。——译注④《幸福》中的女主角。——译注恨她。”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居于这次蔑视战争的法国旅行之首的一场灾难。
两位妇女1918年3月21日离开班达尔,打算直接回伦敦,凯瑟琳的护照只适用于巴黎,因此她们去了巴黎——春天的巴黎——就在这一天德国开始使用新的远射程大炮轰炸这个城市,在一片恐慌中,再也不能指望渡过海峡,她们在索朋①附近找了一个旅馆安顿下来。
加农炮每隔18分钟就发出一阵可怖的声音——或者一天一次,从没有一定规律。坐在旅馆地下室的煤堆上,“听着该死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说话”,这一切太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情节了。而默里却似乎更欣赏象征性的联想。
他给凯瑟琳写信说,“我处于一种现在常有的心理状态,我在一切事物上都看见了象征。。这几个星期难以形容。。似乎我的灵魂,以及比我灵魂更为珍贵的东西,一种灵魂相依的美好理想从我这儿被拽了出去,变成了飞絮或亮晶晶的气泡。”埃达一辈子都对她的宝贝所爱的男人的这种专注自我很反感。
两个女人在一个公共食堂每天紧张地工作几小时——这是凯瑟琳战时唯一有记载的工作。她每天都要去邮局拿信,去军事护照处,再去邮局。埃达说她们的钱用完了,凯瑟琳必须去见“某个她情愿付出任何代价而不愿见的人”,带了一些现钱回来。埃达不敢问,但怀疑也许此人是卡尔科(此人更可能是贝阿特丽丝?海斯汀斯)。
可怕的三个星期变成了凯瑟琳称之为“另一个索多姆和哥摩拉①”。当一颗炮弹带着震耳欲聋的响声落在附近时,她跑去看:一幢房子的整个屋顶都“似乎被啃去了”,道路上盖满了瓦砾,街两旁的树才长出新绿,已被炸断了许多枝条,但在残枝上还挂着许多碎衣服,破纸片——一件睡衣,一件无袖衬衫,一条领带,都在阳光下零星挂着,然后:两个工人来清理废墟,在瓦砾下发现了一件女人的丝衬裙,他把它穿上,跳了一两步舞,引起众人的哄笑,这让我充满了恐惧,再也不能忘记他那舞动的双脚,他龇牙裂嘴的笑容,折断的树枝和炸毁的房子。
观察人性的这三个星期本身就是堕落,“这不是巴黎,这是地狱”,凯瑟琳写道,说埃达在那个地方扮演了魔鬼卫土的角色:“在每一家店前停下脚步来,咕哝着说,‘我真想哪一天看见你双手戴满了精巧的戒指’。”
凯瑟琳自己的梦想是一回到伦敦就尽快同默里结婚——不想在每一封电报、文件上被称为“波登太太”,只有这个希望支撑着她,使她能抵挡生命的损害和浪费。然后,他们就要去找一所“苍鹭”,她甚至还抱着这样一种女人的希望:“我想去看看医生,问一下自从那个星期天下午玛莎姨妈①就没有来过,是否有什么值得庆贺的理由。当然要等到我问了以后才敢抱有希望。”
但是她并没有怀孕,离开班达尔前就病得很严重,后来又到处漂泊流浪,①巴黎市区名,——译注①索多姆和哥摩拉均为《圣经》中传说的上帝摧毁的罪恶城市。——译注①凯瑟琳对月经周期的委婉称呼。——原注弄得惊恐憔悴(护照照片上的人像鬼一样)。最后,在1918年4月10日终于同埃达一起逃离了法国,渡过了海峡,此时已经病入膏盲了。
4年前人们就知道“欧洲的历史”已到了尽头,家庭生活以及其对艺术的帮助也面临威胁,华兹华斯的英格兰,文学家和妻子共有的英格兰,可爱的古老村舍里可以写作,燃烧秋叶的火堆中冒出缕缕轻烟——凯瑟琳和默里的这一切希望也破灭了。
/d/
第8章等待“大象”
;
我隔壁房间那个人也患着同我一样的疾病,夜间醒来我听见他在翻身,然后他咳嗽,我也咳嗽,静了一会儿以后,我咳嗽,他又咳嗽,就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觉得我们两人像黎明未到就互相鸣叫的两只公鸡,在那远远隐僻的农庄上。
——《日记》
1918年6月
渡过海峡后几天之内,凯瑟琳去看了英格医生,知道自己“的确患了肺脖,但她说服英格相信疗养院“不能救我,只会让我死得更快”,因此她准备“在家治疗”,也许就在汉姆斯特。她打算冬季到来前找到一所房子,先同默里住在雷德克利夫街,属福尔汉区①,她喜欢那儿,因为那儿没有一点布尔乔亚味,住在那儿的人来去都不戴帽子。当然默里的想法不同,他的房间见不到什么阳光,她又一直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他上班时,她要出去买东西。
她一点也不了解现在伦敦排队买东西是什么情景。
4月29日,凯瑟琳终于获准与波登离婚,5月3日,由j。d。弗格森和多萝西?布雷特作证人,凯瑟琳与默里去了结婚登记处,终于正式结为夫妇,凯瑟琳摆脱了那个每次看见就使她深感愧疚的姓氏,马上不无骄傲地写了一封信给维吉尼亚?吴尔夫,落款用了新的姓名缩写k。m。m。然而,她对这种布尔乔亚的快乐又有种矛盾心理,因此当她们会面时,她又对其加以贬低,这也许是一种对抗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那伙人的自我防卫。结婚几天以后她去吴尔夫家吃饭,不久维吉尼亚就写信告诉莫瑞尔夫人说发现凯瑟琳仍一如既往地神秘,迷人,但又觉得结婚像聘请一名打杂女工一样平淡无奇,“她的迷人之处部分来自于她必须发些荒谬的议论。”
事实上她结婚的那一天也是个悲惨的日子:我们的婚礼,你不能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本来应该充满阳光——虽然生活中有其他不如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