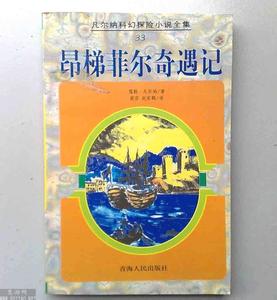曼斯菲尔德传-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圣诞节这一天,其他人在庄园内聊天,散步,以便增加食欲,她写着那场戏。后来“李敦爷爷”给大家念了一篇自己写的关于阿诺德博士①的文章,这是后来使他一举成名的书中②的一个章节,满是对在座的人开的玩笑,读到一段字句抑扬顿挫的话,结尾是这样的:“尊敬的柏德勒先生说‘公学是罪恶的中心和温床’”,起居室内一片吃吃暗笑声。
①牛津大学学院之一。——译注
①朱利安?赫胥黎(1887~1975),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哥哥。——译注②即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曾写过名为《在德国公寓里》的短篇小说集,于1911年出版。——译注①阿诺德(1795~1842),英国教育家。曾任拉格比公学校长,对英国的公学教育有极大的影响。——译注②即斯特雷奇191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人物》一书。——译注最后,到了节礼日的夜晚,凯瑟琳写的戏上演了,卡林顿告诉她哥哥说那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俄国戏,了不起的机智,很好。”而奥尔德斯?赫胥黎则说“我们表演了一出凯瑟琳创作的戏,即席表演,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默里扮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角色,李敦则扮一个极其邪恶的老祖父。”
第二天,大部分客人都乘火车消失在伦敦的浓雾中,但与此同时,邮局给奥特琳送来了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包裹,给奥特琳夫人带来了惊恐;如果早到几天的话,那个圣诞节就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劳伦斯(根据她的要求——她已听到了一些传闻)把自己在康沃尔写的小说的手稿寄给她①,当她读了以后,感到自己的脸都吓白了。
她读到自己被安上了各种各样的名称,从性欲狂的“老巫婆”直到衣着邋遢的“堕落的同性恋者”;在一个情景中甚至描写她向“庄重的弗丽达”求爱。房子、花园以及住在里面的人都描写得细致入微,整个小说写出来似乎就是为了侮辱她,而她从惊恐中唯一能够找到的安慰是“所有最糟糕的部分都是弗丽达的笔迹”。
显然,她认为实际上是弗丽达写了那些部分,也许是这样的(在那小屋里弗丽达闲着没有事干);或者此手稿只是她帮着整理的多余的一份,她有时也帮着抄写一些。
奥特琳马上就写信给罗素和凯瑟琳告知此事,凯瑟琳说她希望能够说服劳伦斯不要发表此书,又说“我认为离群索居使他心中产生一种疯狂”。后来,当她从布雷特那儿了解了更多情况,但自己仍未读过此书时,说道:毫无疑问,离开大家,劳伦斯发疯了,同大家在一起时,他能感染大家的热情和智慧,他是亲爱的宝贝,常常很了不起,但离开大家,他就变得冷漠,阴郁,孤独,当然弗丽达是起因。他已经选择了弗丽达,同真正的人在一起时,他知道这是一种致命的选择,但是同她独处时,他那该死的固执却竭力企图证实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不惜用最卑鄙的手段。
她劝奥特琳嘲笑劳伦斯,而不让他知道自己多么伤心。奥的丈夫和克莱夫?贝尔都给了她同样的劝告,但没起作用。贝尔告诉他妻子,“奥特琳退还了劳伦斯的手稿,还回了一封极其愚蠢的信。尽管我给了她一些很好的建议,菲利普也曾竭力阻止她不要犯傻。我听到她读的每一行都暴露出一个伤口,劳伦斯真要得意了。”
菲利普?莫瑞尔曾冒着断送自己政治生涯的危险在下议院询问过有关查禁《虹》的问题;奥特琳曾尽力筹款帮助劳伦斯同弗丽达团聚,而上述的事件则发生在仅一年之后。莫瑞尔立刻写信给劳伦斯的代理人j。b。平克,警告说如果此书照原样发表,将会被指控为诽谤。据奥特琳回忆,书没有照原样发表,“最糟的部分”作了修改。但可以证实这一点的稿件却没有保留下来。
还没有人意识到杰若德和戈珍是指默里和凯瑟琳,而那个“有学问的50岁的干瘦勋爵”取名乔舒亚?梅尔森,则表明劳伦斯听说了罗素同康斯坦斯?梅尔森的恋情,再根据此事作了窜改(1917年或稍后)。
①即劳伦斯于1920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据专家们考证,小说中的“布雷多利府郾便是以莫瑞尔的家为原型描绘的,女主人公之一赫米恩?罗迪斯也有奥特琳的影子。奥特琳为此而与劳伦斯断绝往来达10年之久。——译注从佳星顿回城后,默里和凯瑟琳准备离开“方舟”,没有出现过争吵。
但是凯瑟琳自从离开法国后,除了圣诞节那个模拟喜剧外,没创作过新作品,现在感到急需找个能写作的处所,而凯因斯的房子则不是这样的地方。
年初她去找过房地产商,没有什么结果,只发现战争开始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租金增加了;寓所更难找,房地产商要求签订三年的租约,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经受那种折磨,“那些我们租下来又退回的所有房子,所有寓所,所有的房间”。因此,她从年初就开始寻找一间工作室,默里也要找几间房,以便写作。人们谣传曼斯菲尔德和默里分手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然而,她此时仍在进行同罗素的心智和感情上的小小冒险。
她给罗素的信与她任何别的信大不相同,它们像漂浮过月亮的云彩——存在着,但不能触及,也不能同其他物质相比,不能否认其中有着热情,有尊敬,也有魅力。布雷特的“野性的呼唤”似乎不是合适的词,为了找出更恰当的词,只有当他俩在餐桌旁谈话时去坐在他们身边——也许彼此有些误会对方的意图。罗素是否知道凯瑟琳手上的戒指是弗丽达婚姻破裂的象征呢?他们谈了很多“真实”。
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凯瑟琳告诉罗素他的信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感到我俩将坦诚相见,彼此没有保留——这将是一种很大的冒险,心情难以平静。”几天以后她告诉他自己在一部电影“身着散步服装的外景”中表演;后来在一间空旷的大摄影棚里,她必须身着制片人称作“奇异的晚礼服”行走,她遇上了这么多荒唐事。她刚刚被一个狡诈的波兰人骗去了一所公寓,“整个事件就像一部道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
在这期间,有天晚上她和默里去霍加斯宅第同吴尔夫夫妇共进晚餐,由她的亲戚西德尼?沃特罗作陪。她可能过多地谈到电影或那个狡诈的波兰人。
一个月以后,吴尔夫告诉她姐姐:“我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她似乎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然而难对付、肆无忌惮的家伙。”吴尔夫大概听到了布卢姆斯伯里的闲谈,由凯因斯和克莱夫?贝尔津津乐道的关于凯瑟琳和罗素的传闻。奥特琳也意识到罗素的感情被吸引开了,但她并不知道转向谁那儿,凯瑟琳也不知道。
一月底,凯瑟琳写了这封信给罗素:
你给我写了如此可爱的信,我亲爱的朋友,好,让我们星期五晚上一起吃饭,如果你来接我,我将一切准备就绪,然后我们将谈话,我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我将在那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很久没见面了——虽然没有见到你,我的“友情”却继续增加,变得越来越深了。
让我们愉快地度过星期五晚上,握你的双手。
罗素把这封信给了康斯坦斯?梅尔森,信的措辞使她确信凯瑟琳同他有恋情。1949年罗素清理文稿时,在凯瑟琳的那些信件旁附了一张便条读到下面这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信时,我吃了一惊,它们给人的感觉是我们有着恋情,或将要有。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退缩了,也许是因为柯尔特①,虽然我从不知道原因。我对她的感情是矛盾的,我深深仰慕她,但她①即梅尔森夫人。——译注那黑暗的仇恨又阻止了我。
。。
曼斯菲尔德传…2
,小,说,网
罗素的自传说在1916年秋天,他“感到自己正同柯尔特有些小小的恋情”——而她收到的他写的充满激情的信却完全推翻了这种说法——关于凯瑟琳他则说:。。正是在此时我才开始了解她。不知道我对她的印象是否正确。。但是当她谈到别人时,她羡慕、阴郁,有着令人不安的洞察力,能发现人们最不愿让别人知道和自己天性中最坏的东西。她恨奥特琳,因为默里不恨她。
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必须克服对奥特琳的感情,因为她不再肯给以足够的回报来让我感到幸福,我听着凯瑟琳所说的于她不利的话,最后却很少去相信它。。。很难知道该相信谁。凯瑟琳唯一称作狡诈的人是那个骗了她一套公寓的波兰人。布雷特说“罗素是个混蛋”,这话的确不错。
2月,凯瑟琳离开了“方舟”,搬入乔奇街1419号的一个工作室,其中有着最大的窗户——我的“上帝俯视我的窗口”——默里在相距半英里的雷德克里夫街47号租了几个房间(j。a。弗格森在那条街上也有一个工作室)。
凯瑟琳从她的“修道院”给奥特琳写了一封信,透露出曾经有过一些尴尬,她有些害怕遇见她,但宽恕了一切。她写给罗素的最后一封信是2月24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学识方面的困难而受到阻碍。他曾寄给她一份自己写的文章,评论“战后世界”,文章结尾说如果不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小学生了解战争的真相,文明人就会在地球上消失。“这是否令人遗憾,我就不想下结论了。”凯瑟琳感到吃惊,读这篇文章,她同他一起攀登到高处,却发现这个过程有些嘲讽意味,“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5个月后,罗素坚持说,作为一张反征兵传单的作者,他应该受监禁,而不是散发传单的人,因此他被传出庭,受到罚款。
在此之前几天凯瑟琳写信给奥特琳,“我为罗素感到非常遗憾,我见过他一回;他对我的工作非常关心,我很高兴同他谈话,他情绪很好。我们没有谈论现在的人和事,而谈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例如奉承和称赞,以及人们写作时实际上要表达什么意思,等等。
罗素写信告诉梅尔森夫人凯瑟琳又见过他,谈论她的作品,似乎急于做他的朋友。但是她接着可能听说了柯尔特(即梅尔森夫人)。
在切尔西的工作室
目前我暂时隐居,只是写了读,读了写——不见任何人,不去任何地方。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给伯特兰?罗素
1917年2月24日
1917年发生的事件①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也改变了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生活。虽然,这种比较的尺度过于悬殊,但两者都包含有毁灭和再生的多重矛盾,却是相似的。
a。j。p。泰勒②从男性的观点出发,在他写的大战史中生动地说明了1917年欧洲变化的实质。泰勒说,“如果拿破仑在1月能复活,他就会发现‘欧洲历史’依然存在:沙皇、国王、皇帝以及自由党政客,强国依然进行着他熟知的同样战争,所有这些拿破仑都能辨认和理解,但在接下来的12月,他就会感到困惑了:那时在欧洲的一端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全新的思想和政府制度;在另一端则是美国,介入的规模将使所有的强国黯然失色。仅在一年之内就产生了现代政治世界。”
然而还发生了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妇女有关的社会变化。对于英格兰的青年男女,战争带来了相反的影响。在战场,机关枪杀害了欧洲年轻人的一半,然而在国内的妇女面前——因为有了机器,而不是鼓吹参政的妇女——却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其中就有埃达?贝克小姐,“上校的女儿”,头戴棉布帽在普特尼的飞机制造厂操作车床。
她写道:“我非常喜爱这儿的工作,奎尼先生对我们极其友好,我在那儿遇见了斯苔拉?德鲁蒙特(即后来的尤丝苔丝?帕西夫人),同她成为好朋友;还有玛丽?汉密尔顿夫人。”如果车床对这两位并不意味着自由,至少对埃达如此,她在汉姆斯特有一位房东,好心的巴特伍什老太太,她每天早晨5点半为埃达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当我回来时,在我能休息和阅读的起居室内有温暖的炉火和晚餐”。这无意中描绘了一幅新权力的画面,过去曾经是男人的特权,现在成千上万的英国妇女在战争中期第一次尝到了滋味。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找到了新的事情做——大声吆喝她所有的乘客;“女商人”吃完午饭后当众点起一支香烟;叫作拉格泰姆的美国舞蹈完全改变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女人该如何摆动四肢的概念;短裙、短发和胸罩——所有这一切都使妇女和青年走向20世纪60年代。
对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17年也是带来创作力增加和不幸消息的一年。在1月,她是拉格泰姆似的知识妇女,充沛的活力吸引了伯特兰?罗素,使维吉尼亚?吴尔夫感到不安。在春天和夏季,她则像显微镜下的生物,从古典的种籽,即那将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