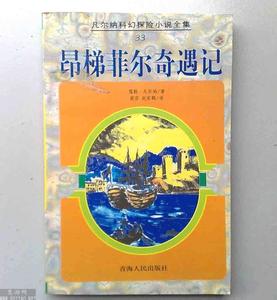曼斯菲尔德传-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际上古德伊尔认识作为作家的凯瑟琳比默里还早,因为奥列加曾将他的一篇文章同她的第一篇来稿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他告诉她“当我第一次在《新时代》上读到《德国公寓》时,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女人还年轻的话,她绝对会有出息。但我肯定她已结了婚,45岁,已至更年期。所以我那时没有写信,也许还是不写的好,因为这不是我的职责。
这以后他们只短短地见过一次面,那时古德伊尔在英国休假。1916年下半年,古德伊尔显然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桩婚事,决定要求上前线,结束这种烦闷的生活,这次轮到他厌世了。
。。。!
第6章1916年,康沃尔…1
小!说
你们很幸福,我非常高兴。只有这样才能幸福———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亲密相爱,不管世上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傻瓜才会去为世人担忧。一个人应该恋爱,感到幸福——这就够了。除非还有一些能使自己更幸福的朋友,那就更好,让我们一起幸福吧。
——d。h。劳伦斯
1916年1月17日
应劳伦斯的盛情邀请,1916年4月初默里夫妇去了泽勒①,接下来的一年凯瑟琳没有写什么自己认为值得保留的东西,没有哪篇故事是在康沃尔度过的那5个月中写的,也没有记日记,以后在伦敦的7个月也几乎搁笔,是否古德伊尔说的真心话使凯瑟琳在这整个阶段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失去了信心呢!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凯尔特康沃尔“布满了巨大的石头”,劳伦斯夫妇表现出来的疏远和烦恼,再加上不停地搬家,虽然每次搬家都有很好的理由。
“凯瑟琳看上去像个移民”,这是弗丽达在她写的书《不是我,而是风》①中说的话。。她讲述了默里夫妇到达时的情景:“他们高高地坐在堆满家具什物的马车上,沿着大路向特雷格森驶来”——这使人们想起了另一位移民亚瑟?比切姆,他的鸡听见打点行李的声音时,就会乖乖地伸出脚来让主人捆绑。
自从1912年默里和凯瑟琳同居以来,他们少说也搬过16次家,而凯瑟琳本人自从1908年来到伦敦,则换过29次通信地址(还不包括她去比利时的旅游或同加纳特?特罗维尔的小住),自从遇见劳伦斯后,受他影响就搬过6回,第7次也近在眼前。也许就默里夫妇和劳伦斯夫妇这么4个时代的产物而言,遗传因素并不重要,但是那些祖先的母鸡确实一直在挠着他们的背脊。
乱七八糟的什物是从呵卡西亚路拿来的,他们在泽勒阶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永远不会喜欢这个地方”,凯瑟琳说),买了一些廉价的旧家具,告诉邮递员把他们的邮件送到劳伦斯那儿,然后开始用涂料和油漆装饰另一所农舍,劳伦斯也热情地做帮手。
上特雷格森由两幢瓦片铺顶的建筑构成,曾经包括5个小小的工人住所。“农舍”在沿海朝东的长房子里,三个住所全部打通,这也就是默里夫妇一年花16英镑租下的。另一建筑里的两所农舍面对大海,一幢空着,劳伦斯夫妇住了另一幢——一间楼上,一间楼下,还有一个长长的贮藏室——一年5英镑。他们共用一个户外厕所,去山上取泉水,上特雷格森的农舍与农庄不同,特雷格森本身离海更近。
在切斯汉,当弗丽达说到劳伦斯像“公狗对待母狗那样占有她”时,当然只是泛泛而谈,但根据《恋爱中的妇女》中“远足”一章来看,也许有所指。不管什么地方不对,默里相信错处全在弗丽达(凯瑟琳有次给杰克写信说“她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胖家伙,劳伦斯真是糊涂了”)。
①康沃尔郡的一个地名,劳伦斯当时住在那里。——泽注①这是弗丽达写的一本有关她自己与劳伦斯结识以来共同生活的回忆录,成书于1934年,知识出版社(沪)据格兰达出版公司1983年本译出,于1991年出版。——译注当时,弗丽达正对奥特琳夫人心怀怨恨,默里夫妇到达的那个星期,弗丽达还写了一封信给她,狂怒地发泄一通,指责她“傲慢无礼”,想同劳伦斯建立“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几天以后,邮递员像往常一样,给了劳伦斯夫妇一些默里夫妇的邮件,有一封信来自佳星顿,显然弗丽达偷偷拆开了信封,或仅仅凭直觉知道其中附寄了她的那封发泄怒火的信,因为过了一小时左右,劳伦斯就直截了当地对默里说,“奥把弗丽达的信寄给了你们”。
在这件事中,劳伦斯完全站在弗丽达一边,费了很长的时间企图说服默里和凯瑟琳,说他们继续做奥特琳的朋友是对他的背叛,所以应该同她“大闹一潮,虽然仅仅为了劳伦斯夫妇的原因,还是最好不要这样,等等。
于是默里试着对奥特琳分析他们的情况,他说劳伦斯现在在许多方面似乎比过去更为年轻,更为幸福,但他为这种幸福付出了代价,而且肯定失去了什么:“我觉得他将来不会再创作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此时劳伦斯已开始重写《恋爱中的妇女》,象征性地描述两对确实与他们4人有些相像的情侣。)至于弗丽达,“我们真的很怕她”,总有一天她会对默里夫妇翻脸。因为她觉得他们威胁到她现在对劳伦斯所占的上风。三年以来他们一直尝试去喜欢她,但她“绝顶庸俗”,使他们望而却步;也许同样的原因使她把矛头对准奥特琳:不再是有钱雇三个仆人的男人的妻子,她觉得自己降低了身份,因而鄙视自己。默里他们一搬进自己的农舍就要开始写作,而目前住在旅馆里,“悬在半空中”。
正在此时邮递员送来了古德伊尔对凯瑟琳的“精神分析”,接下来就是她写作生涯中最长一段时间的辍笔(或自我抑制)。
尽管有弗丽达的愤怒,最初在这邪团体”中还有着愉快的时刻,一月份劳伦斯还称默里是“仅有的几个我信赖的人之一”,现在两人将背着旅行袋高兴地登上去圣?埃维斯山的路程。劳伦斯像一位友好的园丁,让默里觉得他身上有些东西值得发掘,但劳伦斯真正想从杰克那儿得到的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而一旦他有所发觉,就会马上退缩。此时劳伦斯开始谈到兄弟情谊,暗示说他们之间需要一种牢不可破的神圣兄弟关系,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默里马上退缩了,但是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拒绝对劳伦斯意味着什么——虽然《普鲁士军官》可能会使他明白一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说《恋爱中的妇女》里的茹珀特?怕钦就是劳伦斯,或杰若德?克莱奇是默里当然不对,但事实上劳伦斯正坐在农舍里写一本小说,其中有一个男人,像他一样渴望能爱一个女人,却不能够(因为同女人在一起,他觉得或者有过多的姐妹般的爱或只有一种“残暴原始的欲望”),同样是这个人觉得自己受两种男人的吸引——一种肤色白皙,四肢灵活,双眼透出晶莹的蓝色,另一种有着“人们似乎能够投身于其中的漆黑的双眼”,“黑色肌肤,柔软,发出夜的芬芳的男人”,用“笼罩一切的沉重漆黑的双眼”凝视着,这些话出自1968年才第一次发表的《序言》。
后来在小说中,当茹珀特渴望“进一步交往”时,杰若德在那笼罩一切的沉重漆黑的凝视下退缩了,事实上在上特雷格森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形。
与此同时,凯瑟琳感到沮丧,因为“一切似乎都是大石头堆成的”,觉得她波琳别墅的杰克被别人从身边拖走了,而且正被引入歧途,学会了以她觉得非常荒唐的方式看待生活。她给贝阿特丽丝?坎贝尔①写信说,“我绝不会在树上,在流动的小溪中,在石头上看到性,在一切事物中看到性”,但在她的信中没有一丝一毫暗示同性恋,她像默里一样根本就没往这上面想,而且她认为弗丽达该为所有这些“象征”负责。
凯瑟琳觉得他被劳伦斯所吸引,开始感到自己陷入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的情绪之中,而一旦凯瑟琳感到悲伤,默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立刻重新回到她的身边,这对劳伦斯是灾难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常常大发脾气——这与他的疾病有关——而现在就更是频频发作了。
最糟糕的一次——默里对其令人厌恶的细节缄口不言——发生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凯瑟琳告诉柯特她目前同弗丽达己不说话,与劳伦斯也极为疏远,完全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他俩之间的情景,她不知道哪种情形更使她恶心——他们相爱,互相嘻戏,还是他们高声叫嚷,劳伦斯扯着弗丽达的头发,说“我要割断你的喉咙,你这婊子。”他的身体再也健康不起来了,任何一件事,如果有人意见与他不同,他就暴跳如雷,直至精疲力尽,站立不稳,非得躺到床上去不可。只要有争议,他就说因为你性生活不对,精神卑劣。
凯瑟琳说“目前他真有些偏执狂”,因为弗丽达让他够受的。
5月5日是星期五,凯瑟琳去他们那儿喝茶,非常不巧,提到了雪莱,弗丽达说“我认为他的《云雀》是一派胡言”,劳伦斯说道,“你这样说不过是想炫耀一下,雪莱的诗你只知道这首。”于是弗丽达说“我真受够了,滚出去,你这万能的上帝,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你到底闭不闭嘴!”劳伦斯说,“我要给你一巴掌让你住嘴,你这臭女人”等等。凯瑟琳逃了,一口气跑回家。
那天晚上劳伦斯来同凯瑟琳和默里一起吃饭,但是弗丽达不肯过来。劳伦斯说,“如果她敢靠近这张桌子,我要割断她的喉咙”。晚饭后弗丽达来了,在屋外的夜色中来回走着。劳伦斯突然猛地朝她奔过去,他们开始尖叫撕打,他打她的头,脸,胸脯,扯她的头发,而她大声向杰克求救,“保护我,救救我!”然后他们冲进默里的厨房,绕着桌子跑着——劳伦斯气得脸色发青,退后一步,挥手上前,“给了这个大胖女人一掌”(凯瑟琳告诉奥特琳),“然我为劳伦斯感至非常遗憾,却一点也不同情弗丽达,后来默里告诉我他也有同感——他根本不觉得是一个女人在挨打。”
然后劳伦斯倒在一张椅子中,弗丽达倒在另一张上,没有人说一句话,“除了弗丽达的抽泣声和吸鼻子声外,屋内一片沉寂”。劳伦斯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坐在那儿盯着地板,咬着指甲,很久以后才抬起头来,问了默里一个有关法国文学的问题,默里回答了,三个人渐渐地坐到桌子边上来,弗丽达给自己倒了一些咖啡,半小时以后他们几乎和好了,开始“同时记起他们曾经吃过的一种非常好吃味浓的,但价格昂贵的通心粉奶酪”。
第二天弗丽达躺在床上,劳伦斯把饭给她端上楼去,并且开始为她的帽子缝花边,到了下午,她唱了起来(“故意地”),劳伦斯也加入齐唱,挨了一顿打后,她似乎精神好起来,好像对此感到津津有味,因为她开始为自己做衣服,在头发上插花,用小女孩的嗲声嗲气同劳伦斯说话,“这使默里和我目瞪口呆,十分厌恶——尤其是感到厌恶!”
①戈登?坎贝尔的妻子,坎贝尔本人1915~1918年任英国军需部助理审计官,他与劳伦斯、凯瑟琳等人都有较密切的来往。——译注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他身上那个两人都曾经爱过的“亲爱的人”隐藏起来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就像一只小小的金戒指埋藏在弗丽达这个庞大的德国圣诞布丁中,食欲最旺盛的人也不能吃尽弗丽达找到他,只好一旁等待着有人拿刀来把她切成碎片,那时他才能重见天日,重新闪光。
但是他自己并不想发生这种事。”
在默里和凯瑟琳所有的信件中,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劳伦斯不好,只有对他的同情和遗憾。默里夫妇开始另找住处,这两对夫妇各自躲进自己的小屋,各自庆幸自己的爱情与另一对不同,各自都使用了“厌恶”这个词,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种狭隘火热的亲昵令人厌恶,这些结了婚的人,关上房门,把自己囚闭于这种不与外界交往的结合之中,虽然是爱情,也使他感到厌恶”。
就这样戈珍①和杰若德被描写为走向毁灭,而至于他们的原型,事实要简单得多,也更近人情。杰克和凯瑟琳那时只是彼此相爱,就像人们有时做的一样,不想让人打扰,但是那时恰好在写《恋爱中的妇女》的人却觉得厌恶,恶心。
虽然人们一般认为戈珍和杰若德是凯瑟琳和默里的写照,他们自己在此书发表时,却不这样认为。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故事情节(戈珍离开杰若德去找莱尔柯)出自柯尔斯伯里那场戏(凯瑟琳为了格特勒离开默里),而非出自他们的真实生活,只有开始的几段话劳伦斯写时似乎心里想到了凯瑟琳:“戈珍是一位雕塑家,爱好小事情,喜欢带着不动声色的好奇心观察人们,表现他们的真实面目,使他们固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