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因要从结果中寻求之时,就是每逢我们从一事物探求该事物是否存在,或它是什么……此外,因为当人们向我们提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够立即看出它的存在属于什么性质,也看不出是需要从词句去寻求事物呢,还是需要从结果去寻找原因,等等。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些特殊点再予赘述是绝对徒劳无益的。事实上,要解决任何困难,如果全面有秩序地进行,那就比较少费时间,也比较方便。因此,对于任何给予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努力清楚理解所寻求的是什么。
事实上,经常有不少人慌慌忙忙探求人家所提的问题,甚至来不及注意所探求的事物万一呈现,要根据怎样的标记才可以把它们识别出来,就以昏乱的心智 着手去解决;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愚蠢不亚于这样的小厮:他的主人打发他去什么地方,他连忙遵命,慌慌忙忙跑去,甚至来不及听完吩咐,也不知道命令他到哪里去。其实,在任何问题上,尽管总有点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否则,寻求就是无谓的了。然而,应该说,即使这也是被某些确定的条件指示了的,这样我们才得以确实下决心去寻求某一,而不是任何其它。这些条件具有的性质使我们说,必须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它们,就是说,把心灵的目光转向这些条件,清清楚楚逐一直观,细心探求每一条件怎样限制着我们所寻求的那个未知项,因为,人的心灵在这方面通常有两种错误:或者超过了为确定问题而已知的规定,或者相反有所遗漏。
应该好好注意,前提不要规定得过多、过死。这主要是指谜语和其它为了难倒智士而巧妙设计出来的询问;不过也指其它问题,只要我们觉得,人们为了获得解答而规定了某种大致上确定的前提,哪怕是我们相信这种前提不是由于某种确定的理由,而只是由于一种习俗定见。例如斯芬克斯的谜语,我们不要认为,“脚”这个名词仅仅指动物真正的脚而言,还应该看看它有无可能涉及其它事物,比方说,幼儿的手和老人的拐杖,因为他们使用手和拐杖,大体上跟使用脚一样,用来行走。同样,对于渔夫的谜语,应该不要让鱼这个观念盘据我们的头脑,使我们不去认识那种动物,即穷人尽管不情愿也只好带在身上,他们捉住之后就扔掉的那种动物。还有,要是有人问怎样制造一种瓶子,就是我们有时见过的那种,里面立一根柱子,柱顶是唐塔路斯喝水的姿态,把水注入瓶中,只要水没有升到进入唐塔路斯嘴里的高度,瓶中的水就完全盛得住。但是,水只要一涨到这不幸人的唇边,就忽然一下子跑光了。乍看起来,全部奥妙很像是如何塑造那个唐塔路斯形象,其实这丝毫也不解决问题,只是随着问题而存在罢了,因为困难全在于:设法把瓶子造成这样,使得水一达到某种高度就漏掉,而在此以前却涓滴不漏。最后,要是有人问我们,根据我们关于星体的观测,对于它们的运动可以肯定些什么,那我们就不应该同意这样一种没有道理的见解,即地不动而且位于世界的中心,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从小就觉得仿佛正是这样。我们应该对此置疑,留待以后去研究,看看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什么确切的判断。诸如此类。
不过,我们犯错误,往往是由于疏忽在确定问题所必需的条件明显存在,或者理应以某种方式不言而喻的时候,我们却不予考虑。比方说,要是有人问到永动是否可能,不是例如星体或泉水那样自然永动,而是人工制造的永动,要是有人像以往不少人相信的那样,以为这是可能实现的,既然大地以它的轴为中心永无终结地作圆周运动,而磁石保有大地的一切属性,因而认为自己即将发现永动,只要他把一块磁石安排得使它成圆周运动,或者至少使它把它的运动和其它特点传导给铁;然而,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他也不能用工艺方法制造出永动,只是利用了自然的永动,完全有如把一个轮盘安置在河川中,使它永远旋转。这样做的人其实是忽略了确定问题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如此等等。
充分理解了问题之后,应该看一看困难究竟在哪里,以便把它从一切其它中抽象出来,求得较容易的解决。仅仅领悟问题,并不总是足以认识其中困难之所在,还必须加以思考,弄清楚其中所需的每一事物,使我们可以在某些较易发现者呈现时把它们略去,从所提问题中取消掉,使得剩下的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例如前述的那个瓶子,当然我很容易发现该怎样制作这种瓶子:得在瓶子中间竖一根柱子,上面画一只鸟,等等。把那些对解决问题毫无用处的事物一旦撇开,那就只剩下光秃秃的这样一个困难了:原来装在瓶子里的水在达到某种高度之后必须全部漏光。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就是我们应该寻求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说,值得花力气的只是:有秩序地通观所提问题中已知一切(因素),去掉我们明显看出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的,保留必需的,对尚有疑问的更细心地加以研究。
二、指导心灵的规则(4)
/小。说+
原则十四
还应该把这个(问题)转至物体的真正广延(上去考虑),并把它通盘提供给想象借助f于单纯形象(去观察),因为,这样一来,悟性才可以更加清楚得多地知觉它。要借助于想象,必须注意的是:每逢我们从某个原来已知项中演绎出一个未知项的时候,并不是因而就发现了某种新的存在物,只是把整个有关的认识扩展了,使我们得以看出所寻求的事物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命题中已知事物的性质的。例如,设有一人生而盲目,我们就不应该指望依靠任何说理的办法,使他知觉真正的颜色意念,恰如我们从感觉中获知的那样。但是,假如另有一人至少有时见过基本色,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中间色和混合色。那么他就有可能自己设想中间色和混合色是什么样子,尽管他没有见过,却可以使用某种演绎,按照与其它颜色的相似去设想。同样,假如在磁石中有某种存在物,我们的悟性并未见过相似者,我们就不应该希望多少有点可能通过推理去认识该物;因为,要能这样,我们必须或者具备某种新的感官,或者禀赋着一种神圣心灵;然而,人类心灵在此问题上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能够做到的,既然产生与这种磁石相同效应的混合物或已知物的混合,已为我们十分清楚地觉知。
诸如广延、形象、运动这类已知存在物,这里不及一一列举。凡此种种虽存在于不同主体中,它们之被获知却都是通过同一意念:一顶王冠,无论是银子做的,还是金子做的,我们想象其形象都不会不同,这种共同意念从一主体转移至另一主体,不会以其它方式,只会通过单纯比较,我们就是用这种比较来肯定所询问的事物与某一既定项构成什么关系:相似或对应或相等的关系。因此,在任何推理中我们准确辨认真理只是通过比较。例如这一推理:凡a皆为b,凡b皆为c,因而凡a皆为c,我们就是把所求和既定,即a和c,按照二者皆为b的关系来加以比较的,等等。但是,前面已多次提醒,三段论各种形式对于知觉事物真理毫无助益。既然如此,读者最好是把它们统统抛弃,然后设想:绝对而言,凡不能凭借对单一事物的单纯直观而获得的认识,都是通过两个或多个项互相比较而获得的。当然,人类理性的奋勉努力几乎全在于为进行这一比较作准备,因为只要这种比较是公开的、完全单纯的,就不需要人工技巧的任何协助,只需借助于天然光芒,就可以直观这一光芒所获知的真理。
必须注意,所谓简单而公开的比较只指这样的场合:所求和已知共具某一性质;至于其它一切比较,则不需要任何准备,除非是由于这种共性并不同样存在于所求和已知之中,而是始终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某些其它对比关系或比例之中;人的奋勉努力主要不是用于别处,只是用于归结这些比例,使我们得以清清楚楚看出所求和某种已知是相等的。最后还要注意,归结为这种相等关系的只能是可以容纳最大和最小可能的事物,我们把一切这类事物用量这个词来概括,因此,在按照前一条原则从任何问题中把困难各项抽象出来以后,我们就不要考虑其它,而应该仅仅以一般量为考察对象。
不过,为使我们在这样的时刻还想象某个事物,而且不是运用纯悟性,而是运用幻想中描绘的形象所协助的那种悟性,还要注意的是:一般量,要是不特别与任何一种形象相关联,就谈不上什么一般量。由此可见,如果把我们所理解堪称一般量的事物,转化为可以在我们想象中最容易最清晰加以描绘的那种量,我们将获益匪浅。那就是物体的真正广延,它是存在为形象的,除形象外抽象掉了其它一切。从原则十二中引申出来的结论正是如此,既然在那一原则中我们设想,幻想本身连同其中存在的意念,无非是真正有广延的、存在为形象的真实物体。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以任何其它主体都不能使人更清楚地看出各种比例之间的一切区别,那么,虽然可以说一事物比另一事物白或不白,这个声音比那个声音尖或不尖,等等,我们却无法确定两者究竟是相差一倍、两倍……除非与存在为形象的物体之广延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完全确定的问题几乎不包含任何其它困难,只有一个困难,就是如何把比例发展为相等关系;凡是恰恰存在这种困难的事物,都可以而且应该容易地同任何其它主体相区别,然后把它转移为广延和形象。为此,直至原则二十五之前,我们将仅仅论述广延和形象,而略去其它一切考虑。
我们愿意希望有哪位读者喜欢研究算术和几何,虽然我宁愿他还没有涉猎过此道,不要像一般人那样所谓已经精通,因为,运用我在这里将叙述的各条原则,就完全足以学会这两门学科,比学习任何其它问题要容易得多。这种运用用处极大,可以使我们达到高度的智慧。因此,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指出:前人从未借助于数学问题(的研究)而发现我们的方法的这一部分,然而,我要说,现在的人学习数学几乎正是应该为了发扬这部分方法。对这两门学科,我要假定的不是别的,也许只不过是某些不言而喻的、大家有目共睹的(因素);然而,一般人对于这些因素的认识,即使没有被任何错误公然败坏,却由于若干不太正确的、构想不妥当的原则而模糊含混,下面我们尽力逐步予以纠正。我们所说的广延,指的是具有长、宽、深的一切,不问它是实在物体,还只是一个空间,也似乎无需作更多的解释,既然我们的想象所能觉察的最容易莫过于此。然而,正因为饱学之士往往剖微析缕,以至自发的(理性)光芒消散,甚至在农民也绝不是不懂的事物中也发现了晦暗模糊之处。我们必须提醒他们,这里所说的广延,并不是指任何有别于、孤立于其主体的什么东西。一般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这类哲学存在物不属于想象所及的范围。因为,即使曾经有人相信,例如,自然界中具有广延性的一切都可归结为乌有。他也不可能排斥广延本身是确实存在的,尽管这样,他还是不会使用具有形体的意念来构想广延的,而只会使用会作出错误判断的悟性,这是他自己也会承认的。如果他仔细思考他那时将竭力在幻想中构造的那种广延形象本身,事实上,他将注意到,他对它的知觉并不脱离任何主体,他对它的想象却不同于他的判断。因此,无论悟性对于事物真理如何设想,这些抽象物在幻想中的形成绝不会脱离它们的主体。
但是,今后我们的论述将无一不依靠想象的协助,既然如此,值得我们慎重区别应该通过怎样的意念来向悟性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词义。因此,我们提请考虑以下三种说法:广延占据空间,物体有广延,广延不是物体。
第一种说法表明:人们以为广延就是有广延性之物,因为,如果我说广延占据空间,这同我说有广延性者占据空间,心目中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如要避免模棱两可,使用有广延性的说法并不较好,因为它没有足够明确地表示出我们心目中的想法,即,某一主体由于有广延性而占据某一空间;会有人把有广延者即是占据某一空间的主体,仅仅理解为我说的是有生命者占据某一空间。这个理由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说:下面论述的是广延,而不是有广延性者,虽然我们认为对广延的想法应该同有广延性者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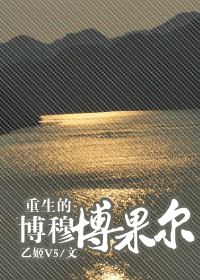
![[基尔·布雷切夫_孙维梓] 必](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