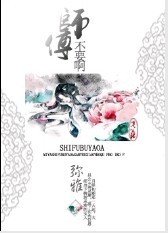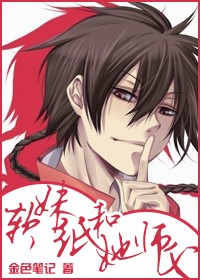师父,床上请-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布巾反复擦拭应笑的胸、背、两腋及双臂。
柳应笑被药粉的气味呛得直咳嗽,捂住鼻子问道:“师父,这是什么?苦极了。”
方泽芹道:“这是云花散,以桑叶桑枝、竹皮苦草等药材研磨调制而成,有温通气血的功效,为师替你擦一擦,肚里的气一散便不会觉得胸闷了。”
柳应笑道:“娘也在水盆里放过药草,闻着很香,一点儿也不苦呀。”
方泽芹道:“俗语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便是指好药往往味苦难咽,但治疗疾病收效显著,为师这云花散正对应笑气郁之症,苦些无妨。”他惯于贱药活用,在乡间行医,那些香气上乘却疗效甚微的昂贵药材是能不用则不用。
柳应笑听师父说有好处,便放开手又闻了闻,“啾”的打个喷嚏,她连忙团身缩入热水里,两手在身前来回摆荡,把水拨得哗哗作响,眯眼笑道:“嗯!不难闻,我在下雨天也能闻到药田里的苦味,虽然苦,闻着却很舒服,师父,我喜欢苦苦的草药味。”
方泽芹开怀畅笑,解开她的头发轻缓擦洗,满头乌发长而浓密,托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大把,洗净之后,方泽芹将湿发拧去水,扭成一缕缠绕在应笑的额头上,连缠三圈,再把余下的发梢塞进三圈发辫中,谁想刚一松手,发辫就滑脱下来,他只得拿个花瓷盆兜住长发,运气将掌心催热,由发根至发丝来回搓揉数遍,待擦得半干之后便用干布连肩带脚地将应笑裹起来,直接抱上床。
方泽芹系上翠雀裹肚,又穿起细布裆裤、白绢衬衣,照料得细致入微,没有一处疏漏,这也亏得他常年在外游荡,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自行打理妥当,若非如此又怎能照顾病患?
柳应笑道:“师父对徒弟真好,我娘时常让我自个儿洗澡,穿衣裳时还得把手背在后面系带子,每回都得系上许久,有时系上了便解不开,可急人啦。”说到此时又垂下眼眸,把两手十指扭结在一块儿,闷闷道:“我娘呢,时而对我好,时而不好,常会突然发起脾气,也不知是哪儿做错了……我不敢烦她,若是心情好时,她也会像师父这般待我,阿娘……总说我惹她烦心,所以不愿见我了么?”
方泽芹将湿袍子脱掉,坐在床头,把柳应笑搂在怀中,拍着她的肩膀道:“大人时常口不对心,若她不在乎你又怎会说烦心呢?”
柳应笑道:“可是她总将我独个儿丢在井下,向天说他娘常陪着他睡。”
方泽芹略一思忖,即道:“这是不得已,应笑生来便有气虚症,入夜后外寒而内燥,体内津液不足,不利于阴阳互生,是而以井下湿热之气调理阴亏寒燥之证,你娘虽从未对你言明,从这番用心里却不难看出她是何等重视你。”
柳应笑嘴角微翘,问道:“真的?”
方泽芹只是七分猜测三分推断,若在平日里,但凡有一分存疑也绝不把话说满,这时见小徒弟眼里有期许之意,竟毫不犹疑地颔首道:“你娘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不关心你又能关心谁呢?很多人总习惯于将关怀放在心里不说出来,面上严厉也是为了让孩子能乖巧听话,常言道棍棒底下出孝儿,不打不成器,打骂亦是一种关怀与寄望,应笑要学会分辨何为善意的严教,何为恶意的伤害,明白么?”
柳应笑皱起眉头想了会儿,似是一知半解地点头应声,又问道:“那师父会不会打徒弟?”
方泽芹更是没有半分迟疑:“别家师父许是会,但为师绝不打骂你。”
柳应笑双眼一亮,随即又绷起了脸:“做错事了也不打骂吗?”
方泽芹笑着道:“不打也不骂,只罚你帮为师捏肩捶背。”
柳应笑爬到方泽芹身上,双手各搭在他左右肩头使力捏了捏,嘟着嘴道:“师父,捏不动呀,硬得像铁锅底。”一面说一面又频频打哈欠。
方泽芹哈哈一笑,抱起她塞进被子里,靠在床头拍哄,讲上一两个轻松愉快的小故事助她安眠。柳应笑连日赶路,早已疲倦不堪,眨了两下眼便打起小呼噜来。
方泽芹拉开竹屏置于床头,待应笑睡熟了之后便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又走到水桶前,两臂环抱桶身,往上一拔,瞬即收手往桶底一抄,便将这百来斤的大水桶稳当当托于掌心。
他将水桶搬出屋外才到隔间请仆从出来收拾,接着又去后槽井里打水擦身,回房后也不上床,拖个蒲团在屋角打坐调息,半个时辰后再去床前观察小徒弟的睡眠情况,见她还似在井底睡觉时那般把身体蜷缩成团,一双小手握成拳头缩在胸口。
方泽芹端详许久,一股怜惜之情油然而升,他当即脱了鞋袜上床,将应笑拥入怀中,轻柔拍抚她的背部。柳应笑迷糊睁眼,抬头见是师父,便伸手抓住他的前襟,把头脸贴靠在他的胸膛上,嘴里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呓语之后又沉沉睡去,姿势稍有舒展,不再像之前那般拘谨。
☆、偿命01
次日清晨,应笑醒得早,方泽芹将衫裙鞋袜逐一为她穿上,皆是青花素布,唯独绣鞋是鹅黄嫩色,鞋面上托着两团绒线攒成的花球,衬得一双小脚更是玲珑可爱。
洗漱已毕,便有庄客前来相请,将师徒二人领入后园,魏进在门下迎接,叙礼罢,引至座上,让方泽芹带着徒弟坐了主位,魏进对席相伴,吩咐庄客铺上糕粥面食,陪着吃了,收拾碗碟后又沏上一壶香茶,亲自替方泽芹斟上满杯,双手捧递上前,说道:“魏某有一事相求。”
方泽芹连忙起身接盏,还礼道:“我师徒二人多承庄主厚待,有何为难之事只需说一声,方某自当尽力。”
魏进叹口气,道:“不瞒先生,老母病有半年,寻医数诊无用,诸医见病症危重,恐治不好有损名声,皆不愿接手,听闻先生正在巡医途中,昨晚见你师徒二人鞍马劳顿,实不敢烦扰,不知可否劳烦先生再为老母诊一诊,若真无可挽回……唉,也就罢了。”
方泽芹二话不说,手往前一摆:“带路!”
魏进将方泽芹引至偏房,推开门,门后挂着两层絮了棉花的帐幔,掀帐而入,一股闷热之气逼面而来,在这温暖的初夏,不开门窗通风也就罢了,卧榻被重重帷帐掩盖得密不透风,床前竟然还摆着一个火盆。
魏进的夫人李氏正坐在一旁摇蒲扇,只热得汗水淋漓,额前头发全湿了,一缕缕贴在面颊上,她见丈夫进门,忙起身相迎。
魏进问道:“老太太如何?”
李氏摇头叹气,回道:“仍是老样子,怕冷,直打寒噤,又叫我给她加床棉被,睡了有半个时辰,醒着也犯糊涂。”
魏进将方泽芹师徒让到身前,对妻子道:“这是方大夫,特来为老太太诊治。”
李氏连忙叉手行礼,方泽芹回了礼,疾步走到床前,李氏将帷帐掀起,床上躺着一名黑瘦老妇,面容枯槁、嘴唇干裂,魏进说老母今年刚过六旬,这般看来倒似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
方泽芹问及症状时,李氏拾起衣袖拭泪,低声道:“老太太只说咽喉疼痛,饮水时疼,饭菜更是吃不进去,最是怕冷,坐起身来便喊头疼,近来连话也不会说了,晕一时醒一时,只能勉强喝些药汤。”
方泽芹见桌案上压着数张方子,抄起来大略翻看一遍,上面都是人参、麦冬、桂枝和生姜等温热补元的药物。
魏进道:“年前请来的大夫还肯医这病,说老太太是患了伤寒,需用温燥的药将体内寒邪驱出去,吃了药后,病没见好,反倒愈发严重,后来的大夫说久病损元气,又开了滋补的药,唉……仍是没用,这往后再请大夫,都只是摇头,谁也不敢医了。”
方泽芹掀开被子一角,为老妇诊脉,脉象就跟水里的鱼似的,头定尾摇、若隐若现,这是阳气外脱的重症。
方泽芹道:“令堂脉象虚弱,是危急之症,据脉象恐难入手……”
这推托之辞魏进是听得太多了,见方泽芹面色沉重,心下一沉,暗自哀叹道:罢了罢了,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又岂能指望一个摇铃的野医。
却听他紧接着又说:“方某定当竭力而为,若庄主信得过我便速取纸墨来。”
魏进惊喜交加,忙叫夫人取来笔墨纸砚,方泽芹提笔开下方子:生石膏、竹叶、天竹黄和枇杷叶等,全是清热化痰的药。
魏进虽然不懂医,但这一年来听大夫讲得多了,耳濡目染,自是有些常识,方泽芹开的方子与其他大夫下的方恰恰相反,尤其这生石膏乃是极为寒凉的药,老太太患了伤寒,正全身发冷,本该用温药补虚,哪还能凉上加凉。
他也不好意思直接提出来,只委婉地道:“先生,你看老母亲还在发冷,病得久了元气大伤,是不是先开些补方再着手医治?”
方泽芹也不跟他客气,直言道:“这补药再下,方某可是半分也入不了手!病患是个虚寒实热的症状,看似阳虚,实则热邪内淤,之所以发冷,恰恰是因热气阻滞气血运行,这证若在发病初期对症下药,一剂凉汤便能痊愈,却被误用了温燥的药,由而滋生痰饮,若再补,便要把这最后一线生机给断绝了。”
魏进也是个有见识的人,这么一听便了悟了,原来老母亲不是病重难治,而是叫人给治坏了,赶忙令庄客去县里按方抓药,煎了一碗竹叶石膏汤给老太太服下,第一副药下去未见起色。魏进不放心,便对方泽芹道:“先生若无急事,请在庄上多歇宿几日,万一病情有变也好及时照应。”
方泽芹道:“方某正有此打算,多有叨扰了。”又吩咐移走火盆,敞开门窗透气,帷帐被褥只留一层遮风。
魏进一一照办,连声称谢,这才确信方泽芹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诚心要治这个病,待他更是热络殷勤。
把魏母的事忙定后,方泽芹便领着柳应笑回到客房,刚往桌前一坐,应笑便跑到药箱前打开屉子,拿出笔墨纸砚摆放上桌,又去瓮里舀来清水润笔,站在凳子上提袖研墨。
方泽芹起身走到她身后,轻声问道:“应笑想写什么?”
柳应笑将墨条在砚上敲三下,以油纸包好装入匣中,跳下凳子,仰头看向方泽芹,说道:“不是应笑想写,是师父要记下那老婆婆的病,每次替人开了方子之后不都是要记下来的吗?”
方泽芹微一愣,不免有些诧异,他虽然对外说应笑是徒弟,实则是将她当作亲人般对待,平日里只是如长辈对晚辈那般教养疼爱,从不使唤她干活,没想到不等人教,她倒自己学着做起跟班的差事来。
方泽芹见应笑忙得勤快,便问她:“应笑可厌烦抄书写字?”
柳应笑回道:“不烦,可喜欢了。”
方泽芹问道:“那应笑可愿代为师记下那婆婆的病?”
柳应笑迟疑了会儿,小声说:“会写错。”
方泽芹摸摸她的头,笑道:“不妨,为师念一句你记一句,写错也不要紧,划去再抄便是。”
应笑这才又站回凳子上,提笔蘸墨,方泽芹便站在她身边,伸指轻点纸页右侧,说道:“先在此处写上——舒州魏母痰饮为患误断为伤寒。”
柳应笑跟着念了一遍,提笔认真记下,写好之后抬头望向师父,方泽芹微微一笑,夸赞道:“好,一字不差,应笑真是聪明的乖孩子。”这番褒奖的本意是为了鼓励柳应笑,说出来之后,柳应笑的反应平平,方泽芹自己倒颇感欣慰自豪。
柳应笑悬笔于纸上,见方泽芹笑着不说话,忍不住催问:“下面该写什么?”
方泽芹念道:“魏母年逾六十,鱼翔脉,唇肿咽痛,难出语言,畏寒体虚……”
柳应笑书写流畅,待他念完也全都记妥了,俯身轻吹纸面,又来回审视三番,拎起纸页展在方泽芹面前,问道:“师父,你看看,可有写错?”
方泽芹早在她写字时便检查过了,却仍是慎重地捧起纸张仔细查看,“嗯”了一声,舒展笑颜道:“一字未错,应笑可真厉害,你知道这些字作何解?”
柳应笑道:“这不是老婆婆的病症么?师父说过,人若有病,身体会产生与寻常不同的变化,这些表现出来的变化即为症,婆婆的症便是唇肿咽痛,畏寒体虚。”
方泽芹从没特意教授医术,听她能对答如流,着实感到讶异,又问:“那应笑可知引发这些病症的原因?”
柳应笑低头想了许久,像背书似的说道:“病患是个虚寒实热的症状,看似阳虚,实则热邪内淤,之所以发冷,恰恰是因热气阻滞气血运行。”停会儿,又加了句,“是师父方才说过的,还说有痰饮,可我不知道痰饮是什么。”
方泽芹愣了半晌,高高举起柳应笑往上颠了颠,横臂兜住她的腿弯,笑叹:“应笑,你若是个男娃,名扬天下亦非难事啊,有这好记性、好悟性,将来考上状元也大有可能。”
柳应笑心直口快地问:“那女娃就不能名扬天下考状元了吗……咦,状元是什么?”
方泽芹端量她玉琢般的雪白脸蛋,半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