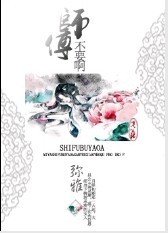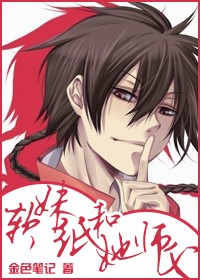师父,床上请-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泽芹道:“应笑,棺里便是你娘。”
柳应笑愣了一愣,趴在棺前看了会儿,叫唤道:“呀……呀!”伸出手,停在空中悬了片刻,似是有些胆怯,但终于还是轻轻拍上麻布,放大声音叫喊,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到最后带上了哭腔。
曹村长与两名庄客看得不忍,不禁垂头叹气。诵经的老僧提醒道:“时辰就快到了。”
方泽芹蹲在应笑身边,揽住她的肩膀,轻声道:“应笑,要盖棺了。”
柳应笑拼命甩头,伸手在麻布上轻推,用劲拍打棺木边缘。老僧用平淡的声音下令:“时辰到,盖棺入土。”
两名庄客走上前,手往棺盖上一搭,柳应笑惊慌起身,倾身趴在棺口,对着庄客摆摆手,又乞怜地看向方泽芹,哀求道:“呀!啊……”
方泽芹狠下心肠告诉她:“应笑,你娘不会醒了,她已经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明白么?”
柳应笑呆了一呆,伸手就想去掀麻布,方泽芹一把抱住她,强行把她从棺材上剥下来,曹村长大喝一声:“盖棺!”
两名庄客立刻推上棺盖,扎桩结绳,将毛竹杆插入绳结里,一人扛一头,将棺材挑起来放入坑里,曹村长把竹片、木篓、陶罐等器物填塞在坟坑与棺材的缝隙之间,下铺锦被上盖草席,诸事办妥后便叫庄客铲土掩埋。
眼见那一钵一钵的土被洒在草席上,应笑心里疼痛,忍不住放声大哭,只觉得胸口被一股气撑得发涨,这气逐渐升至咽喉,似被尖锐的硬物梗住般灼烫刺痛,她张大了嘴,那尖锐的硬物忽而化作一团热气冲开喉咙,心里的话就跟着热气被呐喊了出来:“娘!娘——!!不要睡!不要睡!我听话了,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听话了,你别生气!”
方泽芹一惊,不由得悲喜交加,激动之余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乱不择言地安抚道:“应笑,乖,好孩子,你娘没生你的气,她知道应笑是好孩子,不哭不哭。”
柳应笑挣开方泽芹的手,跌跌撞撞地跑到坑前跪下,抹着眼泪用力地磕头,哭道:“娘,我不骗你,我天天陪你,哪儿也不去,娘,你起来打我,你起来打我啊!”
方泽芹见她额上的麻布渗出血来,连忙上前制止,两手按住她的肩膀沉喝一声:“应笑!”
柳应笑被他的喝声惊得浑身一震,双手握成拳缩在胸前,就这么僵住了,泪水欲掉不掉地在夹在眼眶里。方泽芹心口猛然一抽,伸手抚上她磕破的额头,叹息道:“应笑,你娘累了,让她好好睡吧。”
柳应笑抽噎着小声问:“娘走了?”
方泽芹轻“嗯”声,她又问:“不要我了?”
方泽芹摇头,指尖抹去她的泪珠,柔声道:“你娘怎会不要你呢,她只是太累了,应笑,她会在别的地方看着你,守着你。”
柳应笑垂下眼眸,含糊低问:“娘……会回来吗?”
方泽芹轻轻摇头,应笑瘪起嘴:“见不到了吗?”
方泽芹沉默片刻,摸摸她的头,颔首道:“见不到了,再也见不到她了。”
柳应笑表情未变,双眼越张越大,瞪到极限时,那泪珠子就一颗接着一颗地往下掉,她张了张嘴,突然“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就像寻常孩子那样嚎啕大哭,从掩土一直哭到成坟,把嗓子也给叫哑了,最后抽泣着窝在方泽芹怀里沉沉睡去。
曹村长担心地问:“没事吧?唉!我就说该瞒着她。”
方泽芹道:“无碍,能哭出来是好事,这种剧烈的情感冲击对应笑来说不全然是害。”他认为应笑说不了话与柳元春的严苛对待无不关系,如今能破开这道关卡,倒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小孩子的恢复力很强,只要能给她足够的关怀,很快便能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出来。
立碑之后,一行人回转曹庄,柳应笑像被抽了魂似的抱膝坐在床上不言不语。曹村长又提起要将她过继与史老儿的事,应笑闻言不由自主地咬紧下唇,把脸埋在两腿间。
方泽芹坐过去,抚摸她的头发,低声问道:“应笑愿不愿意做史家爷爷的孙女儿?”
柳应笑咕哝了声,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方泽芹又问:“你想当史家爷爷的孙女儿,还是想当我的徒儿?”
柳应笑抬头看他,眨了眨眼,问道:“不一样?”
方泽芹道:“不一样,当我的徒儿便不去史家。”
柳应笑眼神一闪,随即又黯淡下来,闷声道:“你会走。”
方泽芹轻道:“我会走,我会带你一起走。”
曹村长一愣,说道:“方大夫,请恕曹某直言,你长年在外行医,居无定所,带个孩子在身边恐怕不太方便,史老儿虽非权贵,丰衣足食却不在话下。”
柳应笑抓住方泽芹的衣袖,眼巴巴地望着他,方泽芹哂然一笑,道:“曹村长说得在理,留在史爷爷家能吃饱穿暖,不用四处奔波受累,若是跟我走,少不了要餐风露宿,吃许多辛苦,应笑,你……”
话未说完,柳应笑便一头扑进方泽芹怀中,两手紧紧抓住他的前襟,将额头用力抵在他的胸膛上。方泽芹竟有些受宠若惊之感,不觉暗笑自己年岁未足心却早衰,居然有了当爹的心态。
曹村长见柳应笑这般依赖方泽芹,自然也没话说了。
方泽芹陪应笑守过七七四十九日,离村时已至初夏,曹村长让庄客牵了马来,将细软银两一担挑了,徐氏夫人收拾了数件儿时穿的旧衫裙,打个包裹,与料袋皮囊全拴在马上。一行人围聚村口依依惜别。李春花忍着心疼,用积攒数年的铜钱买了副“银缕朱结锁”送给柳应笑,说道:“小哑巴,我没什么好的能送,听人说这朱结锁能锁命,戴上之后能无灾无祸保平安,你身子弱,给我好好戴着,千万别弄丢了。”便将朱结锁挂在应笑的脖子上。
柳应笑身上只有两样物事,一样方泽芹给她的干姜块,另一样是自幼不离身的铜制佩饰,她没多犹豫,将佩饰摘下递给李春花。方泽芹见了之后微一怔,对应笑道:“可否先让为师一观?”
柳应笑听话地将佩饰上交,方泽芹接过后两面一翻,这是面黑漆游凤花枝太极盘,纹饰流畅精美,盘面油亮如金,这太极盘应是由阴阳两块拼合而成,应笑的这块为阴面,盘上刻有“四方仁德”的阳文,不似市井杂货。
方泽芹稍一迟疑,见两个孩子牵手话别,神情间多有不舍,心道:即便造价不菲也及不上这真诚质朴的情谊珍贵。
仍是将太极盘给了李春花,南向天见柳应笑与李春花相互赠礼,心里也直发痒,翻袖抖袍,想找出些能送出手的,无奈他刚从城里赶来送行,匆忙间什么也没带在身上,只能道:“小哑巴,等你下回再来,我就带你去家里玩儿,你想拿啥就拿啥,就是要门前的石敢当我也给你抬来。”
孩子气的话把大人们都逗笑了,柳应笑“唉”了声,她刚会说话,发音咬字不准,在人多时羞于开口,只歪头一笑,冲着南向天挥了挥手。
方泽芹对李春花与南向天叮嘱几句话,不多寒暄,向一行人拱手作别,翻身上马,将应笑抱在身前,两腿轻夹,那马便撒开蹄子轻颠而去,离了龙江府又取路投江南东路,望江陵府方向西行。
!!!
师徒二人自离开龙江后拣僻静小路迂回前进,白天行路,夜晚歇宿客栈,到了缺医的乡间便摇铃行医,多治顽症难症,若遇贫户则免诊金,若经过贫村便义诊赠药,如此且行且停,在路上辗转一个多月,到得舒州境内。
这一日,天色渐晚,方泽芹骑在马上教小徒弟念诵药诀:“药有温热,医家总括:菖蒲开心气,丁香快脾胃,扁豆助脾,莞香下气。”
柳应笑掰着手指念道:“白木香下气补肾,定心痛,扁豆助脾,以酒行药有破结之用,丁香快脾胃止吐逆,菖蒲开心气治耳聋。”咬字发音还带有些齿风,腔调却学得似模似样。
方泽芹笑着夸赞:“应笑好生聪明,为师只在早上随口一提,你却都记了下来,可知这几味药材形貌如何?”
柳应笑受了夸奖不觉脸色微醺,点头道:“莞香生于树,其叶互生,呈卵形,先端由短渐尖,花黄绿色,择大树,在树干上顺砍数刀,树液自出,数年后即可结成油膏,落水即浮,研磨成粉,色深而带烈香。”
方泽芹见她描述得宛若亲见,不由略感诧异,问道:“应笑可见过莞香树?”
柳应笑脸色一变,垂下头,低低地道:“都是听娘说的,娘教我分管药材,常带莞香木碎回家,想是山里有这种树……”她说着,抬手捂上心口,轻喘两声,往后靠在方泽芹胸前。
方泽芹摸她的小手,略有些发凉,额头上也出了层薄汗,忙问道:“不舒服?”
柳应笑摇摇头,轻声说:“只是有些气闷,不要紧。”
方泽芹一把脉,再按柳应笑的肚腹,便知这是脾胃运化功能衰退而导致的气滞之症,遇到此类情况,最好能以热水活血消淤,思及此,他便打算找处能落脚的客店,可走了许久也未见一村半坊。
这时日头已落,林间幽暗,眼见这前不着村后不巴店,方泽芹寻思:再走下去恐怕也是徒增疲倦,不如寻处避风的地方露宿,先用通气的药缓上一缓,明日再投宿歇息。
正踌躇间,远远望见林荫里灯光隐现,方泽芹心头一喜,赶紧驱马往灯光处前行,转出林子一看,前面有座大庄院倚靠在土路边上,外围筑有土墙,周遭种植百来株翠柏,看来是户富裕家宅。
作者有话要说:防抽:
赶到坟地时,柳元春的尸体已入棺,一名老僧正在棺材前念经,曹村长见柳应笑被抱来,连忙迎上前,解下腰间麻布递给方泽芹,低声道:“来得巧,正要盖棺。”
方泽芹将麻布条扎在柳应笑额上,领她至棺前跪下,柳应笑见棺里躺着个人,一整块麻布从头盖到脚,也看不出是谁,她茫然地望向方泽芹,不自禁地抓住他的衣袍。
方泽芹道:“应笑,棺里便是你娘。”
柳应笑愣了一愣,趴在棺前看了会儿,叫唤道:“呀……呀!”伸出手,停在空中悬了片刻,似是有些胆怯,但终于还是轻轻拍上麻布,放大声音叫喊,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到最后带上了哭腔。
曹村长与两名庄客看得不忍,不禁垂头叹气。诵经的老僧提醒道:“时辰就快到了。”
方泽芹蹲在应笑身边,揽住她的肩膀,轻声道:“应笑,要盖棺了。”
柳应笑拼命甩头,伸手在麻布上轻推,用劲拍打棺木边缘。老僧用平淡的声音下令:“时辰到,盖棺入土。”
两名庄客走上前,手往棺盖上一搭,柳应笑惊慌起身,倾身趴在棺口,对着庄客摆摆手,又乞怜地看向方泽芹,哀求道:“呀!啊……”
方泽芹狠下心肠告诉她:“应笑,你娘不会醒了,她已经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明白么?”
柳应笑呆了一呆,伸手就想去掀麻布,方泽芹一把抱住她,强行把她从棺材上剥下来,曹村长大喝一声:“盖棺!”
两名庄客立刻推上棺盖,扎桩结绳,将毛竹杆插入绳结里,一人扛一头,将棺材挑起来放入坑里,曹村长把竹片、木篓、陶罐等器物填塞在坟坑与棺材的缝隙之间,下铺锦被上盖草席,诸事办妥后便叫庄客铲土掩埋。
眼见那一钵一钵的土被洒在草席上,应笑心里疼痛,忍不住放声大哭,只觉得胸口被一股气撑得发涨,这气逐渐升至咽喉,似被尖锐的硬物梗住般灼烫刺痛,她张大了嘴,那尖锐的硬物忽而化作一团热气冲开喉咙,心里的话就跟着热气被呐喊了出来:“娘!娘——!!不要睡!不要睡!我听话了,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听话了,你别生气!”
方泽芹一惊,不由得悲喜交加,激动之余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乱不择言地安抚道:“应笑,乖,好孩子,你娘没生你的气,她知道应笑是好孩子,不哭不哭。”
柳应笑挣开方泽芹的手,跌跌撞撞地跑到坑前跪下,抹着眼泪用力地磕头,哭道:“娘,我不骗你,我天天陪你,哪儿也不去,娘,你起来打我,你起来打我啊!”
方泽芹见她额上的麻布渗出血来,连忙上前制止,两手按住她的肩膀沉喝一声:“应笑!”
柳应笑被他的喝声惊得浑身一震,双手握成拳缩在胸前,就这么僵住了,泪水欲掉不掉地在夹在眼眶里。方泽芹心口猛然一抽,伸手抚上她磕破的额头,叹息道:“应笑,你娘累了,让她好好睡吧。”
柳应笑抽噎着小声问:“娘走了?”
方泽芹轻“嗯”声,她又问:“不要我了?”
方泽芹摇头,指尖抹去她的泪珠,柔声道:“你娘怎会不要你呢,她只是太累了,应笑,她会在别的地方看着你,守着你。”
柳应笑垂下眼眸,含糊低问:“娘……会回来吗?”
方泽芹轻轻摇头,应笑瘪起嘴:“见不到了吗?”
方泽芹沉默片刻,摸摸她的头,颔首道:“见不到了,再也见不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