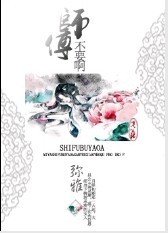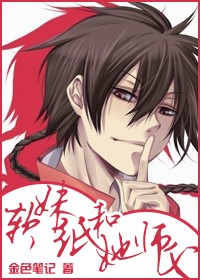师父,床上请-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路掩着身份,亦不张扬,无风无波地到得仙女峰下,嬷嬷却不让应笑下马车,吩咐护卫先行传报,叫人下来接驾。
应笑道:“何需叫人来接,你们不识得路,由我领着上去便是。”
嬷嬷笑道:“公主,您如今身份不同了,岂能还与从前一般?这是娘娘交代下来的,需叫方大人对你另眼相看。”
应笑总觉不踏实,听说是太后的意思,便不作声了。
那里,方泽芹才将门内大小事务料理妥当,刚要回馆,忽而门人报说公主驾临,正在山下候着,叫门主亲去接引。方泽芹正在收拾药箱,听到此话,手上发力,将木楞掰下一角来,冷声道:“告诉传报的差使,便说我在祖师殿上恭候大驾,叫他们自个儿上来!”
门人见他似有怒气,不敢作声,只得匆匆出去,把门主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回给传报之人,那护卫没奈何,复又下山回禀。
嬷嬷闻听,笑道:“咱这公主的架子还没端出来,他那门主倒是了不得了。”
应笑却深感惶恐,忙道:“自来只有徒儿去拜见师父,没有师父迎接弟子的道理。”
嬷嬷暗自乐道:还师父弟子?殊不知这趟来便是要断了师徒关系哩。
于是搀着应笑下了马车,由公公引着,护卫随着,一行人径往山里而去,自有门人引上祖师殿,到得广场,就见方泽芹领堂主肃立阶上,各堂弟子与道众分立两旁,躬身行礼。
这时魏公公才扬声道:“传太后口谕,医圣门门主,万和大夫方泽芹跪下听旨。”
这话一出来,阶上阶下呼啦啦拜倒一片,应笑正待跪,嬷嬷却扶住她,道:“这是娘娘给方大人的口谕,公主不必跪了。”
应笑却道:“师父双膝落地,弟子焉能站着?”当下不顾劝阻,毅然跪倒在地。
那魏公公宣了口谕,却是以公主身份不同以往为托辞,限令方泽芹三日之内写下文书,与应笑脱离师徒关系。
此言一出,莫说在场众人各自惊疑,便是连应笑自个儿也诧异莫名。方泽芹大怒,倏然起身道:“这世上只有师父逐弟子出门,从未听过徒弟不认师父这等忤逆之事!还请太辅回去转告太后娘娘,就说方某恕难从命!”
魏公公也不恼,笑眯眯地道:“方大人,咱家只是来传信儿的,回头自当把你的话对娘娘逐字逐句地禀明,娘娘若怪罪下来,恐怕大人担待不起,咱家这是好意给大人提个醒,还望三思而后行。”
方泽芹道:“不劳太辅费心,我自会一力承担!”
嬷嬷好生讶异,心道:这大人端的是一身傲气,果然如娘娘所说,是果决凌厉之辈,在府上看他对公主似有情愫,这会儿听了口谕却勃然变色,莫不是我看错眼了,原来他当真只把公主看作徒弟么?
那魏公公传了谕,见方泽芹没有留客的打算,便自领护卫而去,嬷嬷受了太后嘱托,还要留在公主身边伺候着,便随着一道进了东馆,铺床扫尘不在话下。
这边才歇住脚,那边就进来个门人传话,说门主请见。应笑心内忐忑不安,直如胸口里揣了个兔子,突突地跳个不停。引至净室,那门人掩门而去。应笑见方泽芹盘坐榻上,脸色黑里透黄,情知这回是惹恼了师父,忙扑在榻前跪下。
方泽芹俯身扶起,盯着她的脸端量许久,皱眉道:“应笑,为师自来由着你,也是因你乖巧懂事,为何这时却要让师父为难,师徒这关系是你说不要便能甩去的吗?”
应笑委屈道:“师父错怪徒儿了,徒儿并不知道娘娘下的甚么口谕。”
方泽芹站起身,双手按在应笑的肩头,问道:“那你告诉为师,为何接连三个月不回来,为师去找你也不肯露面,你不是在避着我吗?如今要我与你连师徒也做不成,不是娘娘要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么?应笑,你是为师养大的,这事我断不可能答应!”
应笑忽而有些难受,反问他:“娘娘要我作陪,只是三个月便让您老人家如此着急,那你要我嫁人,要我嫁给别的男子,可是一生一世的大事,你却推得心安理得么?”
方泽芹道:“为师已说过让你孝敬到老,再不提那等事。”
应笑听他又老调重弹,真是心头上火,实不想再谈下去,说了声告退便要离开,方泽芹却拉住她的手腕,沉声喝道:“不准走!话还没说完,为师不许你离开!”
应笑低呼了声痛,刚然回头,便觉唇上一热,竟与师父对上了嘴,她吓坏了,忙偏开头,往后退了两步,只羞得满面通红。方泽芹把她拉入怀中抱住,嗅到颈间幽香,更是难以自持,便俯□去将这可怜可爱的小徒弟好好亲个够。
这先生此刻是乱了心、迷了性,因着太后收养应笑,连占她数月不让出宫,便觉心慌意乱,生怕小徒弟就此深锁宫门,再也回不来了。今日,那魏公公又传太后口谕,要断绝他师徒俩的关系,想他含辛茹苦拉扯大的乖徒儿,旁人说带走便带走,说恩断义绝便恩断义绝,你说这先生该有多不甘心。
他也是连日来担惊受怕,突遇变故难免恐慌失常,也未及细想这口谕背后的用心,还道太后娘娘真要与他抢徒弟,一急之下却是露了真意,可算是百般隐忍顷刻尽释,不觉情动如潮,一发不可收拾,哪还能顾得了心中那许多周详盘算?
应笑却是被吓得不轻,愣愣地呆了半晌,等回过神来,“呀”了声,忙背过身去,竟慌得踩了裙角。方泽芹扶上一把,继而从后抱住她,柔声低语:“应笑,师父这般喜爱你,与你对为师的心意有何不同?师父不说自有不说的考量,你这孩子,却是逼得我无处可走。”
应笑羞得不敢抬头,转了个身,把头埋进师父怀里,闷声道:“徒儿正是不愿逼着师父才觉难受,师父寡欲少求,徒儿要你做什么,你便做什么,只当女儿般来疼爱,却不像是自个儿愿意的。”
方泽芹道:“为师却不是你所想的那等人,我活到这把年纪,只为你伤过神,总想着怎么做才是对你最好的,总要为你方方面面都打点周全,我想你这丁点大的小人懂得甚么男女情爱?这时对我有意,未见得是真意,若是全依着我的心情,如这般逾越师徒本分,日后你遇上良人再来后悔,岂不是要怨怪我?为师便要再等等,待你大些,定性了,若想法仍是不变,我自然再欢喜不过。”
应笑心中既是感动又有些恼怒,说道:“师父这般说,却是将徒儿看小了,说甚么定性,可不知在徒儿眼里,除了师父的脑袋是脑袋,旁的男子项上都顶了个西瓜呢。”
方泽芹忍俊不禁,拢着小徒弟往榻前坐了,执着她的手问:“那向天的项上也顶了个西瓜么?”
应笑愣了一愣,见他面上带着些尴尬的神情,不由了然,垂下眼眸道:“他却是朋友,与春花一般无二。”
方泽芹叹了口气,说道:“为师亦然,只是你我名为师徒,若我孤家寡人一个,自带你去找处安心之所过活,如今却还要顾着这一门子弟,不能叫医圣门的命脉断在我手里。”
说到这里,不觉想起太后下的那道口谕,这才恍然了悟,应笑也有知觉,喃喃道:“娘娘传口谕要你我断了师徒关系,莫不是有意解围?”
方泽芹道:“惭愧,为师一时心急,没领会到娘娘的好意,但有一点,这不似在宫里,纵是圣上亲下诏令也未见得有用,你我以师徒相处多年,岂会因一纸空言而改变?朝堂那一套只能抑臣下口舌,在这江湖上却是行不通的。”
应笑道:“师父便是师父,徒儿晓得你的心意便足够了,也不要师父娶我,还像往常那般处着便是。”
方泽芹笑道:“这却真是孩子话了,莫说为师从未这般想过,料那太后娘娘是第一个不答应,再等些时日,待为师将门内事务料理好了,便与你定下名分,也省得日夜心神不宁。”
应笑心里欢喜,倾身往师父肩上靠去,方泽芹搂住她亲亲鬓角,见小徒弟满面闲适安然,心下不住叹气,说道:“应笑,为师却有些事还未告诉你,只怕说出来会让你生嫌。”
应笑道:“徒儿便是嫌自己,也不会嫌师父,师父不信任徒儿,总瞒着我去做些事,你夜里换装出门,我还会不知道么?”
方泽芹笑了笑,道:“随师父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拨云见日02
于是引着应笑自出东馆,绕过连山道观,进入后山,曲曲绕绕不知走了多久,来到山根下,见有两座灰白色的巨石错落相夹,矗立在山壁前,石缝中汩汩流出清水。
方泽芹道:“这是为师练武之处,需得费些气力才能进去。”便让应笑退远,掌上运气,击打石面六次,听到“咔”的一响,将双手抄入石缝中往两边掰开,推出一尺来宽的距离,露出后面一个黑黝黝的山洞。
入洞走了不远便至宽敞的洞厅中,厅内横着供桌,桌上放着一座灵牌,应笑看时,只见灵牌上刻有“先师萧远之”五个黑字。应笑不禁讶然,问道:“鹤亭先生过世了么?”
方泽芹道:“鹤亭先生是授我医术的老师,而这灵位上的,却是传我武艺与处世之道的人,此人的名声比鹤亭先生响亮许多,却不是甚么好名声,应笑,你也该听过,这萧远之又名萧森,是江湖上人人憎恶的尸王。”
应笑愣了一愣,瞧了眼方泽芹,又再看向灵位,说道:“尸王萧森竟然是师父的师父,看这牌位,想是过世有些年头了,如何能杀得了那恶侯爷?莫非是有人冒名顶替?”
方泽芹道:“当年,萧森被江湖门派围杀至重伤,为了避人耳目,便躲在这山洞里当起了野人,为师给他水食,要他传授武艺作为回报,不过,萧森已于十一年前在这夹水关中病故,杀永昌侯的的是为师,萧森死后,又有多起借他名号犯下的凶案,皆是师父所为。”
应笑怔愣半晌,摇了摇头,说道:“师父是好大夫,是个有善心的人,徒儿那时失言,说要下药让永昌侯变为废人时,师父分明说医者不该有害人之心,怎有可能杀人?”
方泽芹对她摊开手掌,道:“为师这双手杀了很多人,我在行医途中,但凡遇到该死未死的恶徒,都假尸王之名暗中除去。”说着,从袖里掏出一根指粗的竹管,续道,“这便是用来杀永昌侯的尸毒,乃是萧森的独门秘药,你可知他为何被称作尸王?正因善用尸体育毒,这管中的尸毒虫正是在为师协助之下栽培出的毒蛊。”
应笑问道:“师父只杀坏人,可曾害死过无辜的人?”
方泽芹道:“为师在初学医时因下错药治坏了不少病,也有因此丧命的。”
应笑道:“那却是无心之举,师父为何从不对徒儿提起这些?”
方泽芹审视她的面容,未见厌憎之意,不由暗里松了口气,道:“你总以好坏论人,怕是会将我想成面善心恶的奸人,又且为人师表,自当以身传教,怎能在弟子面前显出那些暗昧手段来?”
应笑微微撇嘴,斜瞟着他,软声问:“既是如此,师父为何在这时却说了,不怕教坏了徒儿么?”
方泽芹道:“若以师长自居,自不会叫你知晓,如今却有不同,你要孝敬为师到老,我也将你当作这一世的伴侣,在应笑面前,我是师父,也是个普通男人,便想叫你把这个名为方泽芹的男人好好看个透彻。”说着俯身凑近。
应笑面色微红,伸手轻抹师父的额头,却是不敢看他的眼睛,只偏垂着脸,低声道:“徒儿在师父面前不仅是个年小的徒弟,也想做个寻常女子呢,师父可看透了没?”
方泽芹见这羞怯的姿态里竟略显出妩媚来,不由心神一荡,险些在尊长灵位前无状,忙退后两步道:“应笑,为师之所以带你来此,是想让你拜见先师。”便从桌上拈起三炷香点燃递上。
应笑却不接过,皱眉道:“师父,萧森若是那等残害无辜的恶人,恕徒儿不能拜。”
方泽芹闻听,暗道:这孩子倒是明大理。
便道:“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萧森绝非穷凶极恶之徒,只因他生性怪癖,行事张扬,不屑这道上的规矩,非要反其道而行,难免犯了众恶,在有心人士的拨弄下成了江湖上的恶魔头。”这一说倒是不假,他却仍是将萧森早年杀人取尸的斑斑劣迹给瞒了下来。
如此一来,应笑便放宽了心,随方泽芹三叩九拜,给萧森上了香。师徒二人往侧方洞室进入,这洞窟里有张岩石凿出的床榻,便是修炼内功的地方。方泽芹拉应笑在石床上坐定,对她道:“为师有个不情之请,我说出来,你却别多想。”
应笑嘟哝道:“徒儿会多想全是因师父甚么也不说,你若言明,一切清清楚楚,徒儿便是要多想也没处钻心思呀。”
方泽芹心下一宽,笑着说:“你总是有理。”定定地望着她,执起手道,“你我之间虽是有情,为师却希望你暂不要在外人面前显露声色,寻常还当师徒来处,太后娘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