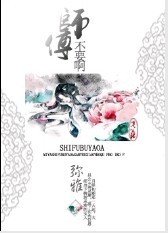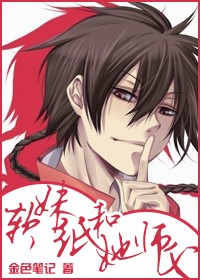师父,床上请-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天只道是熟透了的人,亦不避讳,也不循着那套繁文缛节,坦而直言:“我这大老粗也不懂甚规矩,只道家业已成便当娶妻,我与应笑自小相识,彼此熟悉,而今她尚未婚配,学生也未定亲,便想结个长久姻缘,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应笑原是让他避着人私下开口,哪儿料到话说得这般没遮没掩,当下挣得满脸通红,只把头低了看桥下。
赵文意悄立一旁观望,心里暗自乐道:这是哪里来的楞二爷,提亲这头等大事也不避着姑娘家,竟当成是家常话来拉扯,岂不有失慎重?我若是先生,见了他这股冒失劲儿,断是不敢许的。
方泽芹却道:“你可有问过应笑?”
向天道:“她只说婚嫁大事当由父母作主,叫我先问过先生的意思。”
方泽芹沉吟许久,说道:“这事还需你情我愿,我这做师父的也不便自专,若是应笑情愿,方某自是…自是……”说到此处心里发涩,这后面的话是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
应笑听得前句,那后半句还需明说么?自是又要把她往外推,心中好生气闷,思忖道:我分明说了不愿嫁人,师父自是晓得的,如何还要问?好啊,他面上对我千依百顺,心里怕是烦得很,若不然,怎的总觑着些空子就要送我出门?
这么一想实是难受至极,鼻子发酸,泪下两行,恨不得就允了向天,可转念再想:我虽喜欢向天,却不是女子对男子的喜欢,倘若贸然允下,不是成心要骗他?
于是将莲花莲叶俱都还回向天手上,抹泪说道:“对不住,向天,我早便决意今生谁也不嫁,只愿出家修道,你我朋友一场,话若由我说穿,岂不叫你难堪?师父分明晓得应笑的心意,本指望他会替我婉言相告,谁想却佯作不知,我实不愿牵累你,不能说着昧良心的话讨你欢喜,你去寻别家好姑娘吧,找我是不成的。”
说着转身便往桥下跑去,南向天与方泽芹俱都愣在当场,待回过神来时,应笑已没了踪影。南向天还不知就里,向方泽芹问道:“她这是何故?好好儿的花姑娘不当,偏要去出家,莫不是见春花当了尼姑,她便非要当个道姑来凑成双?”
方泽芹望着桥头发呆,好似头顶飘三魂、脚底荡七魄,谁说的话也听不见了,心中纷乱如麻,只不由自主往应笑离开的方向走去。
南向天正待跟随,赵文意却往他身前一挡,拉长了脸冷声问道:“你是哪家府上的?如此没规矩!见了本宫也不行礼?”
☆、王府03
南向天这才留意到还有个外人在,愣了愣,问道:“你是谁?”
赵文意缓下脸色,挑眉笑道:“你站在我家的地头上,还问我是谁?”
南向天心忧应笑,无暇顾它,只道:“这姑娘,我有要事,得罪之处还望多包涵。”便要绕开她追过去。
赵文意又横出一步将他拦住,说道:“本宫乃是东平王之女永庆郡主,你姓甚名谁,是哪里官员?”
南向天一愣,忙作揖道:“下官南向天见过永庆郡主。”
赵文意笑道:“原来是南观察,常听姚将军提起你,真是久仰大名。”
南向天心焦如焚,踮着脚往郡主身后望去,说道:“下官有要事待办,不想冒犯了郡主,这便告退。”
赵文意道:“你的要事可不就是要去找小师妹?”
南向天却不知她指的小师妹是谁,赵文意心里暗骂:真是个楞爷。
便道:“本宫曾投在先生门下学习医术,先生的徒弟自然是我的师妹,你还是歇着吧,莫去自寻烦恼,小师妹对你无心,你若再缠搅,岂不是叫她为难?”
南向天正色道:“应笑与我自小相识,是我的救命恩人,纵是不谈儿女私情,朋友情谊还在,如今她好端端要去出家,我怎能袖手旁观?定然要去劝她一劝,想她才多大年岁?这时遇不上知心的,难保往后能碰上,如何恁的看不开?”
赵文意心想:这楞爷倒是个爽快直性的人,虽是莽撞,却也干脆利落,还是个热心肠,莫怪乎姚将军与包大人如此提携他,只是这男子也忒呆了些,瞧那师徒二人的神情还瞧不出端倪来么?
这郡主到底是姑娘家的玲珑心,起先因情窦初开,见了门主仪表不凡、颇有名士之风,自是心生仰慕,那却只能远远观望,光这么看着是君子无暇,几番交谈下来却有些不如意,只因那先生礼数顾得太周全,待人却是极其疏淡,不似在医圣门时那为人师表的光景。
赵文意是个活泼性子,好动爱玩,二人对座吃茶,那先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这边说着话,那边魂却不知去了哪里,总是放着姑娘家滔滔不绝,他先生只低头看盏,好似茶盏子上长出金豆子银豆子来了,从不把目光放在人脸上。如此这般,文意与他共处时便觉无趣,一想日后若要天天对着那张淡而无味的脸面,不免兴致大减,遂冷了初时的情意。
便如先前博弈之时,本是杀得难分难解,可见先生技艺之精,谁想小徒弟一走,把他的魂也给勾去了,往后便敷衍了事,一手下着棋子,目光却不在棋盘上,总是往西门外游离。
赵文意落在眼里,心内自思:我看这先生对小师妹挂心得不寻常,莫非他不思娶妻的根源在自家徒儿身上?
那时还存疑,见了应笑的举动之后,料想这师徒之间已然暗生情愫,再看师父失魂落魄的茫然神态,便晓得还有层窗棚纸没捅破,都各自畏首畏尾,梗在葫芦腰子里了。
这郡主虽觉惋惜,毕竟没投下多少感情,已自收了心,见南向天还无所知觉,便有意点他一点:“南大人,你想医圣门乃从属于归云道派,本是个道观,如今先生接掌门主之位,也算半个道士,小师妹不想嫁人只愿出家,可不正是为了留下来孝敬她师父?先生至今未娶,不也是成心想受徒弟的孝敬?你说,这不是黄盖周瑜愿打愿挨的事儿?何需旁人操心?”
南向天经此一说,犹如醍醐灌顶,骇然变色道:“应笑是先生带大的,他二人不仅是师徒,更情同父女,若真如你所言,岂不是乱了伦常?”
文意暗自思忖:看那先生裹足不前的模样,怕是与你这楞二爷有同等想法呢。
她也不多言,见南向天仍傻愣愣地原地发杵,显出些失落的情态,心觉可怜,便道:“姚将军在后殿,前头见着时正念叨你,何不与我同去见个礼?”
南向天道:“你且在此等我片刻。”
文意正待问何事,却见他跑去湖边,将莲花莲叶洒在水里,扑在老树干上哭了一场,回来时已是精神抖擞、满面畅然。文意好生惊奇,心道:哪有这等将喜怒哀乐尽摆在一张脸上的男子,这楞爷实是好玩。
见他两眼通红,脸颊上还带着泪痕,便从袖里抽出帕子递上,笑道:“大人,把泪擦擦干,见了姚将军,千万莫说是我欺侮了你。”
南向天面色一红,接过帕子胡乱擦了两下,伸手还回去,文意却不接,说道:“这帕子上沾了灰,我不要了,你洗洗自个儿用吧。”
南向天自是不会用姑娘家的花帕,也不便当着郡主的面弃了,他见绣帕柔软精细,倒还真觉扔了可惜,便往怀里揣好,拱手道:“多谢郡主赏赐。”
文意瞪圆了双眼,心下暗暗好笑,想道:这楞爷果然呆头愣脑,我实是笑他面上脏污,他倒当成甚么赏赐,也罢,随他乐意吧。
当下多瞟了向天两眼,二人一前一后,自往林荫道上走去。
!!!
且说应笑负气跑开,沿路而行,不知走了多久,见前方叶影间掩着一带粉墙,似是所院落,往前走不出多远,惊见一片彩云也似的花圃,犹如锦绣铺成,满地芳菲嫣然如霞。
应笑看得目眩眼花,不觉走进花丛中,拣了块草皮席地而坐,看着满目花景,回想起当年被师父带着去洛阳游玩的往事,那时年小不知愁,总被师父抱在怀里、扛在肩上,往日光景还历历在目,却只能这般空想,再也回不去那时了。
应笑想想伤心,禁不住低声抽泣,暗恨光阴流逝太快,欢乐总是一晃而过,越是长大越添了许多愁苦,正伤怀时,忽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谁家丫头这般好心,跑来我这花田里浇水?”
应笑回头看时,就见有个嬷嬷扶着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母从院里走出来,应笑忙站起身,弯腰致歉。老母迎上来,侧头端量,说道:“先抬起头来。”
应笑依言抬头,老母瞧了她许久,问道:“你叫什么名?家住哪处?”
应笑想这老母住在王府里,当是一位家主,不敢怠慢,恭顺回道:“回老太太,我叫柳应笑,是龙江府人,原住在基山脚下,随师父前来贺寿。”
老母略略颔首,伸手将她面颊上的泪珠轻拂去,笑问:“娃娃,你为何在此落泪?”
应笑见老母面容慈祥,目光甚是温柔,心内竟自涌起一股暖意,说道:“我在此看花,想着光阴荏苒,花谢来年开,人去不复还,便觉难受了起来。”
老母望了她良久,忽而笑道:“你这娃娃才多大年岁?竟这般多愁善感,正当花开之际,愁甚么花谢人去。”便牵着手往院中花亭小坐,吩咐侍女铺下茶果点心。
应笑哪能吃得进去?只捧着茶盏浅啜两口。老母问道:“方才你说随师父来此,你师父又是何人?”
应笑道:“师父姓方名泽芹,被封了甚么官,我却不太清楚。”
老母笑道:“原来是方渭帅家的公子,我听过你师徒二人的事,那师父是医门之主,你这徒弟想必也相当了得,老身近来身体微恙,找了大夫,开了些药,却是不见多好,你来给我看看。
应笑听老母说话时声音略微沙哑,带着些痰音,便问:“老太太是个甚么症候?”
老母道:“腿脚酸痛,弯曲时尤为不便。”
应笑坐在老母身前诊脉,再看面相,见眼睛发红,下唇起了些皮子,便问:“老太太可是觉着口干舌燥,胸膈不畅?”
老母道:“确是有些胸闷,夜间身上发痒,似有虫爬。”
应笑又问:“可是小便短赤?”
老母一愣,隔了会儿才道:“确是如此。”
应笑便要开方,老母吩咐摆上笔墨纸砚,应笑开了一剂地黄汤,再加山栀子与柴胡两味药为辅。
老母有意试她学问,便问:“这方子可有甚么说法?”
应笑回道:“老太太身痛是筋脉拘挛,筋脉需以血养,目赤乃是肝血不足,如此一来肝火便重,口干有痰是体内津液不足,夜间起病则是阴虚,是以要用上滋阴补血的地黄汤,再用清虚热肝火的山栀子与柴胡为辅药,一面补血,一面平肝,三日便能好了。”
老母见她言语明晰,说得头头是道,不由满心欢喜,立时吩咐按方抓药,屏退左右,单与应笑叙起话来。
应笑久未与人谈心,这时见老太太慈眉善目、气度从容,便觉莫名可亲,如同遇上了亲家人,便将过往经历细细道来。老母听得目中含泪,执起应笑的手拍了又拍,叹道:“苦了我这女娃娃了。”
应笑道:“多得师父照应,应笑才能有今日光景。”想起方泽芹,她自黯然伤神,却不知这一番女儿情态尽落在老母眼里。
老母不住地看去,听她说得那些话,十句里倒有八九句离不开师父,心下便有了知觉,探问道:“适才见你在园中落泪,可是与你那师父相干?你不要瞒我,好好儿说个明白。”
应笑撅嘴道:“师父好不利索,明知徒儿想孝敬他一世,却总盘算着要将我嫁人。”于是将之前发生的事俱都吐露出来,说完之后便觉心气畅通。
老母道:“这也怪不得你师父,到了这年岁,哪家长辈不急着给自家孩子找一门好亲事?”
应笑轻声嘟哝:“我却不愿他把我当孩子看呢。”
老母笑道:“你不也把自个儿当孩子看?说的都是些孩子话,瞧瞧你小不隆冬,无一处不像个娃娃,叫旁人如何能不将你看小,若想令师父另眼相待,还需端正自身行止,做出个姑娘家的模样来。”
于是领应笑进了寝室,叫嬷嬷找来几件衫裙,一件件比过,挑了件合身的,老太太亲手为应笑换上,见她胸前挂着朱结锁与香囊,便问道:“你只有这两件随身物?不似是家传的宝贝。”
应笑道:“还有块半面的太极盘,说是祖父留下的,我与姐姐交情深厚,她送了我朱结锁,我便将太极盘给了她,都是一家亲,不分彼此。”
老母已知春花的遭际,默默留意在心,换上衫裙后瞧了瞧,真个是芙蓉出水,愈发惹人怜爱,把个老太太喜得眉开眼笑,向那嬷嬷问道:“你看如何?”
嬷嬷举目端量,掩唇轻笑,说道:“极是好看,这衣衫是娘娘还住在湖州时穿过的,奴婢一直好好存着,如今穿在小姐身上,却颇得您老当年的风范。”
老母叹道:“我这才是人老一去不复还,像她这般大岁数时,哪里晓得愁?”
嬷嬷一笑,又道:“人和衣衫倒是相衬了,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