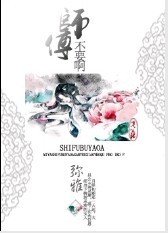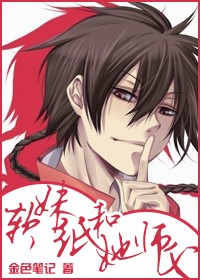师父,床上请-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忽听应笑在里间问话:“是师父吗?”
方泽芹道:“是师父。”快步走到床前,见应笑缩在被子里,双手捂脸,额上全是汗,他忙揭开被子,扯来外袍替她擦汗。
应笑放下手,仍闭着眼睛,问道:“师父去了哪里?”
方泽芹随口道:“去了趟茅房。”
应笑沉默片刻,轻哼了声,转身朝向床里,气鼓鼓地说:“你们大人专会骗小孩子,这儿与师父家不同,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乡里乡间更无茅房,攒着黄金要去浇灌田地呢!”
方泽芹暗道“惭愧”,心想三年不见,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好唬了,便说:“师父怕把你臭到,自去林子里解决的。”
应笑哼哼地道:“那敢情师父是闹肚子了?”
方泽芹微愣,问道:“应笑醒了多久?”
应笑道:“有些时候了,喊师父没人应,徒儿又不敢睁眼看天色,不知到了什么时候。”
方泽芹听她语气冲冲的,憋屈地很,心下好笑,从后轻轻抱住她,问道:“为何不敢睁眼?这么大的姑娘还怕黑么?”
应笑道:“徒儿是为师父着想。”
方泽芹奇了:“这怎么说?”
应笑道:“师父适才跟徒儿说了什么?‘明儿早上一睁眼,保准叫你看到师父’,若徒儿睁了眼,师父又不在,岂不是叫师父做了不守信义之徒?所以徒儿只能闭着眼等师父回来呀。”
方泽芹听出她在赌气,好声好气地道:“为师已经回来了,来,转过来看我一眼。”说着伸手去扳她的肩膀。
应笑起先倔着劲,被师父扳了两下后气就顺了,乖乖转过身来看师父,张大眼睛眨了眨,抬高手从师父头上摘下一片叶子,拈在两指间转动,说道:“这是水杉的叶子,荆湖岸边才有。”
方泽芹心知这孩子不好糊弄,只得老实坦白:“除了上茅房,为师还去干了些别的事。”
应笑扒拉在师父身上闻了闻,又伸手轻摸微湿的长发,说道:“师父下水了,有湖水里的草腥味,你又到游舫上去做什么呢?”
方泽芹笑道:“替应笑把辛苦钱讨回来,再猜猜,师父还去了别的地方。”
应笑摇头回说:“猜不到,师父回来就好。”
方泽芹道:“我去城里打探荷云的下落。”
应笑一愣,弹身坐起来,方泽芹拉住她,也跟着起身,见她着紧那毒妇,心中不免郁闷,应笑轻声问道:“那……找着了吗?”
方泽芹踌躇不决,暗自想道:应笑竟这般重视那荷云,若说出真相必会惹她伤心。
挣扎良久,按住应笑的肩头道:“荷云此刻正在朱雀楼,却不是被捉去的,是她心甘情愿送上门,为师见她在楼里过得舒服自在,便随她的意了,你也无需再为她担心。”
应笑垂下眼,低声问道:“子元真人没为难她么?”
一回想在楼里的所见所闻,方泽芹就怒火中烧,吐纳数回方才压下怒气,叹道:“他二人同桌饮酒作乐,有甚为难?应笑,她对你的好并非出自真心,师父不想让你伤心难受,却也见不得你对那样一个口蜜腹剑的毒妇人投下感情。”
应笑咬住嘴唇,喃喃道:“我能瞧见别人面上的好坏,又瞧不见心里的,谁知道心里是黑是白呢?也只能认面上的好了,她对我好时,我便也对她好,对我不好时,那不理会就是了,我也不伤心,也不难受,因她对我不好才是应当的,我不是她生养的,为何要对我好?”
方泽芹不禁愕然,绝没想到她会有这样的想法,只听得心惊胆跳,不知该如何接话。应笑复又躺下来,将头发丝绕在指头上把玩,说道:“我仍是感激她的,如今晓得她心地不好,以后不见就是了,听师父说她过得快活我就放心了。”
方泽芹怔愣半晌,也睡下来,揽住她道:“能看得开是好事,只是你这番话倒叫为师不甘心了,你也只认师父面上的好,却不相信我是真心待你?”
应笑道:“我看不到别人心里的好坏,却晓得师父是个大好人,你对不认识的都好,对徒儿就更好了,徒儿当然认师父的好,面上也好,心里也好,若要说有哪些不好……”说到这里她就抿起嘴巴了,怯怯瞥了方泽芹一眼。
方泽芹坦然笑道:“师父有哪些不好,你说出来,为师改就是。”
应笑却道:“改不了,只因师父是大人,你们这些大人总是仗着年岁长就不把小孩子瞧在眼里,我见到的都是这样,师父比旁人好些,也还是有这个怪毛病,可不知你们大人的言行举止可全落在孩子眼里呢,我看着、记着、想着,时常觉得你们怪滑稽可笑的。”
方泽芹惊笑,问道:“师父哪儿让你觉得滑稽可笑了?”
应笑有板有眼地道:“师父睁眼说瞎话的时候就挺可笑,你道小孩子好哄骗,却不知咱们也会装傻哄大人乐,应笑不想对师父装傻,以后师父也别再随便诳我,不然应笑会暗地里埋怨师父,还会在心里笑话你。”
方泽芹连声说是,心道:这孩子怎的成了个小人精?往后的日子可要有意思了。
他见应笑用孩子气的口吻说这些老成话,只觉可爱逗趣,忍不住摸摸头发,捏捏鼻尖,恨不得将这讨喜的小徒弟搓成面团揉在怀里。
作者有话要说:望天……某控深入骨髓了,给我来只小徒弟…。…
☆、06
二人又交心畅谈许久,方泽芹见应笑了无睡意,看看天色亮了,便带她起床梳洗,捧上面汤来,问道:“可要熬药汁将红斑洗去?”
应笑摇头道:“不碍事,不疼不痒的,那些药材得留着给病人用。”
方泽芹见她有医者的仁心,心里欢喜,从药箱里取出马蹄木、赤小豆与红枣,塞在红布小袋里,走去替她挂上,说道:“这是避瘟疫的悬挂方,行医的需先顾好自己才能悉心照料病患,晓得么?”
应笑乖乖点头,洗漱已毕,拧了条热布巾捧在手上,踮起脚往头顶上举,眨巴着大眼望向方泽芹,说道:“师父,给你擦脸。”
方泽芹忙双手接下捂在面上,应笑又端来凳子放在他身后,拍了拍,偏头唤道:“师父,请歇着。”
方泽芹一屁股落下去,好似坐慢了;那凳子就会凭空消失一般,应笑颠颠地跑到他背后捏肩捶背,一面念叨着:“昨夜辛苦师父了,湖水凉,您老千万别被冻着,徒儿给您老人家舒筋活血,叫您一辈子也不会闪到腰。”
方泽芹心里乐个不行,笑道:“师父还没七老八十,可吃不住你这般孝敬。”
应笑竖起食指点了点,鼓着腮帮道:“少时不养筋血骨,待到老来徒伤悲,师父,您这会儿不好好养身,日后就会像那三条腿儿的桌子凳子似的,颤巍巍,风一刮就倒了。”
方泽芹哈哈一笑,拱手拜拜,连声道:“受教受教。”说着拉小徒弟坐在身前,拿把篦子替她梳头结髻,谁知三年不练,手也生了,拢半天拢不出个圆揪揪来,没奈何,只得将粗长的发辫一把抓在头顶心,七弯八绕攒成一团,再用方巾包起,拿根布条连巾带发一并束紧。
这是个男子发式,梳在应笑头上倒更显活波伶俐,她自个儿也不在乎,跑去院里收了道袍,换下勒里勒得的肥衫裙,把一身道服穿上,活脱脱就是太上老君炉前的小仙童,方泽芹见她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开窗扫尘、收衣晾衣,每件事都做得似模似样,不觉悲喜交加,暗自叹道:这孩子在外定是吃尽了苦头,真难为她了。
忙走去陪她一起收拾,正忙时,忽听梆子声响,公孙先生在外大声呼喝:“吃饭了!吃饭了!”
这一喊,男女老少俱各起床,捧碗的捧碗,拿钵子的拿钵子,纷纷赶去灶房前领饭,待众人吃饱喝足,方泽芹又安排青壮去村西开田掘井,妇人家全留在村里照顾老人,一切杂事都有分工。
因昨晚又入驻一批难民,公孙先生便觉米粮太少,不够三日吃的,带上赵宏,一人拖一条板车,风风火火地往府城方向去了。
方泽芹带应笑往后村探望病人,正走在路上,忽见一妇人迎面跑来,神色惊慌地叫道:“先生,你快来看看,我婆婆许是不行了!”这是戚家寡妇张氏,丈夫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她婆媳俩西迁避灾,谁知到这村里没多久,戚老太也染病了。
方泽芹随她进屋一看,就见老妈妈躺在床上哧哧喘气,一诊脉,细促不耐按,是个危急重症,当下就纳闷了,心道:昨儿看时病情尚且稳定,怎么才过了一夜就病危了?
便问是如何起病的,张氏拭泪回道:“昨晚吃完药后婆婆便说胸口烦闷,像憋着一团火,叫喂她服下散火的青蹩丸,夜里吐了一回,早上就不行了!”
方泽芹听闻后拍桌而起,把张氏给吓了一跳,应笑见他满面怒容,再看戚老太颧骨焦黄、浑身发汗,便知道为什么气了。方泽芹握着拳头在桌上按了许久,终是什么话也没说,复又坐下来,见老妈妈大汗淋漓、颧高唇白,他就如同被泼了桶冷水,只觉得心里透凉,叫应笑赶紧去煎碗独参汤来。
等应笑端来了参汤,戚老太却再也喝不进去了,喂多少吐多少,药汁从鼻子里直往外冒,到最后已自不能吞咽,捱不出半日便断了气,张氏在床前哭得死去活来。
方泽芹出得屋外,叫人把戚老太的遗体拖到后村荒地上,用干枝柴禾搭了个架子,要放火烧尸。
张氏哪里肯依,扑在老妈妈身上护定,厉声叫骂:“好你个狠心的庸医!就是你那药让婆婆断命的!人都死了你还不让她入土为安,连个坑穴也没有,到了九泉之下让她如何安身啊?”
众人见她哭得可怜,也同来央求,应笑又是难受又是憋闷,看向师父,拉着他的手摇了摇。
方泽芹面不改色地道:“这老妈妈是染病而亡,疠气存内,这疠气正是疫病之毒,此时正当暑天,尸体易腐,尸腐后疠气散出即成病源,人因感病气而生瘟疫,此后转相染易,终遭致灭门之灾。”
众人一听都怯了,不敢再多嘴,唯有那妇人闹腾不休,哭嚎道:“你要烧,便连我一起烧死吧!”
方泽芹不为所动,叫人将她拉远,用浸过药汁的布巾为应笑蒙住口鼻,点起火把往木架下塞去,不一时火焰腾起,将干枝柴禾烧得噼啪作响,方泽芹将应笑拉到上风处远远观望,身后传来张氏发疯似的叫嚣怒骂,字字句句砸在应笑心上,再看被火焰吞噬的人影,只觉得分外凄凉。
待火熄灭,方泽芹用药汁浇在骸骨上,用麻布兜起,带到后山掩埋,应笑默默随在身旁,师父挖坑时她递锄头,师父埋骨时她捧土,又找来一片木板刻字作碑,立在坟头上。
待忙定后,二人已是一身泥污,回村用药汤洗手擦脸,脚也没歇住,又去给其他病患复诊,直到午时才总算闲下来。
回到屋里,不消人说,应笑自拿出笔墨誊抄诊籍,方泽芹煎了药茶端上桌来,见她一声不吭,便问道:“有何心事?”
应笑停笔,皱眉看向方泽芹,说道:“那老妈妈之所以没救,是因她媳妇儿喂她吃了青蹩丸,青蹩丸里有藜芦,与师父方子里的人参药性相克,《本经》言明这两种药材最忌同服,再则老妈妈的病本该补气,怎可给散气的青蹩丸?这不是师父的过失,你为何不说?”
方泽芹道:“看那妇人是个孝顺媳妇儿,若让她得知此事,兴许会觉着是自己害了公婆,悔恨之下若自寻短见可不是又添一桩憾事?”
应笑哪儿能想到这些,听他一说,也觉得有理,却还有些不平:“可她吵吵嚷嚷,到处说师父是庸医,万一别人也这么觉着,岂不是冤枉师父了吗?”
方泽芹盯着她看了许久,笑问:“应笑可认为师父是庸医?”
应笑连连摇头:“师父开下的方子可好用了,吉灵社卖的百草还魂汤便是按固命汤的方子来配的,正对这疫病的症状,买药去的都说吃了便好。”
方泽芹愣了一愣,旋即道:“应笑,你记住,瘟疫非寒非暑非风非湿,症状各有不同,常与伤寒风湿相类,实是因疫毒之气内侵所致,这疫气所引发的症状因人而异,不可单一而论。”
应笑乖乖听从教诲,正编写诊籍时,忽听外头喊道:“方大夫,有人要见公孙先生。”
方泽芹闻听,便知是胡东等人来了,让应笑避在屋内,自到院中接待,却见四个小道士已换了身农人装扮,用煤灰将脸庞抹得漆黑,辨不出原貌来,暗自好笑道:这四人倒是机灵,如此一来,也能避过子元真人的耳目。
便充作不识,上前拱手作礼:“在下方泽芹,是公孙先生的朋友,不知四位找他何事?”、
因他昨夜是憋着嗓子装出的假声,四个小道士浑然不察,只当是个斯文书生,向前作了一揖,各自报上名号,严怀准道:“我们是西迁来的难民,因与公孙先生相识,听说他住在此处,特来投奔。”
方泽芹道:“公孙先生不在村里,你们且在此稍候。”将四人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