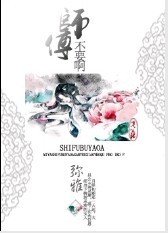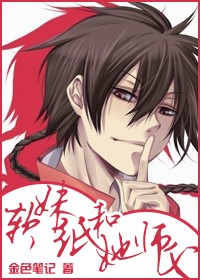师父,床上请-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杨广道:“就在此处尿!”
方泽芹道:“在哪处倒无妨,只是你们这般绑着她,血行不畅,这童便一旦缺了血气,怕是会削弱疗效,以令弟的伤势来看,至少要饮三副,且要趁热服食,积尿也喝不得,何不把那孩子放开,等需要时,便让她解了热尿来用。”
杨广寻思道: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与一名文弱书生,真有变时一刀一个结果了便是!还怕他作甚?
于是爽快答应:“好,放了她也可,但你二人必须留在屋内,不许出门!”
方泽芹道:“一切都听英雄吩咐。”
杨广便让杨飞放开柳应笑,拔去她口里的布团,柳应笑一得自由,立时扑进师父怀中,也不敢说话,只是紧紧抱住他的腿。
方泽芹心里疼惜,把小徒弟抱起来,在她耳边轻声哄道:“应笑乖,好孩子,别怕,有为师陪着,没事了。”
这时,李氏夫人捧了水食衣物前来,杨广便差她去拿盆,李氏夫人听说是接尿用,便就近去院中取来汲水的木桶,又对杨广道:“我还要去照顾老母亲,老爷若见不到我,恐怕会起疑。”
杨广道:“你自去便是,你女儿和这大夫留下来,若你敢多舌,我便先宰了他二人,再送你们全庄老小一发上路!”
李氏一叠声的“不敢”,看向方泽芹,刻意道:“先生,烦请你照顾小女,得蒙厚意,此恩来日必报。”
方泽芹道声“应当的”,待李氏掩门而去,他又对杨广道:“女娃家面皮薄,外人看了怕是尿不出来,不知可否拉竹屏相隔?”
杨广嫌他啰嗦,不耐烦地嚷道:“要隔便隔,麻利些,耽误了我兄弟你可担待不起!”
方泽芹连声称是,将柳应笑领到屋角,放下木桶,拉起竹屏。柳应笑看向木桶,皱眉道:“我不想尿,才不想尿给那人喝!”
方泽芹竖起手指轻“嘘”了声,俯在她耳边窃语:“什么也不用做,应笑只需坐在屏风里等候即可,等为师叫你时再出来,可好?”
柳应笑点了点头,旋即又凝起面孔,一把扯住方泽芹的衣袍,神色有些慌张,她轻声道:“那日下井之前,娘也是这么嘱咐我,我听话的在井下等了许久,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方泽芹一愣,连忙蹲□抱住她,柔声安慰:“放心,为师绝不会丢下应笑,只是稍等片刻,我也不出去,一会儿,只等一会儿便好。”
柳应笑把脸埋在他的颈间蹭了会儿,往后退了小半步,靠墙坐下,双臂环住膝盖,低声说:“应笑等着师父,师父不叫我,我便不离开,谁来叫我也不走。”
方泽芹轻抚她的头,外面传来杨广不耐的喊声:“还没好?悉悉索索的!还要尿多久?”
方泽芹脸色倏然冷沉,道声“这就好了”,提着空桶闪出竹屏,越过杨飞身侧时迅疾出手,食指戳刺锁骨中央和胸骨正中,眨眼间便点住了哑穴与定身穴,杨飞僵硬地维持站姿,既不能动又不能言,只有眼珠子还在骨碌转动,眼神里透出惊异。
杨广压根没留意到方泽芹的小动作,杨飞虽然脑袋清楚,却苦于无法说话,只能频频朝大哥使眼色。
杨广虽然瞧见杨飞在拼命眨眼,却哪能料到他会被一介文士点住穴,只没好气地道:“老三,你眼睛抽筋儿了么?”
正说时,方泽芹身形一晃,已逼至床前,杨雄虽然躺在床上,却看得最为清楚,这般身法岂是普通大夫能有的?当即奋力叫道:“大哥小心!此人有武……”
话没说完就被拂中哑穴,杨广这才有所警觉,他反应倒也快,立时后跃两步,撤出大刀照准方泽芹的面门竖劈下来。方泽芹不闪不避,竖指于头前,拇指中指一开一合,便将刀刃夹定于指间,任杨广如何使力,那刀刃既砍不下也抽不出,恁的是纹丝不动。
方泽芹夹着刀刃往侧方拨开,另一手放下空桶,缓缓朝前探出,杨广立即撒手想要退开,谁知胸前一麻,大刀哐啷落地,身体便如僵木般再也动弹不得。
杨广悚然大骇,睁起圆彪彪一双牛眼不可置信地瞪向方泽芹,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方泽芹不答反问:“你们可知道那竹屏中的女孩儿是什么人?”
杨广道:“不就是那婆娘的女儿!”
方泽芹又问:“你们可还记得在基山脚下所杀的柳姓寡妇?”
柳应笑在竹屏里听见这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里怦怦直跳,她听方泽芹说过娘亲是被贼匪杀害,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原来竟是那日上门借米粮的恶汉。
杨广却道:“什么基山,什么柳姓寡妇?我全不识得!”
方泽芹倒也不恼,还颇能谅解,叹道:“也是啊,手上人命太多,你自然记不得,我便给你提个醒,那柳寡妇看起来面貌丑陋,额生双角,鼻如鹰隼,宛若五六十岁的老婆子,你们杀了她之后,又劫掠财物、纵火烧屋,后在一座废庙中弃了两个大木箱,一箱是衣物,另一箱则是诊籍纸张,可记得了么?”
杨广眼光一闪,面色阴沉下来,冷笑道:“原来是那个歹毒的丑婆子,我等只是上门讨些米粮,她却下毒谋害,老子一气之下就拿她练了刀!如何?你认识那婆子,想替她报仇么?我杨广早做好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准备,如今落在你手里便也认了,是我轻敌大意,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这些事跟我两兄弟无关,放了他俩,要杀要剐,老子随你处置。”
方泽芹拍了两下手,笑道:“好气魄,好胆色,真是有情有义的血性男儿,方某自愧弗如啊。”说着从药箱里取出绷带和金疮药,打湿布巾替杨雄清洗伤口,敷上药膏后以绷带扎紧,摊开手掌覆在他肋下,掌上运气,轻轻往下一按,只听“咔啦”脆响,肋骨在掌压之下竟生生崩断两根。
杨雄登时两眼一翻,疼得晕死过去,杨广面色刷白,叫道:“住手!杀那丑婆子的人是我,与我兄弟无关!”
方泽芹道:“凶手是左撇子,你与老三都是右手持刀,杀人者除了床上躺着的杨雄不会再有别人。”琢磨了会儿,又似自言自语地道,“即便另有他人亦无妨。”
杨广见杨雄口角泛出血沫,急问道:“你!你对他做了什么?”
方泽芹只是在马蹄印上又加送了把暗力,重创其内腑,让能治的血瘀变成致命内伤,他也不理会杨广的质问,取出一个瓷瓶,径自走到桌前,打开酒壶盖子,从瓷瓶里倒出两粒黑色丹丸掺入酒中,提起酒壶轻轻晃动。
待药丹化开之后复又走回杨广身前,捏住他的下颌往上抬起,迫使他仰面朝天地张大嘴巴,接着用壶嘴子压住他的舌面,强灌了一口酒,听到吞咽声才松开手。
杨广气急败坏地喝问:“你给我饮了什么?”
方泽芹淡然道:“不是毒药。”
又以相同的手段灌杨飞喝下酒,不出片刻,两兄弟便站着昏了过去,再解开穴道,他二人便软倒在地。方泽芹将酒壶扔在地下,又将饭菜铺了满桌,放倒凳子,这才走到屋角拉开竹屏,对柳应笑道:“没事了,来。”说着拍拍手张开,做出要抱的姿势。
柳应笑一骨碌爬起身,顺势扑进他怀里,偏头看向瘫倒的杨家兄弟,问道:“师父,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好端端的都倒下了?”她缩在屏风里不敢探头出来看,倒是将两人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方泽芹道:“为师在酒里掺了蒙汗药骗他们喝下,这蒙汗药能让人昏昏入睡,他们喝下酒便睡着了。”
柳应笑问:“是像娘那样睡着了吗?”
方泽芹摇摇头:“他们还能醒过来。”
柳应笑低声道:“可是他们却害得我娘再也醒不来了……”
方泽芹把柳应笑抱起来,说道:“应笑,这三人不仅害死了你娘,还杀了许多无辜之人,官府正在追拿他们,捉到之后无非要公开处斩,为枉死的受害者讨个人命债,你若是想报仇,为师马上就让他们为你娘偿命。”
柳应笑认真地想了想,问道:“是不是我一个人报了仇,别人便报不了?如果官府来做的话,既能给我娘报仇,也能给其他人一个交代?”
方泽芹道:“也可这么说,无论是我做还是官府来做,他们的下场都不会变。”
柳应笑握住方泽芹的手,轻声说:“那……徒儿不要师父来做,交给官府便好了。”她虽不知道方泽芹究竟要怎么报仇,却莫名地生出一种抗拒感。
方泽芹都听小徒弟的,她说不要便不要,于是用麻绳将杨广杨飞二人绑在一处,杨雄只剩下半口气,纵使能醒得过来也无法动弹说话,便懒得管他。
这头忙妥之后,方泽芹抱着柳应笑去找魏进,正巧李氏也在,便将杨家三贼以人质要挟的事据实相告,问到如何制服三贼,只说趁其不备在酒里下了烈性麻药,其他一概不提。
李氏夫人闻言长吐一口气,这才对魏进道:“老爷,对不住了,我怕那三名贼人对小娃娃下杀手,是以不敢告诉你。”
魏进笑道:“夫人是一片好心,何错之有?换做是我也会这么做。”又对方泽芹拱手道,“先生,这回可真是多亏了你,否则我全庄老小性命堪忧!”
方泽芹道:“快别这么说,方某也是为了自保才铤而走险,这三名歹人乃是榜上悬赏的叛党贼首,还请速去报官。”
魏进忙差遣庄客快马飞奔至县里报官,县尉亲率土兵来魏庄押解贼匪,方泽芹一时脱不开身,只得抱着应笑去拜见县尉大人,凡事有问必答,将缘由都仔细交代清楚,待到送县尉离庄时,应笑已窝在他怀里睡着了,小呼噜香得很。
方泽芹与她同床而眠,一觉睡到天大亮,醒来之后便收拾行囊相辞要去,庄主夫妇苦留不住,只得托出两匹布帛、百两花银作为酬谢,李氏夫人又送了些女孩儿家用的挂镜插梳及丝纱小件,方泽芹推不过,只得收下。
经此一事更加深了返乡的念头,离了舒州之后,方泽芹带着小徒弟一路北上,打算回老家探亲。
☆、洛阳01
师徒二人在路上行了许久,来到西京洛阳,城外的田间地头种植大量花卉,绿叶捧簇五彩锦团,枝杈相交,连绵成片,暖风中带着股馥郁的馨香。入城看时,只见民宅沿街成市,宅前翠荫蔽檐,各家窗下都修筑了花台,花坊前更是姹紫嫣红,粉蝶扑扇翅膀在花丛中嬉戏,身穿素雅罗裙的妇人蹲在花盆前修枝剪叶,贩夫走卒亦不乏俊秀之辈。
柳应笑生在山里,这一路行来多是走的乡野小村,何曾见过这么满街花光的坊市,只看得目中生辉、眼花缭乱。她下了马,徒步闲逛长街,停在花坊前探头张望,就见屋内屋外摆满各色盆花,有的如小喇叭,有的花瓣重叠相包,大多都种在盆内,也有些插在水桶里。
方泽芹见她蹲在花盆前不起身,问道:“应笑喜欢花?”
柳应笑轻“嗯”了声,凑近花团深吸一口气,笑着说:“花香又美,看着就喜欢,山里也有许多花,都没这儿的好看。”
剪枝的妇人一听到这话便喜笑颜开,抬头朝柳应笑望去,见小娃娃生得白嫩可爱,心里喜欢,顺手就从桶里拿出一枝桃色的花红蝶送给她,也不肯收钱,只是在应笑水嫩的脸蛋上掐了一把。
方泽芹谢过,将花去了枝干杂叶,簪在小徒弟的发髻旁,柳应笑取出挂镜照了半天,皱起眉头,方泽芹问道:“怎么?不好看么?”
柳应笑指了指发包,抱怨说:“花好看,可是师父梳的头不好看,总是一边高一边低,松松散散的。”
方泽芹抹了把脸,笑道:“是为师手拙,还需再多练几日。”
柳应笑轻抚花瓣,体谅地说道:“不是师父手拙,是手太大太硬了,头发却细而软,能梳成这样,哇,师父真厉害。”说着还拍了下小手。
方泽芹哈哈一笑,转弯抹角,来到一座跨河拱桥前,这处是连接南北坊街的要道,摊贩云集、人潮如流,方泽芹怕小徒弟走丢,便就近在一家客栈里寄存了马匹行李,抱着应笑游览街市,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任她看个过瘾。
正走着,忽见前方人群围聚,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应笑好奇心起,拉着方泽芹挤入人群里,就见前方有块空地,一名青衣少女跪在墙根下,身前横躺着一个后生,这后生身上盖着块白麻布,布上写着四个大字:卖身救兄。
那少女朝着三个方向拜了一拜,哽咽道:“小女子姓石,小字金莲,地下躺的正是小女子的兄长石庭之,去年因爹娘病故,便同兄长来此投奔亲眷,却不知那户人家搬去了哪里,只能流落在这异地,靠兄长卖字画勉强度日,不想我兄长在一个月前病倒,找了三个大夫来治,把过活的钱都给用光了,病却未见好转,反倒越来越重,已自不能开口说话,那济民坊的大夫各个束手无策,小女子只能斗胆向众位好心人求救,若能求得名医救我兄长,小女子愿以身相许,甘为牛马,终生服侍恩人。”
石金莲抬起头来,众人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