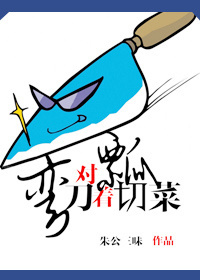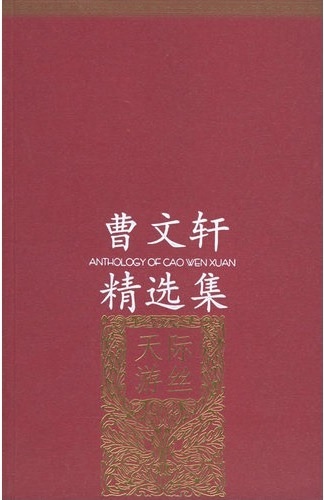曹文轩天瓢-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不久,有人惊喜地叫起来:“天好像下雨了。”
于是许多人仰脸去望天空,或是将手伸出去看看天是否真的下雨。不一会儿,四周都渐渐平息了下来———周边村庄的人似乎都感觉到了雨。
接着,欢呼声此起彼伏。
再接着就是一片安静:所有的人都在凝神注目着这雨的走势与结果。
这天似乎被这一连好几个小时的大火烘得大汗淋漓了,竟下起大雨来,并且越下越来劲。
因这天空布满了厚厚的黑烟与灰烬,这雨竟是黑的。黑汤子。
人们的脸上,是一道道黑色的细流,像是黑色的蚯蚓,用手一撸,便成花脸。
没有一个人躲雨,众人都伫立于雨中,翘首观望那片大火——— 火在雨中挣扎着,起来,趴下,趴下,起来,再趴下。雨像鞭子一般在抽打着火,火在雨中吱吱如耗子一般叫唤着。
火在缩小,在慢慢地矮下去。
雨是黑的。天堂里有一汪墨池漏底了。
花了脸的孩子们在黑雨中奔跑跳跃,一个个像小鬼似的。
天黑了,这黑雨还在下。虚惊一场的人们都回家去了。
可就在油麻地的人安心地在家吃晚饭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黑雨中到处传播开来:刘家桥的刘金扣弟兄几个正在那片后着火的芦苇地里割着芦苇,忽然看到了大火,就拼命往水边跑,而跟着刘金扣去芦苇地玩耍的八岁儿子刘东子却因走到一处玩耍,未能被大人找着被活活烧死了!
第四部分黑雨(5)
深夜,油麻地空前的寂静。
只有老塘边枯草中的唧唧虫声,只有秋风吹过落尽叶子的枝头所发出的沙沙声。
杜元潮不发一声地躺在床上,无法入眠。透过天窗,他望着低矮的秋天的夜空以及稀疏淡漠的星星。他似乎觉得艾绒也没有入睡,只有乖巧地睡在他们二人中间的女儿已经熟睡———熟睡时的女儿几乎是无声的,像一片树叶飘在水上。
杜元潮觉得自己的身体忽冷忽热,好像生病了。
芦荡大火总在他眼前燃烧着,烧成了火山,烧成了火海。
他终于躺不住了,于黑暗中穿上衣服,然后轻轻下床,轻轻走向窗口。当靠近窗帘时,他看到月光将一种他所熟悉的影子淡淡地投照在了窗帘上———那匹永远处于朦胧中的白马驹。他不禁一阵激动,因为这是它第一次如此接近地靠近他。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撩起窗帘将它看个清楚。风从窗隙中吹入,使薄薄的窗帘颤动起来,那白马驹的投影便也跟着颤动起来,像投照在被风吹拂着的水面上的影子。
杜元潮回到了聚精会神地看皮影的童年时代——— 白马驹在窗前走动着,一会儿低着头,仿佛在嗅着地面,一会儿仰着头,望着天空一轮明月。它不时扇动着耳朵,抖动着鬃毛,摇摆着尾巴。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一棵桂树下。
杜元潮觉得映在窗帘上的白马驹比出现在远处的田野与林子里的白马驹更加的优美。
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窗口,用手轻轻撩起窗帘———就在那一刹那间,那匹白马驹像梦一般消失了。
望着空空落落的院子,杜元潮的心中泛起一片惆怅。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预感使他情不自禁地掉头看了一眼身后床上静如秋水的妻子与女儿……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邱子东正独自一人走在通向刘家桥的路上。
他的姑姑家在刘家桥。
一直走到姑姑家的门前,他都未遇到过一个人。
他敲开了姑姑家的门,并将两个已经熟睡的表哥叫醒,然后走进一间里屋,关上了门。
一个多小时后,邱子东趁着浓浓的夜色赶回油麻地。他前脚出门,他的两个表哥后脚就去了还在一片哭泣声中的刘金扣家……
第四部分黑雨(6)
第二天清晨,刚刚醒来的油麻地一如往常,开始了新的一天:清扫庭院与街巷、担水劈柴、生火做饭、将鸡鸭放出笼外、将牛羊赶往田野……
许多孩子还没有洗脸,就在清凉的街巷里奔跑。
今天,邱子东起得比油麻地任何一个人都早。他一直站在院门口,眺望着镇前的那条大路,脸上毫无表情。当他终于看到一条长长的白色的队伍出现在大路的尽头时,向后退了一步,轻轻将院门关上。他仰望苍天,然后闭起双目,用双手上下磨擦着冰凉而瘦削的面颊。
那支队伍像一股水流向油麻地流来。
一个孩子先发现了这支队伍,转身向镇里的人们大声喊:“你们快来看呀!”
接下来,许多人看到了这支队伍。于是油麻地到处响起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宁静的早晨陷入一片喧嚣与不安。
所有人家,男女老少,都纷纷跑出家门,涌到镇前的大桥头,无声地望着这支队伍。
刘家是刘家桥的大姓,刘家桥的居民,十有八九姓刘。而刘金扣一门,又是族中之大族,光刘金扣亲兄弟就有八个。这一族代代兴旺,都是兄弟众多,惟有到了刘金扣这一代,香火清淡,兄弟八个,五人成家,但各家都只生了一趟女儿,就刘金扣一家生了儿子。由老太爷取名为东子,刘家上下,将其视若眼珠。
这一行人,百数以上,皆着白色丧衣。衣,长而松,随风飘飘。前头四位青年男子,抬一口还散发着木头香气的新棺。因棺中死者为八岁小儿,棺材便做得十分的小巧秀气,一头大一头小,头大的一头冲向前方,棺放在四人肩上,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之下,赫然在目。紧跟棺后的是年迈的老太爷,接下去按辈分与亲疏一一排列。老太爷步履蹒跚,拄一根高高的拐杖,身旁各有一个人轻轻搀扶着。队伍中,有一些悲痛欲绝的女人,已无明亮的哭泣之声,沙哑,接近无声,身体显得虚弱不堪,或是扶助,或是被另外的虽也悲痛但还不至于悲痛得身如抽丝的女人无声地搀扶着。
油麻地的田野因为这支白色的队伍而显得天地明亮,草木清新。
走近油麻地时,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显得更加缓慢,仿佛在故意煎熬油麻地人的心。
队伍走上了镇前河上大桥,于是一行白色的影子倒映在早晨平静而淡漠的水面上,惊走了几只觅食的鸭子与鹅。
这支队伍几乎是无声的,几位女人的低低的沙哑哀鸣,更将山一般的沉重压到了油麻地人的心上。
陌生的脚步声叩击着油麻地的桥梁与被夜露打湿的土路。
与所有的油麻地人都翘首观望相反,所有的刘家桥人都低着头,仿佛那八岁孩子的魂灵被大地吸去了。
油麻地的人,不分男女老少,皆被一种凝重的气氛所感染,无一人再说话,甚至连狗都不再吠叫,苍天之下,就只有一个沉寂到几近死亡的世界。
这是一支被精心组织的队伍。
这支队伍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鲁莽与疯狂,没做一点点狂暴的动作,而是平静地很有秩序地进入了油麻地镇。他们踏上了油麻地镇那条长长的由古老的大青砖铺成的街面。
所有的铺面都开着门,但他们目不斜视,目光里只有脚下这条被脚磨亮了的街道。
油麻地的人分站在街的两侧观望着。
范瞎子站在巷口,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二傻子出人意料的安静,腰间那支一年四季不分昼夜昂举的枪也都垂挂在裤裆里。
队伍从街的这头游行到街的那头,再从街的那头游行到街的这头,然后走向镇委会。
镇委会大门紧闭。
这支队伍就长时间地站在镇委会的大门口。
刘家老太爷有点儿站不住了,双腿颤抖,两个年轻人立即将他架住。他用手颤颤巍巍地指着那块镇委会的牌子,于是,从队伍里冲出来两个年轻人,将镇委会的牌子猛地摘下,砸在了地上。牌子裂缝了,但未断折,于是又有两个年轻人冲出来,将牌子捡起,一人握住牌子的一头,将牌子横在空中,向一棵大树冲去,就听见咔吧一声,被大树拦腰折断,并哗啦啦震下无数枯叶。他们将断折的牌子愤然掼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了几脚,转而冲着紧闭的镇委会大门大叫: “杜元潮,站出来!”
队伍怒吼了:“杜元潮,站出来!”
声音震得镇委会的屋瓦嗡嗡作响。
杜元潮当然不会站出来。不是因为胆小,而是他不能让油麻地的人看到他可能被这群发了疯的人肆意糟蹋。他心里非常清楚,此刻他一旦出现,刘家的人就会蜂拥而上,揪他衣领,扯破他的衣服,扇他的耳光,往他脸上吐唾沫,在他脸上抓下血痕,对他推搡谩骂,将他那副每时每刻都很在意都很讲究、一丝不苟的形象彻底毁掉。于是,他在听到了风声后,没作丝毫反对,就接受了朱瘸子朱荻洼的建议,上了一只由朱荻洼摇来的乌篷船,进了苍苍茫茫的芦苇荡。
那支队伍的怒吼声是无效的,于是一群人合力撞开了镇委会的大门,冲进镇委会,将挂在镇委会墙上的一面面锦旗统统扯下,或撕成烂片,或踩在脚下。办公桌一张张被推倒,电话机被扔出窗外,几只暖水瓶被砸得粉碎,周秃子的算盘被掼在墙上散了架,算珠滚了一地……男女老少七手八脚,直将镇委会打得片甲不留。
油麻地的人非常恼火,但却憋住气没有出来阻挡,因为他们深知闹丧队伍的穷凶极恶,更何况是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更何况这支队伍里有那么多经不起任何折腾的老人,又更何况他们是刘家桥的人———刘家桥人的野蛮是远近闻名的。
收拾完镇委会,四个抬棺的人抬着棺材整齐划一地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于是那支本来已经散乱了的队伍又整装待发了。不一会儿,他们开始向镇后杜元潮家挺进,刚才还在号叫的队伍,又变得哑默起来。
几个油麻地的人抢在队伍的前头,向杜元潮家跑去。
今天一早,采芹就从枫桥赶到油麻地。此刻,她正帮着艾绒拾掇一些值钱的东西准备领艾绒和女儿到她家躲避几天。听到报信,她一手拉着颤抖不已的艾绒,一手抱了惊恐的琵琶,说:“快走!”艾绒看了一眼屋子,只好跟着采芹急匆匆地走进了屋后的树林,一路哭着,走上了通往枫桥的路。
这支白色的队伍,不一会儿就来到杜元潮家门前。
他们高叫着:“杜元潮出来!”见毫无反应,就开始大骂:“狗日的杜元潮,你除非藏进逼里!”“藏进逼里也要将你抠出来!”……不堪入耳。一些年轻女人特别是一些女孩儿,或轻轻地或严严地用手捂住了耳朵。
刘东子的母亲蓬头垢面,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双目紧闭,用双手拍打着地面,用哭得已经不能发声的喉咙哭泣起来,随即,所有的女人都跟着哭泣起来。其中一些,在此之前也只是陪着哭哭而已,还有很大的潜力与余地,此时都亮开了喉咙,大声号啕起来。一时间,这哭声此起彼伏,犹如潮起潮落,汹涌澎湃。一些孩子的哭声与老人的哭声也加入其中,使这场撼天动地的大哭泣有了丰富的声部与音色,从而也更加催人泪下。
刘东子的母亲忽然翻着白眼,口吐白沫,抽搐着晕倒在地。
于是,几个有经验的女人就蹲下来,用尖尖的指甲死死掐住她的人中,直到她缓过气来。她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有气无力地张合着干焦的嘴唇,靠近她的几个女人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要我家东子……”
一个年轻人顺手捡起一块砖头,向杜元潮家的窗子砸去,玻璃立即被砸碎。这一动作,犹如一声全面出击的信号,只见刘家老老少少一起向房子扑将过来,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毁灭行动。一些人冲进屋里,见被子就撕,见锅碗就砸,见凳子就摔,见衣柜就推,见水壶就踢,不一会儿工夫就将屋内搞得一片狼藉。没有能够挤进屋里的,见篱笆就扯,见树木就砍,见庄稼就拔,见猪羊就赶,见菜地就踩,不一会儿工夫,就将房前房后搞得一片稀巴烂。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举起一块石头,冲向院门口的一只装满水的大水缸,大叫了一声“狗日的水缸”,石头飞出,水缸顿时瓦解,水哗啦流了一地。怕湿了脚的便向后躲去,撞倒了后面的人,结果撞倒了一片。
油麻地的人只能在一旁看着。
刘家的人屋里屋外地来回奔跑着,寻觅着还没有被损坏的东西。一个人从瓦砾中发现还有一只碗没有被砸碎,便将它捡起,猛地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