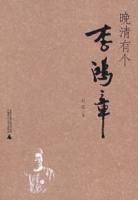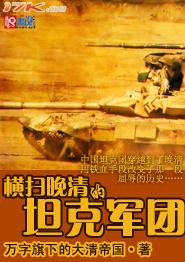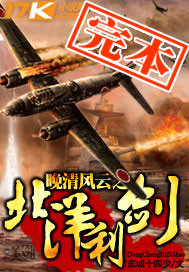亲历晚清45年-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这当口,有人进来传话,说总督召见。总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访时那样友好,看起来似乎脸上有一团阴云。见面的寒暄过后,他问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么。我马上讲了三点。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7 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张荫桓 于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和谈公使去探询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见个面,我把自己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连同我为此书写的绪言,派人送给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读一读,并问我是否可以登门拜访。他给了答复,约定2月28日见面。谈话过程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⑴来于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⑵来于她的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⑶来于她的人口无法增多这种现状,这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就像他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接着我提出了中国扭转颓势的办法:⑴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⑵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⑶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⑷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对此,他的回应是:“俄国是一个让其它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认为英国是最可信赖的。我指出,与所有强势国家结盟是致命的错误。这位和谈公使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⑵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毫无用处;⑶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我的影响力;⑷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⑸铁路会使中国受益非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⑹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的;⑺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⑻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⑼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很高兴见识见识(于是我把拟定的方案呈给他,见下文);⑽对于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赞同。为你创发的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谢,但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当我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供转圜时,他回答:⑾中国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⑿在国外,本人受到了各国政府优厚的接待,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惭愧得很。当我提到应大力诱导改革时,他说:⒀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两点:⑴我把日本进步的原因归于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⑵我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富强的途径。但对于立即实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在同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讨论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8 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访了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看到书后,他自告奋勇要为我写一篇序。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想到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谈话中,他提到了由于民众的贫困,不能筹集更多的税款或者发行更多的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没有把任何税款留在自己手里,同时他强调说,张非常专制,会把当铺、盐商和其它人的积蓄劫夺得一干二净。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上书委员会(图)
1 上书委员会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结果成了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博士、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还有我。我们被责成起草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拟定了一份很长的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委员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2 对基督徒的迫害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会上所做的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被事实证明是太正确了。1892年,在芜湖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传教士的动乱,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通过在的报纸上——日报和周报同时——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响人们,但长江流域的迫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1893年,两位瑞士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⑷满族人无足轻重;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