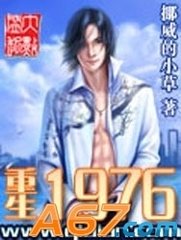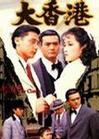生逢1966-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地主。”小魏说。
“我妈妈十多岁就离开家庭自己生活了,她一直在上海生活,不会成为地主的。董同志知道。”瑞平没有称呼董品章为“爷叔”。
“瑞平同学,”董品章也没有叫他“弟弟”。“经过我们调查,你的父亲陈宝栋在1943年到1949年这七年中,每年都在秋收的季节,曾经受姓陈的本家委托到乡下收取租米。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那个本家我们已经去找过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陈宝栋并不是单独一人下去的,当年穷人受了灾害,自己也吃不饱,哪来的租米。你爸爸收租的船上,还有带枪的人。43和44年,那些带枪的人全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保丁!”那个小魏显然感到瑞平很糊涂,“汉奸武装逼租,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瑞平的眼前一黑,他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实。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在萧山弯弯曲曲的水道上,爸爸手中捧着帐本还有算盘,面目狰狞。爸爸的身后,站立着一个像刁小三一样的保丁,斜背着匣子炮。而岸上,是那些苦难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和饥饿的孩子。在萧山老家的院子里,农民正在汗流浃背往里面挑谷子。爸爸就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拿着一箩筹子,每一担发一根。还要催背谷子的人快点。
“政策是很明白的。农村划分成份的时候,收租子帐房是地主的重要的狗腿子,也作地主处理。地主和资本家不一样,地主是敌我矛盾。邵玉清是地主家属,也是地主成份。” 董品章解释说,他的推理是很明白的,有严密的逻辑性,“你们一家土改的时候正在上海,应当作为逃亡地主算。”
陈瑞平的眼眶中满是眼泪。他现在不仅是反革命的儿子,还是地主的狗崽子!
“陈瑞平同学,现在是革命路线考验你的时候了。” 董品章说,“68中是一所很讲阶级路线的学校,全市都很有名的。你陈瑞平也是一个好学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红卫兵。表现一贯很好。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发批判漏网地主陈宝栋和邵玉清,肃清他们的反动流毒!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工人阶级的愿望的。”
生逢1966 11(2)
瑞平是在惶惶惑惑之中听完了董品章的话的。爷叔现在是造反队的头头。这就等于是组织说话了。他垂下了头,说:“我愿意。”
“那么,今天下午三时,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批判,希望你能像一个红卫兵一样参加阶级斗争。”
唐师傅也说:“我虽然到68中不久,但是陈瑞平同学的表现我是知道的。请工厂的战友放心,我们在上层建筑的工人弟兄一定能配合好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唐师傅是一个钢铁工人,脸膛是被炉火烤红的,离开了炉火,脸庞也还是红的。唐师傅对瑞平说:“你交给组织的红卫兵申请报告我看到了,我看你的表现还不错,只要今天能站稳立场,我们一定能考虑你的报告。”
在爷叔和小魏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瑞平赶紧跟上几步,对爷叔说:“你们还要斗三伯伯吗?就是那个上海的本家陈树衡?”
小魏就有一点不高兴:“这是一回事吗?”
“不会,我们是有政策的。你们的那个本家,他的真实身份是工商地主,最大收入来自上海的建筑行和材料行。况且在土改中能主动交代,将土地交给政府。他年纪已经八十一岁了。我们将案卷移交了,本单位的造反派没有要求斗争。”爷叔说。
原来是这样!
红卫兵团的办公室正在隔壁。小木克双手叉在口袋里,已经听了好久了。工厂的人一走,他就喊瑞平进去。他将门关好了,对他说:“瑞平,你这回应该积极进行斗争。一定要出席批斗会。”
“我也是想去参加的。”
“你还要好好进行斗争,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妈妈被批斗是大势所趋,根本没有机会翻身。为什么不斗一下呢?从她的那个角度,你斗争不斗争全一样。从你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参加了斗争,你就表了一个革命的态度,你就能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前途。你不去斗争,你妈妈一样也要被打倒,也要被斗争,所以你还是去斗争的好。”
陈瑞平感到受了很大的污辱,是对自己的思想动机的污辱。于是对小木克说:“我是真想要革命,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清白。”
“难道这还有什么两样吗?”小木克很耐心地开导,“就算你是真心革命,你也需要揭发你的母亲,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你的革命。你革命了,你就清白了。”
瑞平急急地往家走。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家,这就是一个逃亡地主的家,这就是一个沾满劳动人民血泪的家。他要批判自己的妈妈,一个漏网的地主婆。他不知道过去,他只知道今天。他没有更多的材料,他只能观察自己的家,在家中寻找罪证。这是一个家,这里的一切全部有女主人的手印和指纹,他需要从这里开始揭发和批判。
生逢1966 11(3)
或许,这个煤气灶台就是罪证。这个地主婆在这个灶台上曾经烧了很多的好菜,她喜欢用大些的锅做菜,做完了就按照乡下的习惯四处分送。妈妈很善于腐蚀群众。还是在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初头上,全弄堂都喊吃不饱。所有的家庭妇女尽管起得再早,也不能将自己的篮子填满。瑞平家按户计是小户,按人头计是三人。陈家比较的有钱。但是钱是一点没有用的,有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是以后的事情。每天阿姨买菜归来,吹口气能把篮子吹飘起来。那个冬天,冷得很,上海难得下了雪不化。风吹的像刀子一样,阿姨一连走了三个菜场,无非是卷不了心的卷心菜和细得像手指的胡萝卜,还有不要票的豆腐渣。这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瑞平见到很多同学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饥饿。有人用标准粉加上半块鲜酵母再加上半粒糖精,拌成糊,放上数片菜皮,装满一个腰子饭盒,蒸出又酸又僵的“发糕”。他见到食堂里很多同学都带有一只装过药片的棕色小瓶,里面是烤焦的葱花和盐,这些盐全是在烧完菜之后吸干那些可怜的油水用的。葱花盐每天用来拌泡饭吃,可以省了一分钱的酱菜。面疙瘩是经常的佳肴,省油省菜,还有一时的涨饱感。全班全校都是一副饿相,夹杂着山芋粉的馒头到手两口就下了肚子,这一些孩子就尽量在口中含着最后一口馒头,用不断分泌的唾液滋润着。回家的时候瑞平眼睛依然饿得发绿,打开菜橱每一只碗都看上一看,如果碗能吃也会吞下去。
石库门的习惯,是非常重视自己有一个“乡下”,石库门的女人经常要到乡下去。即使她们的乡下亲戚穷得叮当响,一年四季写信哭穷,她们也要炫耀。绍兴老太从乡下没有东西带出来,就砍了一捆苋菜梗,她就一家一家送着,然后推广她的“霉菜梗”经,一条弄堂几乎全被菜梗“霉制”过程中的臭气熏倒。老太没有牙齿的扁扁的嘴,有滋有味吮吸着深绿的汁水。上海石库门的乡土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妈妈是萧山人,是萧山特产的自觉推广者。她经常到萧山去,因为她想念江边沙地。灾害年月,妈妈又到萧山去了,这回是因为饥饿。
那时大约有七个月没有尝过鸡的味道了,妈妈回了萧山就将著名的萧山鸡带了两只到上海,这种鸡原本就是大种鸡,预先又经过阉割,这鸡就只会长肉了。十多斤的一只鸡,临时养在厨房中的时候,伸起头颈能啄到八仙桌上的饭粒。妈妈是在沙地上化了三十元的高价买来的。当年的三十元,足可以买一幅齐白石的公鸡。妈妈先是在锅子里熬“虾油露”,这是糟油加上花椒加上黄酒的混浊液体,她将这些液体倒进甏中,然后将天目山的扁尖和舟山的虾皮扔了不少进去。妈妈先是用大号钢精锅煮熟了鸡,然后一片片斩开,泡在虾油露中。他和阿姨两个人手忙脚乱,封起整整两个甏。三天之后封甏的牛皮纸湿了,瑞平闻到了家中一股特别的咸腥香味。选一个星期天,妈妈就把鸡拿出来,爸爸和瑞平得到各得到了一条粗硕无比的鸡腿,妈妈就走上三楼,用竹竿将一个小篮子渡到对窗,里面有满满一碗虾油鸡。蓓蓓欢跳着接过篮子,好婆随即将一听市场上紧缺的香港精制油渡了回来。
生逢1966 11(4)
妈妈回到楼下,将家中几乎所有的碗放在桌子上。两个甏里的鸡全部清空了,妈妈就一家一家去送,一直送到了绍兴老太门口,鸡刚刚送完。半条小弄堂,一时全都弥漫着虾油露的奇异香味。
最后,妈妈将一片胸脯肉夹给了绍兴阿姨,自己就吃四个翅膀。
“你为什么将所有的鸡送人呢?既然要送人,也不要到萧山去了。”爸爸说。
妈妈说:“老六,这当然是做人的道理。现在弄堂里所有的人家全在挨饿,全部都在买一分一天的菜皮,用豆腐渣糊口。你们家中有这样鲜的好东西,弄堂里瞒不住的,人家自然会谗,还不如送走。”
爸爸显然有点不满,说:“全家一起回趟萧山就好了。”
“你道萧山四邻在吃什么?西瓜皮全部洗洗干净腌了当菜吃!吃鸡?你让萧山的七弟如何做人?”
“那你兴师动众做虾油鸡为什么?”
“不为什么。十年没有做了,过过念头。”
“也不值得这样送,你不是不知道。家里真正有事,靠的还是自己。”
“那不过是一种应酬。我也没有想过要靠别人,我说过求人不如求己。”
妈妈其实开始并没有想得周全,在沙地上见到那两只鸡在稀疏的茄子地里捉虫,就有买下来的冲动。将鸡背到上海,才想到全家吃这样两只鸡似乎有一点过分。将这样肥厚的鸡肉白白送给四邻,她也有一点心疼。不过这样总比以后在弄堂里孤立要好。人们可以忍受饥饿,却不能忍受在自己饥饿的时候有人不饥饿。妈妈在这点上比爸爸多想了一番。
家中最后享用的是烧菜有了最鲜的鸡汤,鸡肫上面黄黄的厚皮烧焦之后可以用来治疗积食,有了一碗鸡油可以在寡淡的汤中点上几点油花。鸡肉已经吃完了,但是两罐鸡汤还在,鸡汤在餐桌上存在了三个星期,在干瘪的胡萝卜中,在鸡毛菜的黄叶中,在菜边皮中生存。
妈妈后来享受了半条弄堂一个星期的“谢谢”。然后享受了一个星期在整条弄堂被人说“人家有钱”的酸酸的风光。妈妈觉得石库门弄堂很有点“两面派”。而在这样弄堂中要算计到很精致地做人,多少年她还没有学会。就是这两只鸡,让那个绍兴老太每天站在门口,用一种近乎仇恨的眼光看着妈妈。她完全知道霉菜梗的味道总是不如鸡的。
他走上三楼,在正房,南窗下是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也是罪证。
妈妈当年是很喜欢自己用机器做衣服的,特别是为瑞平做衣服。后来就为全篮球队的队员做了茄克衫和马桶包。68中不是一所贵族中学,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余国祯校长带头穿有补丁的衣服。学校中将毛主席在抗大讲课的照片画成大幅招贴。毛主席裤子上的两块补丁是很显眼的。全校几乎没有人穿新衣服。妈妈很在意儿子的表现。儿子正在飞速发育年代,衣服永远显得短小。瑞平是一个萧山人所说的“长子”,本来妈妈要将全家人的布票全部给瑞平做衣服,后来一想,还是给爸爸做了。爸爸的身高在一米七九,在老派的男人中间,人还算是长的。爸爸将裤子穿到了七成新,妈妈就给爸爸又做了新的,这条旧的,就放在缝纫机上,妈妈从箱子里找出一些零头布。缝纫机突突响个不停,瑞平的屁股上就画满了年轮,膝盖地方也有了一对“眼镜”。儿子在中学里没有穿过新裤子。瑞平穿有补丁的裤子。一旦补丁破了,妈妈就将补丁拆了,这裤子的膝盖和屁股还是没有破,只是前后有三个深深的印子。瑞平后来人长高了,妈妈就将裤子接上一截。瑞平永远有好裤子穿,但是,永远看不出他穿的裤子比人家的好。妈妈给瑞平做的茄克衫,故意用旧的衣服改做,样子很好看,上面却有补丁。
生逢1966 11(5)
妈妈的缝纫机还给瑞平做了五一块抹布,让瑞平送到学校去。让每一个学生早上都能自己擦一擦桌子。不料因为蔡小妹每天到得最早。她用一团回丝,将每人的课桌全部擦个干净。瑞平妈妈可以说是白辛苦。全班男生集体讽刺瑞平“假积极”。或者是说,你想入团想昏了头。小妹出身在工人家庭,小妹在家中就洗衣服擦地板,为同学做些事情是很自然的。而瑞平平常连一块手绢也不洗,妈妈为瑞平设计的理想主义“积极”就有点做作了。
瑞平打开妈妈的箱子,箱子里只有抄家余下些很简陋的东西,很引人注意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还新的旗袍,颜色是很深很艳丽的紫红,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