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慷永锏闹拔袷俏郎⑶矣肱接讶范斯叵怠4巳吮群嘣蟛涣思杆辏舜κ氯春芾狭贰�
小组长肖云,山东济南人,比亨元年长十岁,解放前被国民党拉夫当勤务兵,该部向我军投诚后,他也反了正,授衔时获得最低军衔准尉,因有"政历"问题而未入党。
进东华大学法学院的,除一部分普通高中毕业生外,大多数是已经工作过多年的调干生。
其中甚至有的人在法院院长的位置上保送入学的。因为注重资历而不重视学历,亨元在大学生活的四年中无一官半职。比起严谨的苏高中,大学生活松散得多了,基本上没有课外作业,无需到教室去上夜自修,晚上自由支配。
生活上,每月交12元5角钱伙食费,主食有米饭和馒头可任意挑选,馒头虽无馅,酵发得很好,可敞开肚皮吃,不计量,小菜量多质好。
后来实行了食堂制,12元5角分解到每天,只有4角钱饭菜票,再加粮食定量,不仅伙食大大下降,还经常闹";饥荒";。
使他感到惬意的是上厕所比高中时方便得多,就在寝室对过有个洗手间,除洗刷衣服外还有瓷砖铺设的小便池和每人隔开的大便间,这样,亨元无需等到夜深人静去上厕所。
任何时候,只要有便意即可一个人关上小间门悠闲自得地排便,而且它是个单人世界,没有人干扰,亨元经常在那里一边登坑(吴语),一边欣赏胸前悬挂的校徽,幻想着毕业后的锦绣前程。
同学美行,文娱活跃分子,向部队借了几十套橄榄帽军服,在班级里组织了一次化装舞会。所跳的是简易的集体舞。亨元在高中二年级时就参加过这类舞会。
当时扮的是白衣白帽的医生,与女同学手拉着手,面对着面跳舞,心情异常激动,也很紧张。从读高中起,他极少有机会与青年女性接触。客观上,班级里女同学少,到了"东大",更是清一式的和尚班。
此外,当时的社会风气男女界限分明,年纪轻轻即好色,人所不齿。主观上,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他都属于低档次的一类:在以智力排名次的省中,因学习成绩不佳而被入";另册";。
在调干生吃香的法学院,又因非党非团受人歧视。唯有在大家化了装的班级和班级的聚会上,亨元才有机会平等地与别班的女同学一起跳舞,怎不令他激动和紧张?
美行以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舞会赢得大家的好感。此人油腔滑调,据其自我介绍,与初中某女同学已有若干年的恋爱史,且已发生过性关系,还无耻地详述下流情节。
不久,学校里贴出许多大字报,揭发了他的种种流氓行径,大字报把美行的“美”改为“丑”,于是他的姓名变成丑行,并在上面打了叉叉。不久此人离开了学校,听说,被处劳动教养。
一天,凤老爷,大姑妈和三姑妈到学校里看亨元。他们对学校的环境赞不绝口。三姑母对内侄说:
"老太太(指其婆)就要过八十大寿了,他们在新雅饭店安排了桌次,到那天一起来凑凑热闹。"凤老爷持相反意见:"走不出不要勉强。"
亨元从小就听说三姑父在上海当法官,姑母当书记官。他们结婚的时候乘的是有四个保镖分站在踏脚板上的汽车。
亨元还不到三岁,父母领着到上海吃喜酒,彼时情景在他不健全的头脑里已毫无踪影,但阿判和纳香人能说得历历在目。
据说,他一到上海最感兴趣的是乘汽车,硬要大人把自己装进玩具汽车内。还有一个恶习是不肯坐抽水马桶,要家里坐惯的小马桶,否则不肯大便。
此后亨元虽然没有再来过上海,但对有一个做过法官的亲戚在上海是很得意的。这种潜意识是促使他报考法律学院的重要因素。既然有这种机会去看自己所敬慕的姑父母,岂能放过。
此外,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表妹,比亨元小五、六岁。童年时代曾到同里来过。时隔七、八年,想来已长成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了。他很想见一见上海表妹,美味佳肴,倒并不追求。
老太太生日那天,他向学校请了半天假。吃过午饭就走到江苏路月村三姑母家中。这是由几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构成的西式公寓。住姑父母及其三子一女和老太太,还有一位掌管全家经济大权的老姑娘。
三姑父作为敌伪时期的法官,抗战胜利后已经失势,但尚未倒霉;解放后变成无业人员了。经济来源全靠美国当律师的弟弟定期供给和妹妹在某化工厂当高级工程师的收入。
亨元眼见自己的偶象一付落拓无为的样子,心里无比辛酸。几位表弟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状态,小表妹从姑母房里出来确实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仔细一看面貌,并不如自己想象那么美妙。
亨元和三姑父等一行六人乘有轨电车赶到南京东路新雅饭店。买车票时,姑父母的仔细计算说明其经济拮据状态。
来到老太祝寿的包间,主宾基本就座。凤老爷见三姑母还带个吃白食的来,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凑过来质问亨元:"你不在学校里吃,伙食费能退出吗?"
那时还没有实行食堂制,吃大锅饭。亨元答:"退不出"凤老爷话中带刺地说:"这太可惜了!"亨元对凤老爷的话很反感,心里想:"即使吃白食,也不是吃你的,何必这么肉痛"从此不搭理这位姑父。
开宴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表妹,她举杯他也举杯;她挟菜他也挟菜。觉得表妹吃饭的样子文雅极了,而且他也感到表妹不断地在注视着自己,梅老爷给他带来的不快一扫而光。
未及终席,他即以晚上还要温习功课为由礼貌地告退,老太等人怕他不识回家途径,令二表弟陪同一起回去(江苏路和东大相距甚近),他买了两张21路中山公园方向的车票,与喋喋不休的二表弟一起踏上归途。
事后,三姑母转告内侄:老太和老姑娘对他的印象不差,认为是一个朴质无华的青年。可是不久又传来消息:三姑父涉及非法从事"地下"工厂,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刑。
对社会关系极为敏感的法律学院是不允许学生与这些亲戚来往的,亨元不得不与三姑母等断绝了联系。
第十回
关帝庙中弄刀品行计入另册触规小题大做泄愤是非颠倒
亨元在经济上很不宽裕,绝大多数同学都获得校方十元以上的助学金补贴,而他得到的是三元钱的丁等助学金。
艾生家庭出身工商地主,其自吹小时候几个丫头陪他一床睡觉。现在仍是一付少爷派头,手腕上套着手表,食堂用餐经常吃甲菜。他尚且能得高额助学金,为什么劳动人民出身的亨元不能得到呢?
他愤忿不平地前往学生科反映意见。皮科长听完陈述,鄙夷不屑地回答:"你家里有父亲挣工资,每月九十多元,艾生家里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发放助学金是按平均生活水平定的,不会错。"
亨元搬出阶级路线一套理论,一条腿在战争中负伤、满身骨头架子的皮科长反唇相讥"你父亲当过旧邮局局长,能说是工人阶级出身吗?"
亨元不服气,要求取出他和猪猡头的档案来对比,皮科长神秘兮兮地急忙把摊在办公桌上的各种材料锁入保险柜内,责令亨元立即离开学生科,说:"我们这里的材料都是保密的,岂能让一个普通学生随便看"。
亨元下不了台,与皮科长争吵起来,惊动了隔壁人事处的女处长,出来为科长帮腔,批评亨元无理取闹。亨元望着这位中年女性冷峻的目光,不寒而溧,只得灰溜溜地跑了。
班级党支部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从此,"大闹学生科"的罪名压得他永远不得翻身,也影响到他日后的毕业分配。
这一年暑假回到家里,发现家门前的藕河浜已经填平,变成一条宽阔的马路,观莲小筑和藕河街变得有名无实。
阿判以兴奋的心情叙述大跃进带来的奇迹。他对小高炉能出钢,一亩田能产万斤粮深信不疑,特别是以供给制为标志的共产主义甚感兴趣。如果按每人的平均消费水平发放各项生活必需品,这个仅靠阿判一人收入维持生计的六口之家肯定不会吃亏。
眼下,家里连电灯也装不起,从同里搬到震泽带来的一只旧电表,放在门口的壁橱里,没有多久就被偷掉了。买一只要化四、五十元钱,原来准备的接装电灯计划作废。
家里没有一台收音机以及任何家用电器,当然,有了也使用不上。缝纫机、手表、皮鞋、呢料之类日常耐用消费品也不具备,唯一的计时工具是摆在长条桌上的一只三十年代的座钟,常常停摆,修过多次。
在阿判和纳香人结婚初期经济条件是不错的。自行车,手表,金戒指,男女双方都有,而且置备了全套深漆硬木家俱。由于阿判缺乏算计,"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人生观,再加一个个孩子的出生,增添了负担。
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件件值钱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阿判手上戴的表在南京三等邮局长培训时,酒席上与他人换了怀表,到同里上任后,一次赌博又把怀表输掉了,幸得邮局有挂钟不致误时。
后来家庭与邮局分开,只得到苏州衙门场把放在那里包括座钟在内的家具全部搬来。
亨元的暑假过得很无聊,纳香人有干不完的家务,而他一件也插不上手。没有自来水,藕河浜又填平了,洗衣服、洗菜要到六十多公尺以外的戏院门前的河浜去,饮用水也从那边挑。每天请挑水工人挑两次水付酬一角,水装在容积一百公升的水缸内;来之不易;节约使用。
两个弟弟都已能同亨元玩耍,围墙从一个乡村教师那里学会了拉二胡,其水平大大超过乃兄。两兄弟分别以笛子和胡琴合奏,初时总是弟弟约哥哥,后来哥哥约弟弟,围墙还要搭架子,说亨元音律不准。
他曾与乡村教师一起上南京报考音乐学校,双双落榜,两人仍勤奋练琴不已。围墙的拿手曲调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演奏时左手在琴把上上下移动,手指在琴弦上灵敏地按捺出美妙的音符;右手均匀地操弄弓弦,必要时还能象弹琵琶那样拨动琴弦。
亨元也想在笛子上下些功夫,买了一本讲如何吹好笛子的书,按图索骥学节奏感强烈的吐音。"脱苦脱苦"反复练习无数次,还是不能象行家那样把《我是一个兵》这个曲子吹好。
陈三在小学念书,成绩优良。回到家里还不时用震泽普通话读课文。有一次两位兄长只听得小兄弟不断地在说:"买子好,买个糕,买子可以做面包,买个可以烧,还可以变三子蒸烧卖。"
不懂其意,要陈三拿出课本来看,原来是:"麦子好,麦杆高,麦子可以做面包,麦杆可以烧,还可以编扇子做草帽。"陈三的语文老师普通话说不好,就这么教导学生。小兄弟为人懦弱,经常给强横同学欺侮,有时家里拿了点心去孝敬这些小大亨,甚至午饭中把剩下的一些好小菜拣一、二块包在废纸内带到学校去。遇到这种情况,两个哥哥总要耻笑他一番。有时要陈三讲出谁是小大亨?以便去教训教训他,陈三坚不吐实。
围墙读书不够努力,拉胡琴之外,打扑克、赌洋片样样精通,其身高力大,在同龄少年中可以拜大王,身后的小喽罗不少。
有一次在家玩弄纳香人的绒线针,竟然拿它来通自己的鼻孔,不慎直扎鼻根,鲜红的血如喷泉般流出来,急送医院抢救,性命无虞,但从此鼻音更重.一直象患重伤风似的。
纳香人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仅七十市斤。哮喘老病,晚上咳呛不止,冬天更甚,怕影响丈夫和孩子们睡眠,强忍不咳。
身体和精神略好时能看看连环图画和通俗小说,还用毛笔给远在广西工作的哈哈写信。字写得十分工整,言简情深,一片慈母之心,看了催人泪下。
她受儿女影响,也是越剧迷,偶而有剧团到震泽演出,大家象过节日一样的高兴。到吴江去看瓜子,也免不了要到演越剧的戏院去过瘾。这是她最大的精神享受,回来总要把剧情仔细回味一番,甚至与家里几个孩子挂起钩来。
有一出戏描写三个儿子对母亲的不同态度:大儿子怕老婆,不敢供养老娘;二儿子吝啬对母亲不孝;三儿子虽穷却挑起赡养的重担,最后做了状元。纳香人认为陈三象剧中的小儿子,就学着剧中老妇的口吻称呼陈三:"三元,三元,你在哪儿?"
读大学的第二个暑假过后,亨元按学校的通知,直接从家里出发到嘉定徐行灯塔大队报到。学校在徐行公社设立了大队部,由年级党总支领导挂帅,年级办公室主任为大队长。中队部设在灯塔大队,迟波是中队负责人。
亨元由震泽到苏州,再乘火车到昆山,乘汽车到徐行。在长途汽车上,亨元望着公路两旁绿树成荫的田野,头脑里浮现出《桃花源记》里的宁静世界。这安逸,闲散的农村,与喧闹的大上海是何等强烈的反差。亨元当时很愿意过陶渊明式的生活。
到了灯塔大队,见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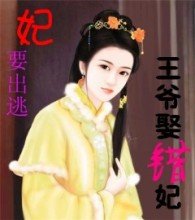


![[裴晓庆] 下雪的故事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