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全家迁入后,原来的草棚准备大儿子将来办婚事用,里面有新添置的家具和床上用品。钟成慷慨让出,给亨元的姐夫作暂时休憩之处。
午饭后,瓜子夫妇回盛泽去了,(林茹已调任盛泽镇党委一把手)哈哈和陈三轮流在医院陪侍父亲,亨元还要到建新大队应付。
不久,围墙在北京闻讯后也请了一个月的长假来枫林探望父亲。亨元的家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那时,恰好吴江邮电局长乘小吉普来探望阿判,在他们回去时,哈哈搭车回震泽。不料途遇大暴雨,吉普车的雨蓬不严实,淋了一身湿,回吴江生了一场重感冒。
陈三有了围墙作伴,两人谈谈说说不觉得寂寞。围墙食欲旺盛,嫂子操持的伙食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旷日持久耽在信息闭塞、穷乡僻壤的小镇,对大城市、大机关来的青年也很不习惯。
终于有一天围墙发出了怨言:"这样的日子还要耽多久?"亨元觉察后立即采取措施,每天多抽一些时间出来与两个兄弟共同分担服侍阿判的义务,还在菜馆里买两个菜改善生活。
同时,在苦涩的生活中尽量挖出一些甜味。陈三虽与凌珍保持着恋爱关系,但感情并不专一,看到漂亮女子经常要动心。
对面大病房是男女混合病房,虽然探病家属唠唠叨叨的的谈话声影响围墙睡眠,引起他们不满,却有一个绝色女子开盲肠炎也躺在那里,而且其病床正在陈三的视线之下。
于是,他们的话题总是在这位不知名的女病人身上展开。"标致女人起床了""标致女人在帐子里换衣裳""外科医生在给标致女人检查开刀创口,这个贼坯,检查的时间比别人长一倍!"
两位兄长甚至设计,如何使陈三能摔掉凌珍,而把那个女人娶到手。毕竟老父重病在身,说说而已。
第四十三回
正直清白乐天离世不愧良心长子年届不惑只得拼命向前
7月下旬,盆子和哈哈一起来枫林,把两个兄弟换下来,打发他们回震泽,等候阿判的病情消息。
阿判的情况越来越坏了,原来精神和胃口都还不差,现在整天昏昏欲睡,已不能咽下饭菜,只能喝一点鱼汤、肉汤和麦乳精。由于翻身少,屁股上已经长了碗口大的褥疮。
三邀四请把外科医生请来,剪去一些腐肉,涂些药膏,贴上纱布。以后护士也天天来换药,亨元还从县属厂借来一台旧电扇,对准父亲病床,呼拉拉地吹,使病人少出些汗,也可避免蚊虫叮咬。
阿判在神志清醒时,仍表示了强烈的求生本能,埋怨医生没有尽力,为什么不能开刀?“要治好病只有动手术,否则,看来要“搀交椅(指死亡)了。”
亨元认为阿判现在的条件比纳香人患病时好多了,回想母亲重病时对父亲的怨言,有些反感,就数落了他几句。
阿判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对亡妻也怀着深深的内疚,因而求生欲望逐渐淡薄,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了。
7月底,医生关照病人家属,阿判的生命已走到尽头,断气就这在两天了。亨元在这关键时刻,索性从建新大队请了假回来,与两位姐姐一起天天陪侍阿判。
他的心脏以下已毫无知觉,每隔一、二小时要帮他翻次身。滞留在直肠里的粪便,亨元戴上薄橡皮手套去挖出来。他还拿出轧剪给父亲理了个发,洗了次头。当然嘴里总要叨上根香烟。
阿判呼吸逐渐感到困难,医生搬来了氧气瓶。8月3日凌晨1时许,站立在其身旁的三个儿女发现插在他鼻腔内的氧气管已毫无声息。
急忙召来值班医生,检查瞳孔、按脉息,确认已离开了尘世。医生给他注射了最后一针,是防腐针。三个儿女欲哭无泪,心里想,这样也好,活着在受罪。
按习惯,要给遗体洗澡,由于在医院里,只好因陋就简。亨元又点燃了一根纸烟,坐在阿判背后将他的上半身扶起来,由两个姐姐用脸盆里的水给父亲全身擦洗一遍。
洗到屁股上的褥疮时,已经烂成碗口大的洞了,洞内白骨隐约可见,惨不成睹。
天渐渐亮了,亨元赶到家中告诉计萍阿判的死讯。草草吃了些早点,就到派出所去开死亡证明,同时打电话给火葬场,请他们将遗体从医院运走。这些事办好后,亨元替换盆子和哈哈,让她们也去吃点早饭,而且,她们还要上街给亡父买一套火化时的穿戴。
亨元坐在病室的另一只病床上,看着被电风扇强风吹拂着的阿判的遗体,凄凉之感使他全身渗透着丝丝寒意。
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亨元的长辈一个个离他而去。
先是母亲在1961年的贫病交迫中撒手西归。
接着咸菜好婆于1962年寿终正寝。
在邮电支票局局长任上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的阿德熬到1968年"解脱"。
大姨妈于1969年被逼投河自尽。
势利小人凤生在那一年也没有逃脱死神的追袭。
随着父亲的亡故,亨元一代的金氏家族中已无男性长辈。
阿判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什么遗产,他死亡时脱下的汗衫也是儿女们给他买的,经过计萍洗涤和消毒后,现穿在亨元身上。
但他对生活始终持有的乐观态度和善良性格,不但成为后代永远的纪念,也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亨元等人今后的行为轨迹。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亨元越来越深刻地回忆起父亲的长处,同时痛楚地检讨自己在他生前所表现的某些忤逆行为。
窗外淅淅沥沥淅淅下起雨来,两位姐姐从镇上成衣铺里给阿判买了身蟹青色单布中山装,却忘了买帽子,大概以为夏天用不着。后来听人家说火葬死者最好戴帽子,以免火化时脑袋炸开。
木已成舟,懊悔莫及。还有一点,死者应当停尸24小时以上再火化,据说,人死后脑部细胞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全部灭亡。
因此,那时人还可能有某种意识活动。如果马上投入火化炉,对死者是不是太残酷了?可是,亨元等人当时并无这方面的知识。
考虑的是天气炎热,停尸太久怕遗体腐烂发臭,事实上褥疮那个地方已经不断在溢出脓水了,所以,他们急于把死者送到火葬场去。
午饭后约12点半光景,运尸车开到医院。从车上下来两个人,抬着一付木板担架。其中一个是司机,摆架子不肯抬死人。
亨元义不容辞补了缺。运尸工人在前,他在后,担架宽度不够,身体勉强摆上去了,两只僵硬的手却没有依托,走几步路就从胸前滑挂下来。亨元只得一回儿把左手托上去,一回儿把右手摆摆好。
抬到医院门口,运尸工人把躺着阿判的担架塞进车厢底下的一个槽里,亲属们则统统进了车厢。
运尸车驶至十四公里远处的朱山大桥,向左面拐了个弯,沿着黄浦江支流南行三、四公里,来到了火葬场。
亨元等人先到业务室付运尸费,办火葬手续。文革期间,一切从简。拣了一只中等价格的骨灰盒,全部费用七十多元钱。
三点钟左右,阿判躺在特制的金属板停尸车上,给家属们见最后一面。当天来火葬场的尸体只有两具,另一具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年仅三、四岁的小姑娘,送葬的人倒不少,哭哭啼啼很热闹。
待小姑娘火化后,礼堂里顿时冷静起来,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厅仅阿判一人和给他送葬的四个亲属。亨元等人在此情此景之下,不约而同感到一阵心酸,个个号啕大哭起来。
在哭声中,火化工将阿判的停尸车推进炉子间,并随手将两扇铁门关闭。
不一回,里面走出一个工人,手里拎着一只黑色塑料袋,估计里面是阿判的骨灰,装入购置的骨灰盒后,交到亨元手中。
四个人神色黯然地从火葬场走出来,就近上了开往朱山的公共汽车,在大桥边下了车,再转乘到枫林的车子,总算在天黑前带着骨灰盒到了家里。
耽在震泽的两个兄弟还不知道父亲的死讯,因此,盆子和哈哈急于带着骨灰盒回去。
次日一早,亨元陪同两个姐姐踏上归途。他们三个人伴着阿判的骨灰盒踏进藕河街的家门时,盆子和哈哈又大哭了一场。围墙和陈三见此情景,知道阿判已经过世了,不禁也很悲伤。围墙嗫嚅着嘴唇自言自语;"什么会去得这么快,我的一个月假期还没有到呢。"
打电话告诉了瓜子,林茹夫妻俩很快就赶到了。简单布置了一下客厅暂充灵堂。大家手臂上都挂了黑袖圈。震泽邮电支局的一些职工和隔壁乡邻闻讯前来吊唁,就开了个追悼会。没有什么庄重仪式,大家以死者为话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阿判不是高人,七十个春夏秋冬,没有建立过什么称得上重要的事业;阿判不是智者,没有为自己或亲人设计过美好的前程。
但是阿判是一个有个性、讲道德、遒纪守法的公民,七十年如一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仍然不失为一个大写的人。
丧事办完,亨元回到枫林。计萍告诉他,在他和姐姐们离开枫林的时候,三姑母前来探望她的兄长,闻知阿判已经亡故且已火化,虽未痛哭,两行清泪却挂在双颊。
计萍正忙着洗涤死者用过的被单、面盆和碗杯,没有多少言语好安慰客人,三姑母呆了一回,只得拎着原本给阿哥吃的水果、食品茫然地乘车回了上海。
亨元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第二期理论学习班,第一负责人换了镇党委组织委员,亨元虽然仍是第二负责人,但是规格和地位不能与第一期相比了。
亨元写的总结材料也没有获得有关方面的重视,略有一些水平的学员甚至表现出瞧不起他的神情。第二期干部轮训班草草收了场。
国庆后,回到车东领导的政工组。当时的中心是按照第一副总理小平同志的思路搞"全面整顿",镇党委派出一些调查组深入基层,亨元跟着办公室主任坐镇枫林商业站。
亨元白天在百货店跟营业员一块立柜台,晚上参加药店的小组讨论。不料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央又批评起小平来了。
一九七六年元旦后,围墙从北京回家探亲,途经枫林,在亨元家的北面一间住了几天。一月七日凌晨,围墙听了自备的半导体收音机后惊呼:"中国要乱了"。
原来,这天新闻报导了周总理因病逝世的消息。在他逝世前,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搞全面整顿的小平同志受到了批判,全国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搞反击右倾翻案风。
那年春节,亨元只身往震泽探亲,宅内只有陈三一人。哈哈去了青云,因为盆子和张林早在阿判生前就已调到吴江青云工作。
陈三描述了一个人在冷冷清清家里的孤苦处境,亨元深表同情。阿判逝世后邮电局发给家属二百多元抚恤金,大家一致同意由陈三认领。三弟把自己准备如何使用这笔钱有了计划。他准备买一台当时价格最为便宜的上海产金星九寸电视机。
问题是市场上上海货不多,听说要开后门才能买到。亨元起初托了镇办厂一名采购员,还塞给一条飞马牌香烟,采购员收受香烟后拍胸担保能买到。
当亨元兄弟俩携款乘轮船到上海找他时,他一脸为难之色。亨元意识到飞马牌香烟丢给"王伯伯"了。
幸亏陈三还有个计划,想托计芳买几块台面玻璃。计芳在玻璃厂工作,开这点后门对一个厂的主办会计来说是办得到的。亨元和陈三总算没有白到上海一趟。这时候,陈三和凌珍的关系已经敲定,所以要采买台面玻璃准备婚事。
陈三要个黑白电视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戏称自己是"七十年代"电视迷"。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在震泽的一家商店里化二百五十元钱买到了苏州产孔雀牌九寸电视机。
弟兄俩小心翼翼地把"宝贝"捧回家。接上电源及陈三早就准备好的各种天线,起先左弄右拨调不出图象。
在弟兄俩唉声叹气、之时,忽然从"宝贝"中的扬声器里清晰地听到了一声"香烟、洋火、桂花糖"。
接着,文革后期屈指可数的新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画面浮现在莹屏上。
两人惊喜之情难以形容,一面观看电视、一面品味着独家享有电视机的喜悦。陈三说:"如果老阿判活在世上该多么高兴。"
被三弟这么一说,亨元不知何故,感到对过世不久的父亲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亨元已到了不惑之年。他不禁想起被鲁迅批判过的胡适的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性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不管胡适的功过是非,他这首小诗却极其符合亨元此时的心态。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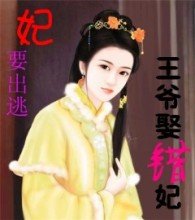


![[裴晓庆] 下雪的故事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