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缣跖用媲啊�
大概同他们这派交往甚少之故,计萍言语不多,基本上问一句答一句,谈到九点多钟,起身告辞。计萍走出门外,皮旦忽然发表意见:第一次相见,亨元应该有所馈赠。
临时去买已经来不及,好在小无锡处有现成的领袖石膏宝象,亨元"借"了一个,飞奔下楼朝计萍前进的方向追。
在楼下南面的广场上双方相遇,亨元恭恭敬敬地把宝象送到计萍手上,苗条女子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楼上的男男女女爬在窗口,一直目睹这场好戏,等他回来,又嘻闹了一番,说:计萍的这一旋转动作,好似白毛女跳芭蕾舞。
以后,亨元就和计萍单独接触了。有时借亦华的单间宿舍,有时直接在广场对面枫小女教师宿舍会面。
计萍的房间在楼上,与其他两位女同事合一室,她的床铺收拾得最干净,几乎一尘不染。写字台是用学生桌椅替代的,放在台上的一只广口瓶里插着一束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腊梅。
两人谈恋爱的新闻在枫中和枫小的教师中不径而走,龙昌俏皮地在亨元这一派人中转述外界对这件事的反应:"枫林镇最邋遢的人和最清洁的人结合在一起了。"
说计萍爱清洁,名不虚传。亨元经常去她房间后发现,另外两位女教师的床来客可以随便坐,唯独她那张一尘不染的床,没有人敢坐上去。
住另一个房间的冬花(刚从上海师范毕业)背着她对亨元说:"计萍的床是不准别人乱坐的。"
亨元问苗条女子有没有这条清规戒律?她坦率承认,同时对冬花臭袜子放在面盆里几天不洗、外丽内脏等懒惰行为表示自己的不满:
"你不要看这个小女子平时穿得三青四绿,领头里的污垢却经常积得很厚。"
冬花是文艺积极分子,起《红灯记》李玉梅角色,一曲:"奶奶你听我说"醉到了枫林小学校长车东,从此颇受器重。
再说亨元邋遢,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他的粗心大意和不拘小节,确实是有点名气的。
有一次,他早晨起床,到设在女宿舍旁的伙房去打开水,觉得遇到的一些女学生都以异样的眼光注视着自己,有的还用手绢掩着嘴,强忍着不笑出声来。
亨元抓抓头皮、摸摸脸蛋,并未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提着热水瓶快步奔回宿舍的路上,只觉得臀部后面好象有什么东西一甩一甩。
放下热水瓶,朝背后一摸,才知道内衣的一只衣袖没有穿进去,因而从外衣后摆处露了出来。有个调皮学生还在朝它吹气,裤带居然还能飘拂起来。
还有一次是给学生上政治课的时候,自以为讲得深入浅出,越讲越有劲,学生却躁动不安,不知什么缘故。
后来发现坐在前排的几个同学,注意力不集中在黑板上,而集中在老师身体的下部,才朝他们注意的热点望去,不望犹可,一望几乎无地自容。
裤档纽扣没有扣好,里面卫生裤的一条白色腰带从裤档里钻了出来。
尽管亨元和计萍在生活上有如此大的差异,自从结识以后,彼此感情发展很快。亨元要对方"敲定"以便向家中报喜。苗条女子说:
"我与你的事我家里还不知道,父亲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母亲可能有些阻力。最近我把手表退给了以前的对象,母亲还对我发了一通脾气。"
亨元说:"那么,先通知你父亲,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他果然利用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在一张空白介绍信上写着:"兹介绍我校金亨元前往上海玻璃厂通过计芳了解其女计萍的有关情况",胸有成竹地到该厂去拜访未来的丈人了。
玻璃厂人事科干部郑重其事地接待了这位前来外调的"中共正式党员",然后根据他的要求把计芳从会计室召来,安排一个小房间让他们单独谈话。
高颧骨、大眼框、面庞四方、前额已经谢顶的准岳父诚惶诚恐地看着介绍信,琢磨着对方的来意。
亨元却异常镇静地先询问对方一番,在确认他是计萍的父亲后,才道出了来意。
计芳逐渐听出女儿在枫林已经有了男朋友,心情轻松不少;又听出坐在自己对面,以调查人身份出现的"中共正式党员"就是自己未来的女婿时,更是喜形于色。
当即表态:"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做老人的决不拖后腿。母亲方面,我会去做工作的。"
午休铃已敲响,计芳热情地邀亨元在玻璃厂食堂里共进午餐,"中共正式党员"婉言谢绝了。第一次接触,要说的话已说了,适可而止,不能给准岳父留下轻浮的印象。
初战告捷,计萍放下了思想包袱,与亨元感情更炽热了些;对方则认为,关系已经"敲定",可以写信给家里报喜了。信是写给哈哈的,因为三姐善解人意。
"。。。。。。,计萍心灵手巧,比较符合我的择偶要求。现在彼此关系已经肯定,希望你能来枫林,大家见见面。"
五一节前夕,哈哈果然来到了他的住处,此时,龙昌一家刚好到上海他舅舅家过劳动节,钥匙交给了亨元。后者让三姐住在里面一间,计萍与她作陪,合睡一张大床。
一日三餐则在外面一间烧饭炒菜,好在一应炊事用具和吃饭桌椅俱全。
短短二、三天时间,哈哈和计萍谈了不少知心话。临走,姐姐乘和兄弟单独在一起时,发表了对计萍很好的意见。
第三十三回
整人挨整轮流花插骑墙头头指鹿为马特疑牛棚苦度春秋
由朱山海防部队派入的军宣队分别进驻派性较严重的单位。枫林中学来了两位军人,一位姓廖的参谋和另一姓常的班长,都是浙江籍人。
廖参谋长得很帅,外形像样板戏里的洪常青,肚皮里有点墨水,文绉绉的;常班长却一脸土气。
他们的任务是抓大联合和搞复课。由于亨元在两派联合中姿态较高,出身又比何西和皮旦等党员好,所以选中了他作为唯一的教师参加大联合临时领导小组。
其成员还有:胡虎和"泥腿子"、"红苗子"各一名小将。武斗工事已拆除,教师们纷纷从三层楼搬回校内,亨元搬进了原来的党支部兼校长室。
亨元在外面搭一张铺睡觉,里面则与其他"领导人员"一起办公。这样,与计萍的约会方便得多,因为晚上别人都走掉了,这个地方可以由他一个人使用。
时值一九六八年,"抗美援越"高潮期,"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紧缺血浆,中国人依靠庞大的人口优势发动了义务献血,要求共产党员带头。
教工造反总部头头借口身体素质太差,没有报名。亨元与他的那一派人私底下讥笑议论一番之后,“挺身而出”,到枫林医院进行了血液检查。
报告出来,医生说:这只血特别好,各项指标完全合格。大约一个星期内就要抽血了,定量200CC。
亨元从娘胎落地,活了近三十年,很少光顾医院,除了伤风咳嗽到门诊部配点药吃,基本上没有打过针。说基本不说根本,缘由大学二年级补蛀牙到市公费医院去,在舌根上打过一剂麻醉针。
现在,听说要用一根象自来水笔吸水管那般粗细的针头插进血管,从血管里抽出一瓶桔子汁那么多的血,送给素不相识的越南人。心里紧张万分,不知道自己能否熬过这一关而不在众人面前出洋相。
那时候,"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军宣队要已经联合起来的两派教师各抽出2、3个人下乡办"伸腿班"。
教工总部方面派出杜行和另几位教师人去杨红大队;"七教员"则推出亨元、马龙等人去新立大队。陈林因与马龙谈得拢,也加盟去新立大队。
一个政治教员、一个数学教员、一个语文教员,三个人构成了这支伸腿班的教学队伍。借新立小学一间教室,生源是当地小学毕业没有上初中的农民子弟。
家访动员后,来了二、三十人。作为唯一的党员,亨元自然成了这个伸腿班的负责人。同时兼教政治课,还发挥特长,给学生上音乐课。
不会弹风琴,(也没有风琴)笛子或胡琴伴奏,反正学生和老师要求都不高,凑合着能对付。
路比较远,从枫林出发要走三刻钟,中午是不能回家吃饭了,就在小学搭伙,他们有一个厨子,多做三个人的饭并不麻烦。
在亨元等人下乡办伸腿班的时候,学校里重新建立了三结合临时领导班子。老干部胡虎仍然被“结合”进去,而教师由复员军人翁玉取代了亨元。
不过这个临时班子寿命不长,两派对它都有意见,胡虎本是个傀儡,翁玉想两派都不得罪,结果左右不讨好,有一次居然在亨元等人面前急得哭出来。
此人也算是行伍出身,却毫无军人的豪迈气概。其妻比他小十几岁,倒是个豆腐西施,还是他来枫林中学教书前,在新行农中当负责人时的一个学生。
他看中了这位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农家姑娘。在穷追不舍之下发生了关系而且怀了孕,这下事情闹大了,如果无限上纲,非但要吃官司,甚至可能吃"花生米"。
只好"私了",豆腐西施变成了翁玉夫人。新行农中不好耽下去了,于是调来了枫中。到文革中期,他已有了三个男孩。
翁玉夫人文化不高,只能在村校代代课。主要经济来源靠丈夫六十多元工资,维持一家六口够拮据了。他把经济大权独揽一身,不许夫人乱花一分钱,但对她的衣着打扮却很注意。
他利用数学上的几何图形原理,无师自通学会了裁剪和缝纫,从而给老婆穿上一件件新衣,他自己则不修边幅,因此夫妻俩站在一起,不很相称。
国庆节一过,浦江县派出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进驻各上层建筑单位。军宣队撤走了,临时三结合组织也偃旗息鼓。
现在来枫林中学掌权的是江涛、封锐等来自叶松和海塘公社的贫宣队队员。
他们根据"红太阳"作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最新指示,提出要深挖教师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把两个伸腿班的教师召回学校,开办了一次次的清队学习班。
"三家村"和"四家店"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们重新被看管起来;其他教师被打发到奋斗大队举办"脱离工作、脱离教学、脱离家庭"的"三脱离"学习班。
亨元打了个被头包背在身上,依依不舍地与仍旧留在枫中教工宿舍那间小屋的计萍告别。数十名男女教师分住在奋斗小学的两间教室里。
课桌椅并成床,白天被头卷一卷又变成小组讨论会场。吃着简陋的一日三餐,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生活。而主宰着他们命运的贫宣队员们,正在根据大字报和小字报进行分析、排队和内查外调。
阳历年刚过,在上海远郊小镇的枫林中学内,贫宣队根据最高指示把十几名教师打进了劳改队,这已经远远超出老人家关于"阶级敌人仅仅是一小撮","不超过5%"的估计。
但是,内查外调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贫宣队毫无收兵之意。江涛有时到奋斗大队来给封闭着的教师们"透透风",说:
“学校里有一颗埋藏得很深的"定时炸弹"还没有挖出来。”“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你们等着瞧吧,阶级敌人也许就睡在你们身边!”
自命不凡的江涛抛下这最后的两句话后又回到了学校。果然不久,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到了奋斗大队:亦华是现行特务,已经隔离审查。
这个消息把大家惊呆了,尤其是"七教员",几乎是致命的一击。余下的六教员以及同情七教员的人对亦华的特疑持怀疑态度。
因为她虽然出身旧军官家庭,但父亲是北阀时代的军官,与国民党关系不大,何况,中学时家乡湖南就解放了,她也参了军,分在文工团。
一九五六年以调干生身份考入某地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年毕业,本可留在城市里工作,却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主动与他人对调到枫林这个偏辟小镇来教书。
几年来担任高中二班主任、语文教师,工作卓有成绩。此人待人和蔼,大家推选她为工会副主席(主席是陶崇)文革前的党支部还列她为建党对象。
她与师范同学辛河已成对象。辛毕业后分配在七宝镇上的上海农校任教师,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蹬着那辆从旧货店以七十余元人民币买来的自行车到枫林来相会。
他们住教师宿舍区另一间单独的小屋,也不足六平方米。如此清白人生,怎么能同狰狞可怖的现行特务联系起来呢?但是,江涛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向教师们解释:
"越是不像特务的人越有可能当特务。你们不能光看表面,亦华的老实都是装出来的。你们可知道,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干什么?在拍电报!同国民党特务机构联络。"
据贫宣队介绍,他们手里有两张王牌,足以证明她是个现行特务。那就是发现她藏有一本密电码和一架发报机。
前者已为贫宣队搜获,放在她的档案里;后者已发现隐藏机器的地洞,可惜机子已被她转移。审问之下,得知转移到她爱人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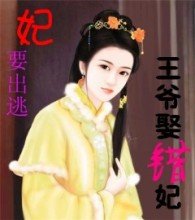


![[裴晓庆] 下雪的故事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