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钱放进短袖衬衫胸前的口袋内,拎着两只箱子离开了县府大门。汽车站在火车站附近,走的是回头路,经过邮电局,抽出十元钱邮汇到震泽。亨元急于要父母亲分享儿子第一次工资的喜悦。
汽车开到米市渡,徒步走上轮渡。轮渡开到黄浦江南岸,只见旅客们飞奔上岸。他拎着箱子慢悠悠地走上岸,眺望一下四周,除了一个汽车站和几个摊头外,不像是集镇。
一问才知道这里是朱山县地界,到枫林还需要乘一段公共汽车。悻悻地走上汽车,座位已被他人捷足先登。车子开动后,他盼望枫林快一点到站,可是报了几个地名都不是。旁边一位年轻农民看到他焦急的样子,关心地问他何去何从?知道是分配到枫林中学任教的大学生,肃然起敬。
青年农民说,他也是去枫林的,可以做向导,领他到学校。枫林到了,他主动帮亨元拿行李,沉重的铁皮箱,轻松地扛上了那人的肩。
两人走进镇来,首先映入亨元眼帘的是个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校园内耸起一座土山,山顶上还有个凉亭。他以为这就是中学了,一看校牌,却是小学。
往前走五十余米,迎面一个小河浜,走过石桥穿过一条小弄堂,往西再走十余米,看到了悬挂枫林中学校牌的大门。进门后左侧也有一个土山,但土山上杂木丛生,十分荒芜。右侧有个大草棚,草棚前是个篮球场。
再往前走,两排三角顶平房相对而立,中间是小树丛。校长和教师办公室设在南边的那排平房内。青年农民带领亨元走进校长室。校长秦东年约三十岁左右,头发已经秃光,白净的瘦脸上戴一付深度近视镜颇具学者风度。
第十五回
身无一技之长上课味同嚼蜡不谙学生心理对话隔靴搔痒
校长热情欢迎新教师的到来,马上召来有一对小暴眼的政治教师杜行,介绍给亨元:"他是本校政治教研组长兼工会主席,年轻有为,今后可以向他讨教。"
矮个子、小暴眼、操一口"牙、牙、牙"浙江话的杜行伸出手腕看看表说:"已经一点多了,你们午饭还没有吃吧。"
亨元点点头,并且把身边的青年农民向两人略作介绍,说:幸得遇到这样的热心人,才避免了旅途之苦。秦校长指示杜行,去找伙房头曹元,叫他安排一下两个人的午餐。
曹元是镶几个金牙的高个汉子,他拿着钥匙去开厨房门的时候,青年农民已经不告别。亨元十分遗憾未能同他共进午餐,更不知道这位做好事的人姓甚名谁。犹豫间,曹元端了一碗饭、一盆菜递给他,说:"粮票和钱以后再算"
亨元就餐完毕,跟着杜行来到办公室。室内约七、八位教师。坐政治教研组长对面是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女教师秀娴,教低年级政治。还有外语教师海嬷、刘玲,都是女的。
一个面目清秀学生模样的人在刻腊纸,介绍说是教导干事;从外面又进来一个学生般的人,蹲在办公桌前在开靠近地面的抽屉翻书,介绍说是团总支负责人、教外语的皮旦。
还有教历史的常和;教地理的江言;教政治的郭谷等。这个办公室称为政史地办公室,统由杜行负责。
"牙牙牙"安置好亨元的办公桌后,让他到宿舍安排床铺休息。由面孔黑黝黝、光溜溜的皮旦领着从办公室沿一排竹篱笆往东走。约七、八十米,看到一幢楼房。前面是一片地,一间小屋。屋旁是一个公用水龙头。
这幢楼房有两个楼梯,正中一个楼梯贯通西南的两楼两底;还有个楼梯设在校园东面的小门内,拾级而上后,楼道口临街的一间是皮旦和教导主任胡虎合住的宿舍,现在安排亨元住进去。对面一间是校长秦东的家属宿舍,楼道往北则是房东的地盘了。
他跟着皮旦进了宿舍,房间面积十余平方,摆三张单人铺是够宽敞的。房门在西,窗户在南,东面还有个窗洞,空气比较流通。
亨元的床铺夹在皮旦和教导主任中间,屋内有两排铅丝可悬挂蚊帐。床铺一律都是棕棚,由学生上升为教师,虽然在穷乡僻壤,住宿条件倒是改善了。
皮旦领新教师进屋后,就出去办他的事了。不一回,教导主任胡虎回到宿舍。此人高头大马,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稀稀疏疏的胡子,被劣质香烟熏得发黑的门牙,说着口齿不清的山东莱西话。含糊地与亨元打了个招呼后就蹲在自己床上挖鼻孔。
亨元向他打听从枫林到吴江的距离和交通路线,胡虎马马虎虎地说了个大概,使亨元感到路途并不遥远,要回家却颇费周折。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他在饭厅的一角选择一张方桌就餐,邻桌一位讲安徽普通话的青年男教师和一位讲上海话的青年女教师,边吃边谈,戚戚促促,十分热络。朝亨元这边望上一眼,话题似乎转向亨元身上了,使他很不舒服。
秦东要他担任初三年级四个班级的政治课并兼初三丙班班主任。缘由本校虽设高中,但每个年级仅一个班,政治课均由教研组长";牙牙牙";包下了。毫无教学经验的亨元只得在初中部授课。
另一个原因,秦东所以向县文教局讨政治教师,是原来担任初三政治课的郭谷,最近获准调回上海,初三的政治课必须有个人顶缺。
那个在食堂里戚戚私语亨元的女教师名申英。在郭谷调离后,暂代三丙班主任一职。现在她站在讲台中央,办理交接。
他,额前一络卷发,戴一付玳瑁近视眼镜,一双套着短统白袜的脚穿在陈旧布鞋上,局促不安地站立在申英身旁。
当中学教师的亨元,三分自豪,七分紧张,望着下面一张张稚气的脸。坐在前排的还纯粹是孩子;而后排的几位已经是喉管突出的青年了。劳动委员朱良,与亨元相比似乎还要年长一些,实际上小他一岁。大概是农村子弟,皮肤粗糙、面孔黝黑,见老些。
申英非常老练地训戒着学生。两手撑着讲台,左腿支持身体的重心,右腿惬意地用脚尖着地不断摆动。她耳听八方、眼观四角,对那些眼睛骨溜溜望着老师,双手在书桌里面做小动作的学生,毫不留情,点名批评。亨元获得启示:必须在学生面前建立自己的威严。
他用生硬的普通话介绍了自己的“辉煌”学历,并对自己主管的这一班学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四、五十名大大小小的孩子接纳了这位从大城市来而衣着并不比他们考究多少的老师。
胡虎是上海某学院下放来的党员干部,是随着解放大军打进上海城的,可谓开国功臣。在上海安家后,把山东老家父母亲外加一个小弟弟接来上海,从此家庭矛盾日趋严重。下放到枫林后,他索性把父母和老弟接到枫林,免得妻子心烦。
一间空着的学生宿舍供他父母兄弟居住,自己则住教师集体宿舍。两位老人衣着不整,很扫教导主任的面子。
而秦东校长的父母也同时从苏北接来枫林,则斯文得多了。秦太翁瓜皮小帽,白净的脸皮配上白须白发,宛如清末遗老。和小脚伶仃的秦太媪在篱笆走道旁开辟出一长条自留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金"。倒也悠然自得。
胡老汉的寒酸相成了某些师生谈笑的资料,胡虎顶不住"舆论"压力,只得打发父母回山东,留小兄弟在枫林读书。于是,大胡把床铺让给小胡,自己在校内另觅住处。
亨元与小胡朝夕相处,觉得这小子很机灵,且有山东人的豪爽性格。有个晚上,各自睡在床上,他和亨元唠家常。小胡问:
“你班有个班长叫李杰是不是?”
“我班的班长叫李甲不是李杰。”
“对,李甲,我认识,个子不高;还有个学生叫奚杰,我经常看到他在大街上用粮票与别人换钞票,我怀疑他来路不大正当。”
亨元也从其他教师口中得知奚杰手脚不大干净。正巧班级里有个寄宿生哭丧着脸来汇报他经常放在口袋里的几斤食堂饭票一夜工夫就没有了。
傍晚,亨元将与那个学生一个宿舍的奚杰召来办公室盘问。自以为具有法官素质的他把其貌不扬,脸上有几点小麻子的奚杰当成“疑犯”。
奚杰对付老师的办法是沉默不语。
"你不要以沉默表示反抗。不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英雄对反动派;一种是罪犯对审判员。你属于哪一种?"
奚杰既不敢把老师当反动派,更不愿承认自己是罪犯,所以继续保持他的沉默。亨元的"审讯"失败,旁听的教师哑然失笑。
他的";审问";手段也有奏效的,又是一起失窃饭菜票案,发生在女生宿舍。怀疑对象是史芬。他把吓得索索抖的这个瘦小女孩从教室里传来,三问四问之下居然承认是自己偷的。他自以为法学院学到的一点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在那些小罗卜头面前耀武扬威了一番。
初三政治课学的是领袖写的现代史。他想:凭我大学毕业前中国现代史考满分的水平,真是杀鸡用牛刀了。
可是,不懂教学方法,板书和讲授不协调,再加逻辑思维混乱和口头表达能力差,在课堂上或则生搬硬套理论;或则信口开河乱讲一通,使学生不知所云,且常常拖堂。
初三乙班学生钱元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当众责问亨元:"杜行老师上课我们听得懂,记得牢;你上的课我们听不懂。为什么?"弄得他很狼狈。
就教未至半月,已近国庆。他盘算着利用假期回家与父母兄弟团聚。秀娴告诉他由枫林至吴江的详细路线。"亨元一站接一站好不容易来到中转地嘉兴汽车站。因为家里来信说纳香人在吴江,所以买了去吴江的车票,准备与母亲会合后一起回震泽。
他拎了在嘉兴买的五斤南湖菱到达湖滨公社已近傍晚。纳香人见到当中学教师的大儿子很高兴。把南湖菱分拣一小部分嫩的生吃;其余煮熟后与奶油瓜子一家分享。她腹部开设人工肠道,食量很小,剥了几颗煮熟的南湖菱,就不敢再吃了。
次日凌晨,母子俩登上轮船回震泽。回到震泽,家里一付油干灯草尽的穷样子,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电灯装不起,家具基本上变卖殆尽。母亲晚上咳嗽不止,气喘吁吁。他在家里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后踏上返校的旅途。从此,再也见不到慈爱的母亲了。
第十六回
西风夕照昏鸦行尸走肉奔丧惨淡经营人生谁与阿亨同房
转眼已近元旦,阿判来信说,纳香人哮喘越来越严重;盆子的附言更使他忧虑:母亲直肠癌患处虽经手术切除,一年后又有转移和扩散的迹象。纳香人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一家人共度困难时期的无聊时光。
学校为教职员工在除夕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夜餐(照样要付饭菜票)亨元缺乏油水的肚皮突然饱餐一顿后,很不舒服,晚上睡得不香。
元旦上午,在校长室值班的秦东,差人将还在宿舍里磨蹲的亨元叫到他那儿。秦东说:
“金老师,请你不要太伤心,你家里来了电报,说你母亲病故了。”
他急看电文内容如斯:“母病故速回”。他应该预料而不愿意正视的事实终于来临了,(其实,这个电报是可以产生歧义的,由于没有标点符号,既可以理解为:“母病故,速回。"也可以理解为:“母病,故速回。”)
在怔了一怔后,嚎啕大哭起来。秦东又召来杜行合计了一番,以工会名义借一百元钱供他奔丧之用。"牙牙牙"一看手表已经九点,催促亨元揩干眼泪赶紧上路。
亨元浑浑噩噩地一站站乘车经过盛泽,天暗下来了,当天已无车可乘,只得在车站旁的小旅馆暂宿一夜。第二天一早,乘车直奔震泽。进藕河街家门,厅堂内都是戴孝之人。除哈哈尚在广西外,全家都已到场,还有苏州衙门场、穿珍珠巷的亲戚。
长条桌上摆着母亲的遗象和香烛纸钱。纳香人躺在靠近扶梯间的一付门板上,头戴黑绒线平顶帽,身盖棉被,脚穿鞋袜。亨元不顾他人,急奔母亲榻前,扑在母亲身上痛哭不已。
晚上,请来了一班做道场的,吹吹打打。纳香人的亲属围绕香桌在鼓、钹和念经声中不断地兜圈子。亨元的棉耳朵鸭舌帽顶上贴了块白布;两只鞋后跟则缝红布;腰际围了白带子。
围墙和陈三也是如此,只是二弟的鞋袜已洞穿,脚趾几乎露在外头;三弟的白带子拖到了地面。
凌晨,送来了一口白皮棺材,亨元以长子的身份,托着母亲的头部,其他人抬着她的身体,放进棺材。他凝视母亲的身躯,却感到她头部沉重的分量。
母亲,你虽然合着眼,一条条深印着苦难的皱纹似乎表示一了百了的解脱,但是,你真的忍心丢下那些深爱着你,离不开你的孩子吗?
据阿判回忆,纳香人临终时正是元旦一时左右,请来的医生打了强心针仍然无效后,盆子痛不欲生,躺在母亲被窝里不肯起来,要与她同归于尽。
二姐在母亲卧病的最后一二个月,经她要求,由湖滨公社调来震泽邮电局话务室工作,现在家里剩下她和阿判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兄弟。这付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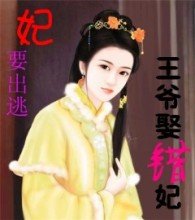


![[裴晓庆] 下雪的故事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