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文
第一回
邮局古镇筑巢小桥流水人家门前商贾林立
屋后载舟河道
江苏省吴江县的同里镇,现在已成为江南的一大游览胜地,但那名遐海内外的:“小桥,流水,人家”,经过人工的刻意雕琢,仍不免带有一些现代化的气息。
如果城里人真正想在同里寻找当年它那古朴风貌,倒不妨找一些在同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人谈谈,可以说四十年前的同里,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亨元一家是在1942年搬来同里居住的。乃父金根,原是苏州邮局的一名小职员,不知哪一点给他上司看中了,选派他到这个古镇来当三等邮局局长。
所谓三等邮局,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所谓局长,属下只有一名邮差。但邮局位置在同最繁华的竹行埭上。这条街不过一百余米。五,六十个铺子,却集中了全镇百分之九十的商店。
在邮局的东侧有锡箔庄、茶馆、饭店以及鼎鼎有名的谷香村糖果店;西侧有鱼行、水果店、席子铺、羊肉馆;邮局对面则是金龙书局、荣荣药房、银行、钱庄、酱鸭店、茶叶铺、绸布庄、旅社。
同里邮局是一幢两层楼房,纵深式二楼二底。楼下临街的那间充当公事房和营业场所;后面的底层没有铺地板,在北墙角砌着有烟囱的两眼柴灶,故只能作为厨房和简陋的起居室。
用水倒很方便,小楼同其他面北的商家一样,背水而立。出厨房有个木梯,可以拾级而下上河滩;上楼的扶梯设在厨房间北墙边,楼上有个过道,把南、北两个房间隔开。
临街的北屋由阿判夫妇携三岁的亨元居住;面水的南屋由亨元的三个姐姐:瓜子、盆子、哈哈居住。
这是亨元一生最幸福的时期。虽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但邮局是这个小镇与外界联系不可缺少的窗口,因而鬼子和汉奸们对这个地方的搔扰相对少一些。
阿判和纳香人正届年富力强,又善交际,同左邻右舍相处得视同亲人一般。鱼行老板金官﹑开水果店的光浩夫妇以及荣荣药房和锡箔庄的伙计们,都喜欢和阿判夫妇交往。
那些小伙计们,也许生活过得太单调乏味了了,向往温馨的家庭生活。所以,朝气蓬勃的金根一家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们。
爱屋及乌,他们注意到亨元这个孩子的外貌兼收并蓄了父母双方的优点,在同类儿童中可以说是出众的。他们很乐意抱着他在竹行埭上兜一兜。当然,经过谷香村糖果店不会忘记买一些花生糖之类塞在他的小手里。
阿判和纳香人都是乐天派。虽然收入不丰,经常入不敷出,但只要手里有一点钱,舍得吃,舍得用。尤其不会亏待孩子们。
寒冬腊月的晚上躺在被窝里似睡非睡之间,听得街上馄饨担子的竹梆声逐渐由远及近,阿判用绳子系了个小篮,从窗口挂下去,小贩接住后盛好一碗馄饨放在篮里,如此往复几次,大家分而食之。多么美妙的夜宵。
还有那春天的清晨,他尚未起床,就听到少年农女喊卖蔬菜发出的银铃般的声音:“阿要买金花菜搭马兰头--”“阿要买鲜滋滋、滑溜溜格莼菜汤”,真是一曲清晨交响乐。
初夏,光浩夫妇送来时鲜水果枇杷,纳香人用旧报纸折了个敞蓬船,把枇杷放在船里,给亨元拖着玩。
盛夏,阿判从后窗口向装着西瓜的农船打招呼,于是,农船靠在他家临水的厨房边,一只只西瓜直接从船里抛出来,里面的人接住后滚得满地都是。待亨元在厨房间的饭桌上午睡醒来,阿判一声"吃西瓜了",大家围而食之。
亨元不能忘怀风韵犹存的纳香人晚上抱着他在被窝里做"鸡鸡斗,哄哄飞";白天抱着他坐在靠背椅子上看小人书,边看边念:"这是好人,那是坏人"。
他也没有忘记,日本投降了,中央军将进驻同里的时候,他问正在熬猪油的母亲:中央军是好人还是坏人?
亨元出痧子的那年二弟围墙尚未出世,母亲把他移到北房间一张下了蚊帐的小床上,痧子发得很厉害,眼球内布满血丝,双眼几乎不能张开。
纳香人每天好几次给他用草药敷涂,为了便于照顾,索性大白天上床.把他紧紧搂在怀里睡觉,亨元在母爱的滋润中,很快恢复了健康。他还记得,母亲在生二弟的月子里把自己的乳汁涂在大儿子的脸上,说这样可以使皮肤长得好些
第二回
父宠母爱儿娇智穷才短胆小徒有金玉其表
其实一包稻草
母亲如此钟爱亨元是有原因的。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女儿,所以,在怀着这第四胎时,怕再生个女孩,心情忐忑不安。为避免第四胎出生,故意作超负荷运动,结果胎没有堕下,头脑被搅得像一团浆糊的人物却按时出生了。
出生的是一个男孩,悬在母亲心里的疙瘩也随之落地。孩子天庭饱满、鼻梁端正、唇红齿白、目光炯炯,将来必有作为。
纳香人娘家没有男丁,苏州北街祥泰糖果店老板把第四个女儿与别人换了个儿子,轮到纳香人怕走父母亲老路,现在不必担心了,而且儿子长得又么神气,这不是做母亲的骄傲吗?
岂知,这孩子是绣花枕头一包草,等长到四、五岁以后,随着他二弟围墙来到人世,两个儿子一比较优劣就见分晓了。
亨元随同三姐哈哈到泰来小学幼儿班念书,围墙跟着母亲牙牙学语。这小子虽然奶声奶气,识方块字似乎不费什么力气,而年长四岁的乃兄却任是怎样教诲,总是不能把最简单的汉字记住。
家里请来了算命的瞎子,闭了眼睛给亨元算一挂,除了多子多孙的胡扯外,对他的智力倒刻画得入木三分:"读书像唱山歌,写字画墨涂涂"。
果然,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书读得一塌糊涂。级任教师鸭连连,因公鸭嗓、八字步得名,经常到已搬至吉利桥堍洪宅的邮局看报纸,与阿判有点头之交,对亨元的学业却毫不容情。他布置的写字课堂作业使亨元常常为之关夜学或则墨笔字没有摆进描红簿的框框,或则一滴墨水弄脏了作本,鸭连连固执地要求亨元重做。
但是,学年结束,还是靠了他的帮忙,使亨元从二年级";升";到了三年级。从此,年年靠"帮忙",一直到小学五年级。
此时,正是国民党最黑暗的时候,内战打得最激烈的时期。阿判在这个小镇上人缘颇好,又有邮局局长这样的头衔,三教九流,都有所结交。或到任家花园(退思园)叉麻将,或在家摆酒请客,或三朋四友在菜馆聚餐。
除雀战外,许多应酬活动都把亨元带上,一则他是头生儿子,二则外表出众,引以自豪。亨元生活在这个今日有酒今日醉,寅吃卯粮的家庭里,时而像爷一样阔气,时而象乞丐一样邋遢。
读书视为畏途,幻想一天到晚吃吃白相相。看小人书、赌洋片、练"武功",样样玩意都沾边,可是智能不高,门槛不精。
纳香人逐渐看出这个孩子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本质是在他九岁那年的年初一早晨。
除夕之夜大雨滂沱,次日早晨,小镇的烂泥石子地一片稀湿。亨元怀揣丰厚的压岁钱,穿着新棉衣,脚踩新棉鞋到金龙书局买了两样东西:一支警笛、一把玩具手枪。
兴高采烈地淌着水家。纳香人见他满身泥浆却还呜呜地吹着笛,一付心满意足的样子,气得几乎晕到。
祖母咸菜更对这位长房长孙经常流露失望情绪。
这孩子胆小如鼠,在竹行埭,眼热荣荣药房小伙计在河浜里自由自在地游泳,纳香人拿着只脚盆叫儿坐上,从厨房后面把它弄下了水,请小伙计推着它河道上兜一圈。未及河中央,亨元吓得面孔变了色。
十岁左右的他还不敢一个人睡觉,去苏州祖母处,一觉醒来见父亲不在床上,对着正在雀战的父亲和其他长辈,大骂粗话。
无节制的吃零食,家里几个孩子数他消费大,而年青时靠手工刺绣度日的咸菜好婆,素以勤俭持家驰名乡里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不肖孙子。。。。。。。
阿判宠爱亨元如故。对他的缺点和弱点只是当作饭后酒余的谈笑资料。他喜在亨元同学面前揭发其子尿床,还兴致勃勃地领他们到房间看亨元的劣绩。
晚上,带了长子和次子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情不自禁会唱起自已编制的歌谣:
“金围墙,西装毕挺从汽车里走出来,金亨元衣裳拖一块勒挂一块,刚刚从地浪爬起来,喔唷,阿哥呀,侬哪能弄得迭能样子,像个小瘪三。。。。。。。”
尽管如此,若有宴请活动,仍然只有亨元有份与金根父亲一起上桌。苏州邮局派顾视察到同里邮局来检查账目,诚惶诚恐的阿判特地到菜馆买了几个炒菜,按惯例,父子两人陪客。
亨元毫无顾忌地尽拣着三鲜汤里的肉丸子吃,一阵风卷残云,把几只炒菜里的精华扫荡殆尽。顾视察瞪着那双金鱼眼睛张口结舌;阿判抚筷叹息。
所幸,事先已由咸菜好婆将亏空的钱款填上,金鱼眼睛拿不住什么把柄,阿判三等邮局长的位置还是保牢了。
一九四八年春,虚龄十岁的亨元要当寿星了,在好凑热闹的房东洪家好婆、同院邻居李家姆妈的鼓动下,请了一班宣卷来唱堂会。
顾名思义,所谓宣卷,就是由七,八个古装打扮的艺人,用独唱和合唱的形式,宣讲一本故事。
全部内容实际上仅由领班一个人叙述,其他人只是在每一段的结尾共同哼上一句:"弥陀那摩佛,那摩佛"而已。
记得这一天所讲的故事是有位员外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做官的;二女儿许配给经商的;唯独小女儿私订终身,与一个穷书生相了好。在老丈人做寿那天,姐姐,姐夫出尽了风头,小俩口却受够了侮辱。
三女在悲愤之下对老头子口出不逊之言:“若要享福,鼻头向北”(意思是老人要依靠这些势利小人安度晚年是不可能的)
结局如何?果然给小女儿说中:
几年后,老人宅地发生火灾,家财化为灰烬。长女,次女夫妇把落难的父母当作上门讨饭的乞丐看待;倒是得中状元的三女婿不计前嫌,把岳父,岳母奉为上宾。
堂会结束,由房东好婆和邻居姆妈共同掏了腰包,算是送给亨元的寿礼。
整整又过了一年,形势急转直下。亨元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小小邮局兼发行报纸,邮局就设在家里,拒台内外成为议论朝政和局势窗口,再加上镇上一些头面人物也不时到这个新闻窗口来转转。
耳闻目睹之下,戴着绒头绳帽子的扁头亨元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国民党也许抵挡不住会让共产党打过来。听说共产党毫无理性,杀人放火,真的打到同里来,非但好日子呒没过,性命也难保险。
那么还是默默祈祷国民党打得狠一点,把共产党赶过去。亨元当时正热衷打乒乓球,每天对着墙壁拍球记数,给自己订个标:连续打不到一百下共产党就要打过来;超过一百天下太平。此法使亨元或喜或忧,全凭球艺决定。
阳春三月某一天,亨元读书的秀才弄小学突然提早放学,说解放军快打过来了,大家逃难去罢。
亨元滚着铁环(一种玩具),七转弯、八转弯在街上游逛,只见商店都已打烊,家家门户紧闭。一个比亨元大几岁的大小伙子站在自家门口,瞪着眼睛指责对方:"快要打仗了,这小赤老还有心思玩铁环。"
亨元穿过尤家弄到了吉利桥堍下,只见兼作住家的邮局也一片惊慌。这邮局,租借洪姓破落地主最外层的一部分房屋。
进得两扇黑漆大门是一个墙门间,右壁一个窗洞,可窥见隔壁铺着木地板的卧室。出墙门间横卧一条走廊,左通厨房、右抵卧室。
过走廊是一个天井,天井右边是卧室走廊。亨元的三弟陈三出生后摇篮就放在儿。走过天井才到达邮局的"公事房"。其实,这是洪家房东的大厅,正中一块匾额书"文魁"两字,亨元只识半边,读作"文鬼"。
据说洪家大厅经常闹鬼。与"公事房"仅一板之隔的地方是二姐盆子和三姐哈哈的住处,她们证实:夜深无人之际听到过翻抽屉的声音。阿判的酒友天吃星,说不怕鬼,曾打赌在"公事房"睡过一晚上,次日,吓得发了高烧。
从大厅再朝里走,是一条长弄堂,通房东洪家和房客李、石等家。
闲话少说,这天亨元进了家门,只见父母亲均一筹莫展。原来共产党还没有打进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在乘火打劫。
洪家这个黑漆大墙门可能是他们的目标。耽在家里很不安全。远远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声,胆小的阿判和受丈夫感染战战竞竞的纳香人,连忙走出天井到墙门间去关大门。
关了大门以后想到,有机关枪和手榴弹的大兵门是挡不住的,只得带了儿女们从大厅往后撤,撤到洪、李两家合用的二厅里。
忽然发现:天井东边的围墙已经与隔壁方医师家住宅打通,也就是说可以从洪家进入方家院宅,反之亦然。如果败兵真的来骚扰,可以到隔壁去避难。
过了一个时辰,阿判唯一的邮差寿生来报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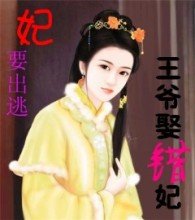


![[裴晓庆] 下雪的故事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