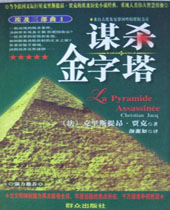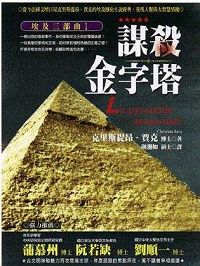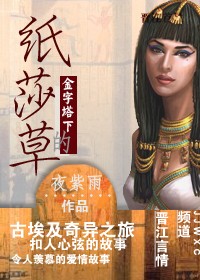红底金字-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享受。玩法里最简单的一种是把冰棍棍往墙上扔,看谁的反弹得远,实际上是比力气。还有一种是将冰棍棍置于窗台或乒乓球台子上,露出一寸左右的头,然后用食指和中指猛剁一下,看谁的远。
那时冰棍的品种单调,冰棍棍进入游戏领域的,是三分和五分一根的那种,竹子做的,有三寸长短,比毛衣针略粗一点。木制冰棍棍不带玩,手背朝上,中间三个指头垫着,小拇指和大拇指别住木头冰棍棍,朝膝盖一磕,就折了。攒冰棍棍,不能指着老赢,高手毕竟有限,大家的本领都差不多。更不能靠自己每天吃的一两根,因为玩起来都是一把一把的。最好的办法是“扫”大街,逮着一条马路搜寻,一趟下来能收获不少,至于卫生与否,说句孩子的糙话:“管丫的呢。”
瓷片、铁片、奶瓶盖
瓷片和铁片的玩法,和三角、冰棍棍差不多。玩瓷片兴起于修地铁时,从工地上流散出来不少五颜六色、方橡皮大小的瓷片,到了孩子的手里,蔚然成风。后来发展到“洗劫”公共场所,从墙上和地下扒瓷片。有个朋友住在宣武区,他们院的孩子经常到南线阁的大华陶瓷厂偷瓷片。铁片来自钢铁厂,有圆、长两型。后来的调查显示,玩过瓷片的孩子要远多于玩过铁片的孩子,这只能意味着瓷片找起来比铁片容易,或者说,“出品”瓷片的地方多于钢铁厂。
那时订牛奶,论磅,有一磅和半磅两种,盛在如今一种盛酸奶的玻璃瓶子里,叫奶瓶。每天早上把空奶瓶放在窗台上,送奶的蹬着三轮车过来换奶瓶。奶瓶口上包着一层纸,用皮筋扎着,揭开后还有一层和瓶口一般大小的硬纸片,是为牛奶盖。这东西攒多了也成气候,一摞一摞的,玩法以接抓为主。
糖纸、剪纸
糖纸是女孩攒着玩的(小男孩也攒),不进入“赌博”环节,但经常互通有无。糖纸都夹在书里,一页夹两张,按类分,五颜六色,花哨。糖纸的分类就是糖的分类。有蜡纸的、玻璃纸的等等。那时上海奶糖如大白兔和米老鼠名气最响,糖纸是蜡纸的,被奉为上品,高粱饴、黄油球等品种也是蜡纸的。酥糖是一般胶版纸的。女孩攒糖纸和男孩攒烟盒一样,也须不怕脏不怕累,到垃圾站里刨。所不同的是,回来后再处理比较麻烦。玻璃纸的要过水洗干净,晾上。蜡纸的先在下面垫一层烟盒里的锡纸(孩子叫金纸),再在锡纸下点火熏,火要恰到好处,可以一下把皱巴的糖纸捋平,过火就成了“烧”,反而坏菜。攒糖纸类似集邮,不少糖纸配着套,得想办法把它们弄齐。成套的玻璃糖纸夹在一本书里,翻着看,对女孩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米老鼠糖纸花样斑斓,当中一种红色的最少见,不容易收集。曾听沈小农夫人任淑平说,她小时候钟情米老鼠糖纸,迷得不得了,非攒成一套完整的则不甘休。家长被缠不过,就领她到崇文门井冈山食品店(前身为法国面包房,北京一种专营西点及高级食品的商店),花八块钱给她买了一铁盒米老鼠奶糖。孩子都喜欢吃糖,拿糖哄孩子,也是那时候家长的惯技。但这次却不是冲糖而是冲糖纸去的。任淑平已记不清通过那盒子糖攒出多少张米老鼠糖纸,总之,自己攒够了,还分给别的女孩不少。
剪纸是一门艺术,归于美术类。但北京孩子“创作”的剪纸,并非剪出来的,而是刻出来的,名为“刻剪纸”。这当然不属于对艺术的追求,而是刻着玩。步骤如下:先到商店买电光纸(电光纸五颜六色:红的,绿的,黑的,天蓝的……);然后将现成的剪纸铺在垫板上,再铺上电光纸(不带颜色的背面朝上),用铅笔涂抹,直至覆盖剪纸,让原剪纸的刻痕凸显在电光纸的背面,这套程序近似制作书法碑帖的拓片;取出原剪纸,即可下刀(竖铅笔刀或剃须刀片),按痕迹刻,刻毕翻过来,就是一幅作品。剪纸的造型按说是不受限制的,但当年干什么事情都为政治气候所笼罩,剪纸的主题也都如此。成套的样本有马恩列斯毛头像、一大会址、井冈山、韶山、遵义会议会址、延安、天安门等革命遗址系列图,雷锋、欧阳海、麦贤德、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组图……刻好的剪纸和糖纸一样,都夹在书里,互相传阅。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弹球
弹球分两种,一种是带“芯”的,就叫弹球,是玻璃跳棋的棋子;另一种无“芯”,叫泡子,体积较弹球稍大,是一种玻璃原料。泡子没芯,但颜色有白蓝黄绿之分。弹球的计量单位是“颗”。
弹球的玩法有不少版本。最惨烈的是“真赢”(当年玩什么都有“真赢”和“假赢”之分)。先要问清楚:“真赢假赢?”赢球的玩法称 “出锅”,以两三个人为宜。在土地上画一个比课桌面小一圈的长方型的“锅”,每人出一个弹球,置于锅内。距锅十米开外,画一道线。每人从锅的位置把手里的老子儿(母球)弹向线的方向,离线最近者先出手。“出锅”的胜负,规则与三角中的“撮锅”没区别,区别在于手中的工具,三角是铁链子或“排”,弹球是球,技巧性的要求要高一些,一般不直对着锅出手,而是斜着打。有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用两颗球赢回一副玻璃跳棋,尽管有好汉不提当年勇一说,但这话如果属实,他至少是当过他们院的弹球高手。还有个朋友,本来赢了一个孩子十来个球,这孩子回家把他哥叫来,威吓之下,又吐了出去。
除了“出锅”,还有“叮大厢”、“吃鸡肉”、“五坑”之类的玩法。这些一般不挂球,属于纯粹的游戏。后来“叮大厢”和“五坑”不怎么玩了,一直流行下来的,惟有“吃鸡肉”。
“吃鸡肉”,理论上人数不限。先在地上挖一个小洞,从十米开外的一道线上开始弹球,目标是把球弹进坑里,和打高尔夫球的意思差不多。中间环节是轮到谁弹,你可以把球冲着坑里弹,也可以根据形势,打别人的球,使之离坑更远,这又有点像斯诺克台球。玩起来也不省事,准度,审时度势的素质,都不可缺。先进坑的呆在旁边看热闹,最后剩下的一个,有两种选择,要么冒险把球往坑里弹,弹进去,大家都重来,无所谓输赢;要么把球弹到一个距坑三揸以里的地方,名曰“挨吃”,其他参与者自坑的位置把球弹向挨吃的球,如都打不着,即告结束。如果最后一人把球弹不进坑(离坑很近),或离坑三揸以外(可以就近击打),鸡肉就算“吃”上了。一人击打一次,要是七八个人,挨“吃” 的球的落点就不知离坑多远了,往回扔不到三揸以里(更不可能直接进锅),再接着“吃”。
“吃鸡肉”两个人玩没多大意思,三四个人以上,“鸡肉”一旦“吃”上,就很难收场。一两个小时过去也是它。被“吃”的孩子往往冲着坑的方向瞎扔,直至绝望。有时候别的孩子大老远过来,人还未到,声音先到:“谁挨吃呢?”经常是双方都累了,或到了饭口上,家里的大人连呼带叫,便以饶了挨“吃”的孩子而告终。挨“吃”的球被“叮”成两半,也是常有的事情。
弹球不像烟盒和冰棍棍,前者大街上捡不到。现在已很难说清,当年的孩子个个揣一兜子的弹球,源自何处。有的孩子专门做个类似烟袋模样的袋子,用来盛弹球。一般是装在裤兜里,不玩的时候手都爱往兜里和弄,哗啦哗啦听响;玩的时候抓出一把来,挑一个“疤痢”最多的出阵。弹球与泡子不可同场竞技,似乎泡子的含金量差一点。如果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新球,能让周围的孩子眼晕一阵子。倘家里有一套玻璃球跳棋,那就无异于今天藏一幅张大千的画,是不会舍得拿到球场练手的。因为球一旦“出场”,一盘下来,就难免会被叮成“疤痢”。
弹球的姿势也有讲究,标准的姿势是拇指弯曲,用拇指关节处与食指指尖夹住球,然后弹出,这样既有力量,也容易瞄准。弄不好成了拇指指甲与食指的弯曲处触球,则被讥为“挤豆子”,犹如游泳姿势里的“狗刨”。瞄准的时候,各人习惯也不尽一致。有的孩子作半蹲状,把球架在膝盖上,有的孩子用左手支撑在地上,再把右手架在左手上,有点像打台球。如果故意把持球的手前移,被称为“大努”或“大杵”,属恶意犯规,好像也没什么配套的惩罚措施,大不了重来,玩嘛。
弹球的很多玩法都离不开坑,挖坑也很简单,或者说不用挖,找一块土地,把大泡子放在地上,脱鞋,用鞋底子猛劲一拍,再用手捻两下即成。
说起来这些收藏和赌博式的玩,都不是消费意义上的游戏。孩子玩这些东西,起初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正因如此,它们才能风靡多时,让几代孩子乐此不疲。倘不是玩出来的,你家纵有三副崭新的玻璃跳棋,家长每天给孩子一张中华烟盒,也绝对找不到那种快感。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骑驴砸骆驼
这里说的群体,不是“三五成群”的概念。今天一个院的孩子,想踢球恐怕连凑足一支足球队都不太容易。那时哪个院里的孩子,玩起来都是成堆的,十个八个算少的,动辄二三十个。彼此都叫小名或外号。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用第一人称说到他们院孩子的外号及其来历:
姓叶叫夜猫子,姓江叫江米条,姓蔡叫菜包子,姓杨叫杨剌子,姓支叫支屁股,姓甄叫小珍主,姓吴叫吴老八,这都是因姓得名;还有因体形长相得名的:棍儿糖,杆儿狼,猴子,猫,大猪,白脸儿,黑子,小锛儿,大腚;一些人是兄弟排名叫响了:老九,老七,三儿,大毛二毛三毛,大胖二胖三胖到四胖;个别人是性格:扯子,北驴,还有一些不知所为何来,顺嘴就给按上了,没什么道理:范三八,张老板,老保子,批崴子,任啧儿,朱咂儿。②
这肯定是一个“据不完全统计”,也已经几十人了。你我他的院里的孩子,也一定不乏与上面的外号重复者。像从大毛数到七八毛,小三、小五、小六,更不在话下,院院都有。什么紫茄子,大楼,小楼,老包子,大猴子,小猴子,老尖,大灯,猪头,曩包,大妈,老杜……叫老什么的,如果和姓搭着,容易闹误会。我们院的“老杜”住一楼,有孩子对着窗户呼“老杜”出来玩,结果他爸出来了。概而言之,小、大、老,经常是孩子外号的第一个字。
孩子一多,群体活动就有了土壤,一些项目经久不衰。
骑驴砸骆驼
简称“骑驴”。分两拨,先猜,输的一拨当驴。一人靠墙立着,叫“柱子”,下一个把头插进立者的裤裆里,如此类推,构成一长串的‘驴’ 。另一拨孩子依次完成如下动作:经一定距离的助跑,扶‘驴’,跃起,腾空,落在驴背上,整个动作类似跳箱。然后由打头的与“柱子”猜猜猜。“骑士”赢了,接着当骑士;输了换位置。也有固定一人当“柱子”的,哪拨都不属于,不挨骑,也骑不了别人。
玩“骑驴”看似简单,实则颇有些“技术含量”。最先骑的,弹跳力要好,尽量往前蹿,否则一旦失去余地,最后有人骑不上去,则判骑士一方输;最后一个骑的,除了弹跳力,更需要的是分量,最好是大胖子,因为一旦把“驴”压塌(趴下),则判“驴”方为负。所以末尾一个已经不必长距离助跑了,只须玩命往起跳,越高越好,以期狠狠落下去,造成对方“突然死亡”。猜的时候,能赢最好,赢不了也尽量猜平,多在“驴”上呆着。有时候猜来猜去,几分钟过去了,尚未分出胜负,“驴”里有支持不住的,趴了下来,则判“驴”方输。也有事先买通“柱子”的,那样“驴”就惨了,弄不好这拨孩子一个下午光撅着当驴。所以猜起来也是争吵不断,互相指责对方玩赖,是常有的事情。有的“驴 ”老挨骑,实在气不过,会尥个蹶子,在“骑士”已经腾空的片刻,突然把头从前面的裤裆里拉出来,制造一个空挡,把“骑士”狠墩一把。
攻城
几年前有个“五一”,北科大一个有收藏癖的朋友约我一道去河北的县里转转,那时还没有节日放长假的规矩,他的旅行理念是不往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我跟着他去了定州和曲阳,果然开了点眼界,在曲阳县城边上一个残破的北岳庙的大殿里看到了吴道子的壁画,以及一块当年钱玄同为当地某学校题写的石碑。他还偷着揣回半块古瓦—秦砖汉瓦嘛。我们在这个俩足球场大小的破庙里盘桓了半日,也许是怀古的思绪连带出怀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