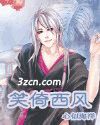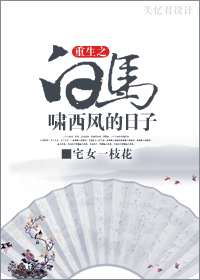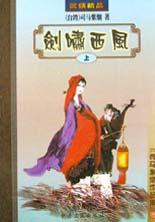宋:西风凋碧树-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左相吴潜排挤出朝,开始独领朝纲。此时,蒙古大军在西路取得重大战果后又从东路渡淮南侵,这年二月趋犯京湖,进围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鄂州。似道受命危难之际的表现是可以想像的,入援鄂州后,果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竟私许割地称臣以求妥协。所幸蒙古内部纷争突起,在鄂州宋军的顽强抗击下又无法遽得全胜,不得已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军北归,似道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凭空就捞到了一件盖世伟业。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肃清之捷。失去判断力的理宗龙颜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并召班师,同时敕命改元为“景定”。这是理宗最后一个年号。
时势已使人不得不发出季世之叹。
杜范曾对帝国军队的状况做过一个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边方帅臣丧尽德操,“黄金不用于反间敌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赐不用于士兵,而用以交通权贵”;其次是“赏罚颠倒,威令慢亵”,最后导致重任者怙权攘夺,禁兵骄悍难制,兵盗群聚,相为剽劫。军队有名无实,则难当卫国之任,这是最危险的事情。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在淳祐年间,杜范对国家的民事状况同样也有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旱荐至,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渐近辅,殍尸盈道。”
如此情形下,贾似道之流犹在歌舞逍遥不舍昼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贫国,有贫民,而无贫士大夫”的精辟之论。主修宁、理两朝实录国史的黄震在后来也说,国家大弊有四: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帝国半壁江山固然富庶丰饶,但历经战乱之后,土地日蹙人民益伤,最后以一百余郡之残力,养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犹且不足,又遑论日渐繁重的军费。本朝由于冗官冗军的先天弊病使财政问题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趋于严重,南渡以来休战之后稍有改观,但同样未能避免重蹈覆辙。问题出在帝国既未能统筹安排开战的时机和规模,就只能长久实行重税重赋的刻薄手段,天下财帛并非取之不尽,于是推剥脧削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对王安石理财的否定使南渡帝国在经济制度上无所更张,使伤贫而不夺富的不平等的现象纤毫未变,以至于生齿之民日烦,而权势之家日盛,兼并既滋,百姓益贫。四海之民既不再有应得的权利,又何意克尽应有的义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忠臣义士们对帝国的病象的慷慨陈词,始终不绝如缕。畅言忧患从来都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激扬人心以作最后一搏的真诚呼唤。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其中既有对大道日丧的激愤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是对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向往和期待。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1节 水天空阔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邓剡(公元?——1297年)
地分南北,人有东西。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牲畜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防护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从民族的角度上说,生活在该区域的许多部落都属于同一个大民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蒙古”族,与突厥族及属于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处于这一地区的边缘,因而得以与中国较早接触,也正是由于契丹的强盛,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动,开始沿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一带。关于这次西迁,蒙古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道:一对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苍狼”和“白鹿”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蒙古重新兴起并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时间确实相当之晚,因为耶律阿保机直到公元924年才驱逐了该地区的突厥族。
一个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缘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这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纪年的绍兴三十二年生于斡难河畔的铁木真。铁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诸部激烈争战的融合时期,九岁时,身为蒙古乞颜部首领的父亲就在部落战争中死去,铁木真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十几年里九死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木真正是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生活磨炼出他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会了他应付时世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使他最终成为草原民族豪放气概和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伐金的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集诸弟、诸子、驸马、部族奴隶以及各部首领召开议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树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国。“汗”原是部落首长之意,北方诸族都以此词来称谓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体含义已无从得知,但它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尊称则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诞生,是世界范围内震天动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进攻的是西夏和西辽,后者是辽国灭亡后契丹残部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在取得胜势后立即就转向了金国。蒙古对金人的仇恨是简直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因为金廷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各部采取极端的压迫政策,甚至在灭辽后,出于对北方各部的恐惧感,每三年出兵掳掠杀戮一次,谓之“灭丁”。如此残酷的灭绝行径,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开始伐金后,举国之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以蒙古强大的势力,孱弱的金国已根本不是对手,四年后就丢掉了中都而被迫南迁汴梁。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对中原的兴趣,也尚未摆脱游牧民族掠夺的禀性。克服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怯绿河上的宫帐中,依旧过着他们传统的游徙生活。大约在两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转而向西,对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帝国展开了征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斗的最初起因也是由于贸易上的纠纷酿成的,这再次证明草原帝国的彼此征伐与物质需求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这场西征几乎荡平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最远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第聂伯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蒙古军队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场战争同时也使蒙古帝国获取了极大的物质利益,虽然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禀信的那种摧毁一切、消灭一切的信条,其实也是长期以来饱受压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他能把这种心态发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却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不过,雄才大略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仍旧只是局限在以弓马取天下的范畴里而已,他还没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道理是:屠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征伐金国并占领中都燕京后,成吉思汗听说了一位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的名声,并于三年后将他召到帐前,向这位博学之士讨教命相占星之术。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完全汉化的契丹人家庭,长期侨居中原,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士人。然而他对于蒙古帝国的巨大影响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成吉思汗除了术数之外,对耶律楚材的儒学不感兴趣。
此外,成吉思汗还接触过一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汉人,这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全真教的掌门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门派,在金国入主中原后发展兴盛,到了邱处机时,门徒遍及整个北方,具有相当的影响。成吉思汗同样是在燕京听说了这位长春真人的名声,不惜派人万里迢迢把他请到了西征行营。与召见耶律楚材的性质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请求这位仙风道骨的真人教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到达了蒙古御营并随之北上。很难猜测真人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应召蒙古大汗的动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响应过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征召。虽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动机后十分失望,但这位道行高深的人并没有以丹鼎灵药之术来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诚恳的劝说,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论而不嗜杀戮。真人强调说,只有清心寡欲才能长生,敬天爱民才能一统天下。显然,成吉思汗并未能为他的高深理论所说服,尽管他始终对真人保持了一种敬重和推崇的态度。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在围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带着遗憾不幸去世,因为他对宿敌金国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