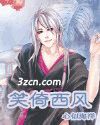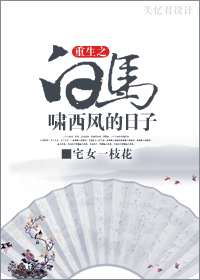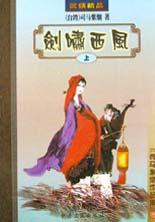��:��������-��2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ǵڶ���������ࡣ�úƴ��������β����������ڿ�ս·�ߣ�������ƽ�ڿܣ��������꣬�����������������ĸ�������ȴ�������˹�ά����Ю˽���ˣ�Ҳ���㸲�켺�����������������������٣���Ȼ�������ݡ���������
�����������������������ú�ȡ��ʤ�ơ�����ɱ����Ƿ�ʹ��ʷ�ƹ���������������������������ڱ��������Դ˰�ȥ�����������������덃���ʾ��������ν����ߺ�����Ҳ������Щ˵����ȥ����������
��������������ԭ���ǰ˸��֣������˹��ϣ����˹鱱������Ȼ���������DZȵ���ġ��Ϲ��ϣ���ʱ��������ö��ˣ���ȷ�е�˵����˸����Dz�������¶����®ɽ��Ŀ����¶����������ʵ�뷨����������
����������ν�����˹��ϣ����˹鱱������˼����Ҫ�Ѻӱ��˹��ڽ���ԭ�˹�����ԥ���⻰�ĺ���Ҳ�����������dz����˵�αռ�����״���������۹�����Ҳ���ˡ��ѱ����˸��ߣ��ⲻ�͵���˵������϶ɳ����Ǵ��ε۹����������ѹ����ӿ����õ�����������
��������������˵�����˹��ϣ����˹鱱�������DZ��ˣ��鵽����ȥ��������������
��������������һ������ľ���������������������˶��꣨��Ԫ1132�꣩���¶�ʮ���գ�������گ�����������ƴ�������֮�ͬʱ���ڳ��ã�������������֮�⡣��Ϣ���������۷��ڣ������������ۣ��������ޣ������ٳ⡣����������ʸ֮�ġ���������
���������������������˻��������ۣ�ʵ���Ƿ�����˼����Ұ���в����˾���Ϊ���������ʵС������������Ϲ�������ɵ㣬���ǻ����������п����ǽ��˵ļ�ϸ�������Գ��Ǵӽ������ղ������ѵģ������������ݹ飬Ϊ��������һ�س����ײ����ӣ����������ղ�����˵�����˹�������ʱ�������Ű���ڣ��Ķ��������˴ӱ㻹�硱������Ҫ���ǽ�����Dz��������ô����������Ƶ�˵�������ҵ��ǣ���Ұ����Щ����Ҳֻ�ǻ��ɶ��ѣ����ò���ȷ���֤�ݡ���������
�������������˶��꣨��Ԫ1132�꣩�����������պ��������꣨��Ԫ1136�꣩��ף��۹��������������һ�����α�������е�����ս��һ�ǶԸ��ص��ܵ��սˣ����о��Dz��ϵ��������Dzʹ��ʾ��ͣս���֮�⡣�Ը�����˵��ǰ���߲�����ʱ��֮Ҫ����Ҫ���Ǻ��ߡ������Ӹе����ε��ǣ���λ�Ժ�������Dzʹ���ͨ�ʣ���������������Է�����������Ҳ��δ��Dz��һ��֮�˱�Ƹ��ֱ���������꣨��Ԫ1133�꣩����ͨ��ʹ����Ңȥ�����أ������ڴ����˾�����������鵱Ȼ��ij����Ϣ��¶�����ڸе����Եĸ��ˡ�Ϊ�ˣ���������ֹͣ�����úƵı�������ͬʱ������Ժ��������ͽ�߽�������Խ���硣�������£�����Ф��Ϊʹ�������º�Ф�в���ʹ��������ʱ�����˽�˧�����ں���Dz�ľ���ʹ���ţ�˫�����ڿ�ʼ����ʽ��̸�нӴ����˺�ļ������͢������ս����̸������˫�����£���ʹ�η���Ӧ���̵�����������͢�ڲ����Ժ������������ʹ����һʱ�������¾��������⣬��������Ҫ������Ҳʹ���ڲ��ò���ʱ���������һ�ԣ�һ�ǽ��˵�Ҫ�����ߣ�һ�Ǿ����������ͺ�͢����������һЩ�൱�ֹ۵���������������ʷ��ͬ�Ļ�����һ�����ͣ�����Ϊ���͡�ս��ʵ��ͬһ���£��ؼ����������������������ж�ʮ��ı������ò���η��ηβ�������ʱ�����ս�ɻ���ռ����������Ҳ���ܲ�Ӱ�쵽���ǵ����ӣ����ܸ��ڴ��ĵ������һ��һϦ�ʹ�����õĺ�ƽ��һ�����ݡ���������
����������͡�ս�ļ���ѡ�������������֮�ϵ����ζ���ͬ��ʮ�ּ��ҡ����úư����������꣨��Ԫ1133�꣩���£�ֱ�ӵ�ԭ�����������ר�й��ڿ��̶�������ʷ�IJ������������ԭ�������������뱱����һ��Ч����ʹһ�����͵ĸ��������������˺�����ʤ�ǵ�����һ������࣬ʤ�������˶��꣨��Ԫ1132�꣩����ȥְ�������ú��������εģ�Ҳ�ǵڶ��������ˡ��������úƺ�������֮����һ�������ڽ������꣨��Ԫ1129�꣩���Ǵα�����ͬ����������֮�����������˵�ʱ�������ܺá��������꣨��Ԫ1134�꣩������ʤ�ǰ�����Զ����ſ��Ⱥ����ࡣ��������
���������Զ���Ԫ���϶ɺ�������˾�ɡ���������ʷ����ʷ��ة���ɲ�֪���°��ࡣ����������һ�������ɣ�����ս���ء������߲��أ�����������Խ������һ��Ķ��£������������ո�����Ҫ�����������ţ���һ���ٳ�����������ս�£�ʹ�����ȡ��ʤ������ˣ��Զ��õ��˸��ڵij���������ſ���������磬�������꣨��Ԫ1129�꣩��������Ӫ�����Ա����ϣ����������δ�����������ʹ��һȥ�������ꡣ�ſ��ڴ������ֿ�ս��ȡ�ù�һЩʤ������Ҳ�ڸ�ƽս������������ʧ�ܣ�ɥʧ���������������Ͻ����ſ���������ʧ���Ͼ�����ȫ��������غ������IJ���������Ϊ���ν�����ǣ�ƽ�����˺ܴ�����ã�Ӧ���ǹ����ڹ��ġ�Ȼ���ſ��س���ȴ�в����˹�����ɥʦ�����������������˵���������д����ǡ��ܻ�Զȥ�����˷������س��ǡ���֪��λ��ǰ���������������ڲ�û��Ϊ�������ң���Ȼ�������࣬�����������˼��������ߵ�ϣ������������
����������������ԸΥ���ԡ������˼�����һ��ʼ�Ͳ�����Ħ�����Զ��ر�ע�س���֮ѧ�����ʮ���Ƴ�Ԫ�v���Ρ��������ڽ��׳��ڰ�ͣ����ʯ�������е�������λ������������Ԫ�v�������Զ�һ�����ٳɡ��Զ��˴�������ᳫ����֮ѧ��ߪ��Ԫ�v�����ﲻ���������Ե�ʮ��ƫ������Ц���ǣ������Զ���û�м������ã�����ð�Ƴ����ӵܣ���Ҳ���ɲ����Զ���Ŭ�����ϸ��ڱ��з�����֮�⣬һʱ�������˳�⳯Ұ���������Ҹ�ȼ֮�ơ���������
��������Ȼ���ſ�ȴ����ΪȻ�����ٲ����Զ������Ը��˺ö������ƻƣ�����ΪԪ�vδ��ȫ�ǣ�����Ҳδ��ȫ�ǣ��Գ���֮ͽ������ҰҲ�����������ڶԴ����˵�̬���ϣ��Զ����أ��ſ�������Ҳ�в�ͬ������ԭ���ϵ��ش�����Ȼ��ӳ���ճ������У��������֮�䲻�ϲ������������ۼȲ��ϣ�����֮��Ҳ�г�ײ���������꣨��Ԫ1136�꣩�ף��ԡ��ŵIJ��ʹﵽ���㣬�Զ��Ի��ϱ�Թ˵����Ȼ�������������ֵܣ������չ��࣬��ͬˮ�𣬲������˶�ȥ��������һϵ�г�ͻ���Զ��������������꣨��Ԫ1136�꣩ʮ���°�ȥ���Ÿ��º���Ϊ����������۪���ѱ�Ͷ�е��¼����ſ�Ҳ���̴�ְ���������ſ��˼ʵı��ֻ���ֵ�óƵ��ģ���������������Զ��Դ��������Զ����ࡣ��������
���������ԡ��Ų��������DZ�������ĸ�Դ�����Ƿ��µIJ�����ˡ�Ĵ�����������������ʼ��ٸ�����ſ�����������Ը����������ϲ����ʿ����˶�����ʮ�����ͣ���ֹһ�ε�����������ǰ�佱�������������꣨��Ԫ1136�꣩����֮�۽�ռ�Ϸ磬�����ľ�����ʼ��ת���ſ����������ã���ʹ�佥�����Զ�ȥ���ſ���һ������������������������������Ժʹ��λ�á��������ſ�������������һ��ʱ���Ҳ��������Ҳ����̫���ˡ��Զ������ܱ�����������������������ķ�ӭ�����£���Ҳ�ı����뷨��������Ϊ���������Ρ��������˵��������ʹ���ǵĵ۹��Ӵ����������һ����˼��ȡ�������Ա���ƫ����Ȩ��ҲΪ�����Լ��ĺ�����Ծ��˷�Ĺ����������
���������Զ��²�����������ˣ��ſ���ʶ���������ø���������������������λ��֮��֮���Ƹ���Ĺ������֮ͽ����̾���ǣ�����������������������ַ�Ϊ�Լ���ƽ��·����������
����������������
���������������꣨��Ԫ1137�꣩��һ����ƽ������ݡ���������
������������Ҫ������ǰ˵���������꣨��Ԫ1134�꣩���£����Эͬ��ԥ�����Ͻ����ڽ������µ�ʱ������ξ��ij�����������˼������в������֪��ô�����ǰ������������ʮһ�¼��һ����ѩ֮ҹ��ͻȻ�ͳ���������ʹ����������ս�۲�����֮���º��֪����ԭ���ǽ�̫�ڲ��ص���Ϣ�����˽�Ӫ�������Ѿ�������ս����������
����������̫�������������꣨��Ԫ1135�꣩���ɽ�̫�������Ձ���λ����Ϊ�������ڡ�����͢�Է�������ս����ȡ��ʤ���������������������ں�����·���Ϊ���ľ����ɱ����γɣ�����֮�䲻�ɱ���ؿ�ʼ�˼��ҵ����������������ں���ν�ġ�����͢���ں�����Ϊ������ʵ���ľ��¼��ţ����������ƶ�·�������ղ������������ں���Ȩ���������죬��Ȼ�����µ۽����ڵ��ɼɣ���λ֮�����Ȳ�ȡ�ܿյIJ���ж���ں����˵ľ�Ȩ��Ȼ����Ĭ�����������͡����ղ�����������Ϊ��һ��ʵ���ɺ����ż��ں����������꣨��Ԫ1137�꣩���죬�ں����ڱ�������������ԥ�ġ����롱�������ղ�һ���������ģ�������ԥ������Ϊ����ƾ������ʸ��ں�����ʹ�����ղ���Ϊʹ�ޡ����ղ�һ��̨���������ڽ����ǰ������ԥ�����õ�����Ӧ�������ʮһ����Ѯ����͢��ʽ��گ�ϳ�����ԥ��α�롣�˺����ղ�������Ԫ˧�����ղ���Ϊ��͢����Ȩ���Ҳ�Ǹ����������������Ķ���֮һ����Ϊ��˵���ղ�һֱ������ʶ���������˵�˽�����ܲ�������Ȼ�������������̸�У������������Dz��ܺ��ӵġ���������
���������ں����������ڲ���ì���ֿ�ʼת���������������ͺ����ղ���Ϊһ�ɣ�����һ��̫�������ڎ֡�����ͳ˧֮һ�����������������ͻ��Ϊ�������Լ������룬���ղ���������͢ʾ�Ժ�̸֮�⣬�������ʮ���·�Dz����ʹ����������ʾ���Թ黹�������ѣ�����ֻҪ��͢������Ը����ԥ�������֮�ع黹�����״���ʱ�����ղ���ζ���˵����������
�����������Խ��Ժ��·��ͨ���������ƽ���ˣ�����������
����������ԥα����Ѳ������ڣ��ν�֮�������ϵĻ�������Ҳ��֮��ʧ��˫����Ȼ���Է������������ǣ����ַ�������ǵĵ۹���ζ��ʲô�أ���������
����������������
�����������ڻʵ�Ϊ�˻������衣��ֻҪ�ܴ�����������һ�������ƽϡ�����������ԭ����������������죬�ֱ������ٶ�Dz����͢�����嵱Ȼ�Ƿ�ӭ�������������˰��꣨��Ԫ1138�꣩���£���ʹ����˼ı��ʯ�������ξ�����ʱ�������������࣬�����۲��۵�ִ���Ÿ��ڵķ��룬��ʼ�˵۹���ʷ��ǰ��δ�е�һ�κ�̸����������
�����������˵�Ȼ���п��̵���������ӳ�͢û�й�����͢�������ݵ�������Ҳ����֪һ�������ڵ�ȻҲû��������̬��ԭ������ִ�����۲���������̸�е������Զ������ܸ�ʹ�������˾ͱ�ʾ���ܽ��ܽ��˵���Ū�������ڵ���ԥֻ�����˺̵ܶ�ʱ�䣬���£��������׳�ʹ������ʮ�·ݣ������Ѿ��������������ȫ��һ�£���ȷ��ʾ������ͣ�����ͬ�����������������������¡�����Ⱥ����Ԥ������ʮ�¶�ʮһ�գ����κε��Զ�ֻ�гƼ���ȥ��ʮ�¶�ʮ���գ���ʹ��ͨ�š����ִܵ��ξ�����һ�γ�͢��������һ���������˶�Ŀ����Ϊ����λʹ�����ҵ�ͷ��һ�ǡ�گ�ͽ���ʹ����һ�ǡ��������������ȡ�گ�͡��֡���������������㶼�㲻��ȥ����ͨ��һ���ٰ����������Ͼͻ�ڵ�����ǰ��Ҫ���ɺ��飬���ǵ����Ӿͱ����ӽ��˵�گ�飬������˵�Ƿ�گ������ʲô����������ˡ����ǣ��������¶��˾��ġ���������
��������
����������ں�ɽ��10�ڡ�һ������
����������Ұ������Ի��ϲ���������ֻ���ٺ͵��������������ƺƴ�Ŀ����˳������ȵ��Ԩ֮�˾��ܴ�����ҵ����������Ͼ�������������֮��ĺ��飻������֮���еĻա��ն��ۣ����Ȳ�������ϥ�Ƴ����۹���ʷ�ϣ�����Ҳû�й���һ�����������Գ���֮���µеġ�������ݹ������������ʹ����������������
����������������ʢ�µ���λ�����ǿ����������������Ϊ���Ա������ˣ�����������
��������˾ѫԱ�������ɵ����˵������������һ���Ѫ����������
����������������
���������������Ժ�֮һ�֣���־������ʮ�ж��꣬�Ը������ң��Գ��ұ߱����Խ��ҹ�������и���Ҳ�������֮���Ծ������й�ک��˼��֮���ӣ���گ�ͽ���Ϊ����Ҫ�����Ի���֮���Թ��������������գ�Ī�������ŭ����������±���Ϊ���֮���գ�������������
����������������
�������������˵�����϶�������ߺ�������֮����һ�����衣��Ϊ�ɹ���ǣ����п��Կ�������ʿ��Ҳ���Ƕ�����̬���ö�������ʰ���ر�������Ժ�����������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