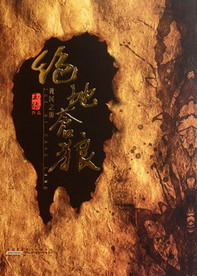绝地风暴-第7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车吧!”程万里点头。他理解马赛的心情,没有谁比马赛更想最先看见海达尔的下场了。
多里昆也道:“队长,我也去吧?”程万里摇头:“不行,局长这里事多着呢,都去了不好。”努尔笑道:“是啊,老多,司马义没抓到呢,有得你忙的。”
货车装好了,越野车开路,两辆车驶出了和库公安局。
马赛和多里昆是刚刚送克里木去市里回来的。峡谷基地一战,马赛最担心克里木的安全,尽量交待进攻的武警,但毕竟子弹不长眼睛。幸运的是,克里木还算机灵,用被击毙的哈力达的尸体盖住自己。找到他后,马赛又怕他控制不住,不敢跟他见面,直到三天后回到和库县城,才把他从看守所接出来,送去市里与热比亚相见。热比亚的身体已恢复如初,见到克里木抱头痛哭。考虑到两人的安全,征得李东阳同意,联系了克里木的父母,把他们送上去口内的火车。
“哎哟,我的妈呀!”
走出沙漠公路,越野车驶进了“搓板路”。躺在后座睡觉的努尔被颠簸弹下座椅,脑袋碰出了一个包,气恼地埋怨道:“妈的,老程,怎么开的车,我才睡不到十分钟,你跟我过不去,另挑个时间好不好?”
程万里冷冷地说:“睁开你的眼睛!”
“那又怎么样?”努尔边嚷边从座椅下跳起,像要吵架,却看见开车的是马赛。
马赛回头笑道:“没办法,努尔队长,我刚才已经是挑最小的坑走了,你实在想躺着睡,不如去后面卡车,重车没这么颠。”由于后面的卡车慢,走了八个小时,天快黑了,还没走到一半路。
“妈的,我不睡了!哎哟,又怎么啦?”努尔一手摸烟,一手摸打火机。车子刚好进入一处窄小的路段,有辆卡车迎面驶来,没有退让的意思,马赛只好靠边踩刹车,他又一头撞上了车顶。
“他妈的,怎么开的车?”努尔看见霸道的卡车,气不打一处出。骂骂咧咧跳下车,车门关得震天响。卡车也停了,同样有人跳下车,关门的声音也不小。程万里怕努尔惹事,也摇头下车。
太阳已落山,天色昏暗。努尔走了两步看清来人的脸目,大吃一惊,伸手去掏枪,站在他面前竟然是塔西。塔西也吃惊不小,不过他是有备而来的,手枪已上膛放在身后。两人像决斗一样,努尔吃了大亏,才掏出枪,塔西已扣动扳机。说时迟,那时快,跟后的程万里猛地跃起,把努尔扑下路基,躲过了一枪。然而,塔西的手没有停,枪口追着打,两枪打入程万里背部。
海达尔抢货车走了一段路,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感觉自己想到的,李东阳一定也想到了。于是,叫另一辆车的三个人带上三个货车司机,继续往藏北方向开,自己和塔西、艾尔调头返回南疆。
坐在车上的马赛被眼前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措手不及,枪也忘了掏,慌乱下车。双脚才着地,比他先一步下车的海达尔,笑盈盈地将一只手雷滚到他脚边。他本能地跳开,手雷也响了,人被冲击波掀起,撞上越野车,又在地上弹跳几下。
路基下,努尔的枪翻滚时掉了,推开压在身上的程万里,顾不得去看他的伤势,伸手去摸脚腕的另一支枪。
“哈哈,努尔队长,我们又见面了。不过,我不想见你,你还是去见真主吧!”
紧追不舍的塔西,已换了一支双管猎枪顶在努尔额头上。
努尔绝望地长叹一声,刚要闭上眼睛,发现程万里颤颤巍巍站起,一把抱住塔西。不过,塔西没费多大力便挣脱,转身就是一枪,威力巨大的猎枪把程万里打得飞上了路面。跟着,调枪口向坐以待毙的努尔扣动板机,却没子弹了。他气恼地一枪托把努尔打昏。
马赛被猎枪有震荡的响声惊醒,他只是一只腿受伤,扶着越野车站起,看清眼前的情景。右手摸出手枪,指向正在低头给双管猎枪填塞子弹的塔西。第一枪打中塔西的脸,第二枪打中了胸口,第三枪干脆闭上眼睛,直到弹夹打空。
海达尔以为马赛死了,和艾尔两人一人一边,走向落后了越野车十几米的装补给物资的卡车,两小心翼翼地枪指卡车驾驶楼。卡车司机看见枪战,缩在车里不敢露头,大气不敢出。海达尔担心车厢有人,绕了卡车一圈,向艾尔点点头。艾尔拿出一只手雷,还没拉开保险,“嘭!”的一声,胸口出现一个血洞,人飞起向前。海达尔惊得退到车厢后,只见马赛双眼微闭,怀抱猎枪,一瘸一拐地走近卡车。
“小马,趴下,小马!”醒过来的努尔发现已钻到卡车底的海达尔,焦急地大喊。
马赛的耳朵被手雷震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只顾往前走,海达尔一枪擦过他的头皮,他才知道趴下。这么一来看见了车底有人,他把猎枪摆在路面上开火。这是一颗霰弹,车底的海达尔大声惨叫,枪也扔了,眼睛也瞎了,一头是血,爬出路面,跌跌撞撞乱走。努尔从路基上来,把他推翻戴上手拷。
这一切,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两名卡车司机战战兢兢摸下驾驶楼,惊魂未定地看向嘶声嚎叫的海达尔和摆在地上的尸体。
“队长,你醒醒,队长……。”
马赛痴呆地抱着程万里坐在路面上,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越喊越大,然而不管他怎么喊,程万里也一动不动,双眼紧闭,那张黑脸更黑了,像在跟谁生气一样。
“睁开你的眼睛!老陈,睁开你的眼睛啊!”
努尔哭出声来,他万万没想到这句话,是程万里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15、
“哟,才半年不见,我们家维维变成大姑娘了!”
刘丽终于可以重见光明,看到每一个人都感觉新鲜,像刚认识一样,包括自己的女儿。
维维搂着母亲笑道:“妈,你不会连我爸也不认识了吧?嗯,那样更好,你们重新开始,可能以后就不会吵架了。”
“鬼丫头,夸一句就乱说话。”经过这一磨难,刘丽也希望跟丈夫重头再来。
维维撅嘴道:“哼,我爸真讨厌,去了这么久都不回来,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妈,等他回来,我们罚他做三天饭好不好?”
病房门外的谢医生和白晓莎,听到母女的话,双双哭声了起来,不敢进门。
“小白,你、你一个人先进去好吗?我、我的眼睛太肿了,我在花圃等你们。”谢医生两天前得知程万里牺牲的消息,每次从这个病房出去都要跑回办公室关门痛哭。
白晓莎眼睛也一样红肿,含泪点点头,拿出化妆盒看了看自己的脸,这才进病房。深呼吸了一下,叫道:“嫂子,维维。”
“你是……。”刘丽不认识这个漂亮的姑娘。
维维跑去拉白晓莎的手说:“妈,这是白阿姨呀?”
刘丽也亲热地搂白晓莎说:“啊,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怪不得是电视主持人。小马真有眼光。”
“白阿姨,小马叔呢?他和我爸去哪了,怎么还不回来?”
维维的话,差点又让白晓莎掉泪,她急忙转脸看门外说:“嫂子,我们到外面走走吧?谢医生说,你可以去适应室外的光线了。”
“好啊,走吧!”刘丽早就想出去,医生不许她马上接受太强的光线。
两人携手走出病房,维维一蹦一跳跟在后面。她心里奇怪,这位平时跟她很亲热的白阿姨,怎么今天突然对她不理不睬。
这时,住院部大楼外,身着整齐制服的向明和李东阳从远处走进花圃,后面跟随的是同样身着整齐制服的努尔、马赛、林建北、多里坤等十几名警察。
维维眼睛盯着这些服装统一的人,她像似看见父亲在向她微笑,向她挥手,往前跑了几步又停下,父亲不见了?她再次认真地看,想从中寻找出父亲,一个一个过去了,还是没找到,她又重新寻找……
尾 声
一年以后。
一辆轿车开进南疆公安局宿舍区,李东阳手提一只大行李箱走出宿舍楼,轿车司机下了车接过手提箱,放进车里。
“等等,还有好多东西没拿呢!”谢医生和李青又提几包东西跑到轿车前。李江阳奇道:“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李青说:“又不是给你的,是给维维捎的。”
“哦!”李东阳脸色微变,不再说什么。这时,多里昆和刘保山从另一栋宿舍楼走来,向‘谢医生打了招呼,若有所思地望司机把几件行李放进轿车尾箱。
“局长,搬家呀?你、你这回真的去厅里了?”刘保山小心翼翼地发问。李东阳摇头笑说:“你这个问题,问了一年了,换点新的好不好?我这是去北京开会。”
“啊,忘记你刚选上人大代表。”刘保山笑得很开心。
李东阳看了看两人说:“怎么,今天星期天,你们刑侦队又要聚餐?”两人现在一个刑侦队长一个副队长。
刘保山笑说:“是,不过,不在家,在恰克镇。”李东阳意外地说:“哈,你们可真会享受生活,聚餐也跑到乡下去?”多里昆笑道:“没有,克里木和热比亚举行婚礼,邀请我们去参加。”
“好啊!代我祝贺他们。”李东阳高兴地说,“咦,马赛呢?他们是好朋友,怎么不去?”
“马赛昨天小白已经去了,他们是伴郎伴娘呢!”刘保山答道。
李青悄悄走开,谢医生爱怜地望着女儿的背影。
恰克镇的一棵大柳树下,十几个身穿维族节日盛装的青年转成一圈,或跪、或坐、或站,有的拨弄卡龙琴,有的弹奏热瓦甫,有的敲击手鼓。木卡姆乐曲明快、奔放、热情,一下感染了周围的乡民,在老镇长艾买江的带领下,男女老少纷纷登场,随着节奏扭动身肢,翩翩起舞。大柳树下的空地,顿时变成了一个欢乐的舞场。马赛和白晓莎,脸上洋溢着笑容,也舞在其中。
“将来,咱们也办一个这样的婚礼好不好?”马赛道。白晓莎说:“好啊,叫热比亚给你介绍一个维族姑娘。”马赛道:“哇,意思是,你也要找个维族小伙子啦?”白晓莎白眼说:“哼,难说。我问你,这次是不是打算等到南疆没有恐怖分子才调回乌市?”
“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马赛叹息道。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正在往舞场外挤,他停下舞步,撇下白晓莎也挤了过去。
舞场外同样人山人海,那张面孔转眼消失,马赛四处寻找,却遇上刚刚到达恰克镇的刘保山和多里昆。
“喂,老婆丢了?你这样子像找恐怖分子一样。”刘保山笑说。
马赛表情紧张地点头道:“没错,刚才我看见了司马义。”
2003年3月新疆昌吉市昌吉酒店起笔
2004年4月广西宜州市寓内收笔
女儿的信
亲爱的爸爸:
今晚,又将是您的一个不眠之夜,尽管为了陪护妈妈,您已经在医院闷热的走道中熬了两个通宵。很抱歉,爸爸,我的出世,又让您继续失眠了。当然,您不是兴奋过度,您是黯然神伤,感觉内心失落,脸上无光。当叔叔阿姨,您的朋友们,来探望我的时候,我看见你那颗平时傲气凌人的脑袋,像驼鸟一样埋进身子里,您甚至拒绝向他们介绍我,似乎人家是来嘲笑您一样,您的难受全部写在脸上。因为,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您所聚集的爱,是准备支付给一个并不存在的男孩的,而我,是个女孩。
我哭了,虽然我还不会流泪。我对您很失望,爸爸,不仅是您那张写满难受的脸。在妈妈肚子里这十个月,您就开始伤害我了。还记得吗?您捧着《圣经》说:“神惩罚女人,要女人承担怀胎生产的苦楚,我不忍心自己的骨肉也受这份罪,所以我不要女儿。”还记得吗?您捧着酒杯说:“我不是封建,我不是重男轻女。我爱女人,但这份爱,只给我的母亲和妻子,不打算再给第三个女人。”最可恨的是,您居然跟一个叫冷静的家伙说:“如果我生个女儿,就卖给你儿子当童养媳。”别以为我看不见,我听见了。也许您是开玩笑,可您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爸爸,我这么令您讨厌吗?才呼吸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口空气,你便喋喋不休地抨击我的长相,“鼻子太矮、嘴巴太突,脸蛋太大”能怪我吗?护士阿姨说,我很像您,这应该全是您的过错。我好伤心,我要是真的这么难看,还不如再回到妈妈肚子里去。幸好您后来说:“长得挺白,一白遮千丑,女孩子家小时候难看点好。”我这才稍稍平静。不过,慢慢想来,我怀疑您是为了哄我不哭和安慰仍在产床上的妈妈才这么说的。
我知道,您想要儿子,不单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有个重要原因,您想让爷爷奶奶高兴,毕竟咱们包姓一直男丁不旺。听奶奶讲,包姓有位杀人太多的清官祖先,他杀的人虽说都是贪官,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