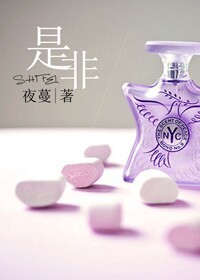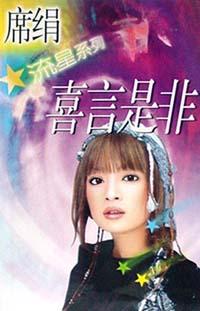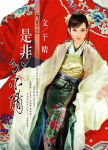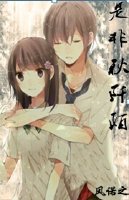是非曲直-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使我翻了翻……
尽管毛泽东后来谈及这件事,心情是很平静的,但当时他却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听凯丰讲话的。
凯丰攻击了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吹捧博古、李德,他不断地引用他早在莫斯科就背熟的马克思的话和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忍无可忍,他反驳了凯丰,但不像凯丰那样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调,而是语调平和地进一步说明了在他心中形成的那条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际上,凯丰的发言没有起到他想起到的作用,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这使得毛泽东的主张更全面更透彻地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夜,将被黎明取代。
毛泽东结束他的“补充发言”之后,博古便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明天继续讨论今天的议题。
人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同样也没有不散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虽然散了,但可以肯定,今天的夜,是一个骚动不宁的夜,是一个令与会者难以入眠的夜。
16日,会议仍在夜间进行;
17日,会议还是在夜间进行。
因为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间进行。
夜间开会,少去了许多干扰,与会者更便于集中精力来思考问题,冷静地发表意见,作出选择。
继王稼祥之后,张闻天第二个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
张闻天这一票也很重要,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张闻天的名字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
与会者的发言在继续。伍修权回忆说:
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朱德发言虽不多,但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这话落地有声,整个会场都在震颤。
周恩来在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并强调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与会者的积极支持。
生死攸关的较量(9)
所有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林彪。
此时,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团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此时虽然他在党内没担任什么职务,但讨论军事问题,他是有发言权的。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他应该发言。
此时,作为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并寄予了厚望的林彪,在这关键时刻,即使不从党和红军的命运出发,只看在他与毛泽东的情谊上,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毛泽东呼与鼓。
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种默认,也可能是一种对抗。
沉默,令人难以琢磨。
林彪在这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就连与会者也是这样。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的。
而当时和林彪搭档、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只是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说别的了。
不过,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由于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而陷入被动局面之后写道:
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注:指1934年),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林彪那时(引者注: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林彪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了《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不推行“短促突击”,谁就是违抗军委命令。聂荣臻说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种表态,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才保持沉默。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否定李德的军事指挥,李德就会把他当初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端出来,可能指责他是反咬一口。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可能把《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端出来,并指责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气了,这无疑将有损于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林彪干脆什么都不讲,听听就是了,这样连毛泽东也没有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态,甚至可能认为他年纪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发言更好一些,不发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
林彪鬼就鬼在这里,使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当然,后来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被批准。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虽然林彪保持沉默,没有发言,但在最后的表决中,林彪还是举手支持了毛泽东。这从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记录中可以看出: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引者注:指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由此可见,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凯丰、李德,有17位支持毛泽东,这17位中当然也有林彪。
在这次会议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并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权的记忆里:
会议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生死攸关的较量(10)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权力。
然而,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早在1月11日,蒋介石的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发出的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称:“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
蒋在珍用词不准确,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意思很明确:“毛泽东当了中共总负责”,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在珍更清楚。他的这份电报表明,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
后来,红军撤出遵义,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柏章辉的表弟余大勋,却愣住了,这里的一切如旧,二楼的餐桌仍放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只是多了些简易的木椅和那张藤躺椅。红军变了,并不像从前那样丢盔弃甲,他立刻意识到红军没有溃败而去,肯定是毛泽东当了红军的头头。
余大勋没有猜错,此时的红军确实在由毛泽东指挥。
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
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坡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